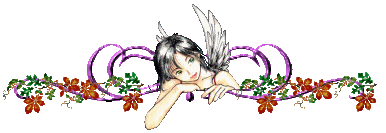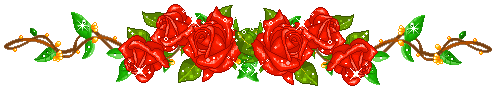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3/05/07 22:29:15瀏覽2560|回應0|推薦0 | |
保釣大將項武忠和他的狀元夫人郭譽珮(2)
保釣運動你可知? 現在看看不算遲, 莫叫後代子孫輩, 指稱你我無見識.
• 參加保釣運動 李雅明:你說你剛開始知道保釣這個事情是在耶魯的時候? 項武忠:我在耶魯。 李雅明:你什麼時候去普林斯頓的? 項武忠:就是那一年前後。 李雅明:你去Princeton,是1969還是1970? 項武忠:我到71年才正式離開Yale。 李雅明:71年才正式去普林斯頓。 項武忠:70那一年是正在休假(on leave),所以我一半時間還在耶魯,還沒有到那去。另外一半是今天開會有人提起,在波昂(Bonn)保釣的事情是我搞出來的。 李雅明:所以那個時候你到歐洲去… 項武忠:歐洲人家請我去半年。較早時我們很生氣,寫信、五百學人上書蔣總統是我們去搞起來的。因為陳省身跟楊振寧名氣大他們頂了頭。又,開始的時候在立法院討論,立法委員說我們要聲明釣魚台是我們國土,可是過了一陣子之後,為了不要搞壞與日本人的關係不肯理了,這時的台灣、以後的北京都是如此。 台北的消息來自袁旂、劉志同在外交部做事的朋友把東西寄到外頭來的。開始的時候,立法院說要管這事情,不久就打壓掉了。那個時候為了外蒙古事情,為了聯合國席位的事情,吵得不可開交,錢復是管這件事情的。項武義前半年沒有參加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兩個都想回台灣。鬧釣運的時候他在台大。我去遊行那時候他在台大,知道這個消息以後,項武義去找錢思亮。因為錢思亮跟錢復住在一起,錢復是美洲司的司長。他們當場在錢思亮家裡就吵起來了。 李雅明:你說項武義跟錢復吵起來了? 項武忠:錢復在台大比我早一年,我們認識。他對項武義說:「你們懂什麼東西?你們學數學的人怎麼會懂這些東西?」兩個人就對吵起來了。 後來釣運起來後,他們就派了個姚舜來美安撫。姚舜也很可憐,他的官運一半喪在我手裏。這些官員都認為這些留學生能搞什麼東西呀?隨便打發一下,安撫一下,就沒有事了。他就先到了西雅圖,在西雅圖安撫的時候,把學生嚇死了。姚舜人滿好的,一路是關懷你、然後又威嚇你,把他們嚇死了。到芝加哥以後到紐約。 李雅明:後來到馬里蘭,到了DC。我接待的。 項武忠:那是後面,先到了芝加哥、紐約。所有的中國留學生被他嚇昏了,毫無辦法對付他。袁旂的爸爸是袁守謙,袁旂的爸爸是國民黨中常委。所以袁旂真是了不起,他參加這些事情,他的壓力你看看多大,獨子啊!結果袁旂打了個電話給我,那時候我們每個禮拜開會討論、唸書,我也不知道釣魚台在哪裡,出了事情,找到50年代聯合國調查報告講下面的油多少多少,我們不知真假,可是沒有道理再受日本人欺負。 李雅明:你怎麼認得袁旂的? 項武忠:袁旂跟項武義同年。 李雅明:因為他那時候在CCNY開始當助理教授。 項武忠:對,我們原來就是很熟的,還有一個原因,跟袁旂的太太更熟(按:袁旂夫人為謝渝秀)。袁旂太太的姊姊是沈君山的前妻,沈君山的前妻是我介紹的。所以沈君山前妻與袁旂太太基本上一直住在我前妻(ex-wife)家裡,等於是我岳父的乾女兒一樣,所以我和袁旂是因為這樣子更熟。 袁旂打電話:「我們需要你這個大砲,你趕快來,我們擋不住了,我們完全擋不住了。」所以那一次到了紐約大鬧,後來我看到別人的筆記,自己看了很難為情,那個時候我野蠻得不得了。我罵蔣介石是賣國賊,蔣經國是石敬塘。姚舜吃不消,後來他問:「這個是誰啊?什麼地方的學生?這麼野蠻。」結果旁人說:「He is a full professor of Yale university.」他一點辦法都沒有、完全被摧毀了。那個時候劉志同他也在場,他們從CCNY跑到Colombia,我們開會在Colombia吵得一塌糊塗。我有一個作用,平常研究生都很害怕,每個都覺得弄下來白色恐怖怎麼辦?因為我其實比他們大十歲。 李雅明:我是1943年,所以比你小八歲。 項武忠:我因為做教授早,我那時候也就35歲。這個吵起來以後,可是我不怕。所有能嚇唬你的,好像用棍子打你,棍子斷掉以後他就沒用了。鬧起來後,我家的信就到不了了。他們派了錢思亮和調查局局長到我家去。 李雅明:叫什麼名字? 項武忠:忘掉了。他們派了最大的官,因為我那時候很有名,所以不敢亂搞,而且我父親是政大教授,也是老國民黨。所以他派了人去看我父親,我父親像是從天上掉到地下。以前我每三年回來,人家捧了上天,突然之間就像坐牢那樣似的,家信都到不了。我父親也是對我一點辦法也沒有,他沒有辦法勸我,我想沒有任何人可以勸我的。後來一月那個遊行… 李雅明:一月三十號(按:1971年)。 項武忠:那時候有一兩千人。那時候根本沒有在做研究,天天搞讀書會。唸了很多很多書,真糟糕,因為共產黨比誰都會騙人。那個時候唸的東西,講的簡直像天堂一樣。因為我們以前都認為中共裡面這麼壞那麼壞,可是你發現他講的這麼好,這個時候對台灣不滿,所以人會受情緒的變動,一翻過去以後覺得他們是好的,他們的科學發展一定很好吧,又會做原子彈,又會放飛彈,一定不錯,所以你的心就變了。而且民族主義是非常危險的事情。我87年寫了一個懺悔錄,戴了有色眼鏡以後,你要看紅的你就戴紅的眼鏡,看綠的就戴綠的眼鏡。文章發表在《中國時報》,沈君山很得意,把我的這篇文章收到他的書裡當作附錄。因為我天天跟他吵架,所以他把他收在後頭。在那個時候我開始唸中文書,唸了很多很多,也去 研究他們的《毛語錄》,看了以後我還真的不相信他們。可是我覺得既然台灣這麼懦弱,我想人家中共能夠這樣子,我能夠犧牲我這一代,假如下一代日子好一點,他們在造烏托邦。不要用現在的眼光看文革,像我基本上是左派的想法。你想假如老百姓都能夠一起平等,工農兵能夠起來的話,我這一代犧牲沒有關係,下一代能過好日子。想的浪漫得不得了。那時我三十多歲了,想這個世界假如我犧牲我這一代,下一代可以好,那你覺得你好偉大,所以一頭就撞進去。而且我唸書唸的快得不得了,我知道很多很多歷史。 李雅明:能不能稍微提一下您那時候遊行後為了了解中共,唸了什麼樣的書? 項武忠:主要是研究中國,文革他們有很多消息過來,所以讀有關大陸的書多了。特別是我去看台灣寫的北京報告,裡面鬧的地方不看,只看他好的地方。所以說他們是很窮,可是好像很有朝氣,年輕人鬧起來都很有朝氣啊!所以我花很多時間,那時候中共跟印度為了西藏的問題跟印度吵架。 李雅明:1962年發生邊境戰爭。 項武忠:我就研究好多西藏他們打仗的問題。而且你看打韓戰的時候,中國人沒打敗過。 李雅明:打了平手。 項武忠:這種情況打的平手已經很了不起了。中國人第一次,中共對美國說:你不要打到鴨綠江,打到鴨綠江就要對付你,中共就過去了。所以中共講到一定做到,這對我而言太要緊了!這個時候心思就往這邊開了,你一旦往這邊轉就非常危險。 那個時候大家就要討論要去遊行,四月十號的遊行,到華盛頓DC來遊行。陳省身從加州想搬到Rockefeller Institute,還有王浩也在Rockefeller Institute,還有一個人叫陳幼石,後來變成王浩老婆的。她在王浩的辦公室召集了一個會,希望全城的人跟我們一起去遊行,大家組織起來怎麼樣。 陳省身講:他絕對不要去遊行。我們搞了半天,我就怒了。他那時60歲,過一陣子就要過60歲生日。我說:「你不遊行,你的生日我不會來了。」說完了以後我就去了德國做訪問教授,做visiting professor at Max Planck Institute。去的時候大家就開始捐錢。 李雅明:這是在四十的遊行之後嗎? 項武忠:之前,同時我們在這之前還在紐約時報登了一頁廣告。捐了一萬八千塊錢買了一頁八千塊錢的廣告。那個時候的coordinators第一個就是我,可是當時我人不在美國,我在德國。 李雅明:你剛剛不是提到,捐了一萬八千塊,但只用了八千塊是不是? 項武忠:後來為了那個一萬塊問題多了,我待會再告訴你。你捐了錢,心就在那裏了,雖然只捐了二十五塊。參加的都是研究生,那個時候全美國的中國研究生都聯合在一起了,天天開會,書都不唸了,整天搞在一起,搞在一起就討論登報。所以一個研究生他捐了十塊、二十塊,我們也沒有人捐更多了,捐二十五塊最多了。連大教授陳省身跟楊振寧一個人也只捐二十五塊。後來就買了個報紙廣告,上千人具名連署,這份廣告在樓下有啊(按:「一九七0年代保釣運動文獻編印與解讀」文獻展,自2009年4月27日至5月10日在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一樓展出),整個通訊網都是從《科學月刊》來的,要不然我們沒有這個辦法。都是來自各個不同學校的研究生。錢捐過來以後收集,由紐約保釣會管。我說我可以想辦法找錢,我不要 管錢。這個時候,每天夜裡我不知道花多少錢打長途電話。在波昂(Bonn)打長途電話你要到電信局去打,時間相差要半夜。 李雅明:從歐洲打電話回來? 項武忠:對,貴得不得了。那個時候整天打電話回來討論。所以我那個時候做訪問教授,早上做研究,晚上做了一半以後去打電話。到四月十號回來遊行,報紙登了以後,搞到這個地步,白色恐怖就來了。愛盟這幫人真是害死人,認為這樣可以打壓人家,他們也知道我家裡被人家這樣搞,像袁旂,他爸爸是國民黨中常委,謝定裕的爸爸謝冠生是司法院院長,國民黨他們想:「這些吃我們奶水長大的人怎麼會搞到這個地步,我們哪裡虧待你了?謝冠生的兒子、袁守謙的兒子、你項武忠我們這麼捧你,怎麼搞反叛了。」可是我們不能忍受政府軟弱,而且他們是用白色恐怖的方式。他們現在最近釣魚台不許出海,是最愚蠢的事情。越壓抑,將來人家炸起來就越發火。他們以為愛盟幫了忙,這是倒忙。可是話講回來,釣魚台 運動裡面我講的是海外的一部分,海外還有另外一部分成分非常左的、認為文革是完全好的,就是廖約克他們、胡比樂。胡比樂就是余珍珠的老公。 李雅明:廖約克是在哈佛(Harvard)唸物理嗎?他當初還是個學生嗎? 項武忠:都是學生。所以今天我們講了半天的時間,你要注意到,林孝信在會中提倡大家要做社工,那時候廖約克他們都到中國城去做社工。而你不曉得哈佛燕京裡面有多少左派的書、雜誌。我有陣子去看,那裡面很多很多的小說,是抗戰時候的小說、毛邊紙爛掉的小說,那個都是講民族氣節的事情,故事寫得讓人熱血奔騰啊!他們常常到中國城去做事,行事也跟我們今天一樣,要往下走做社會服務。這風氣是最近又回來的,前十幾年大家都是認為搞錢就好、富裕就好。這風氣現在又回來了、又開始左派了。事實上林孝信其實非常左派,做這樣的事情,草根運動(grass root)的工作,左派得不得了。那時候大家都開始往這樣想:有學位又怎麼樣、拿錢多又怎麼樣?要緊的是做人!大家有這個想法,認為這樣做簡直高尚得不得了。後來到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談判的時候,要他們硬一點,他們完全不理。 李雅明:我記得四十遊行的時候你是不是也是演講者之一嗎? 項武忠:對。 李雅明:能不能講一些細節?為什麼呢?因為當時我是在華府負責保釣會,可是那個時候四十的遊行主要是由紐約保釣會七人小組在掌控。有些細節您能不能說一下。 項武忠:我記不太清楚了,我知道的是這樣子。因為我是在國務院前面演講,我是用英文演講,還有用中文演講的。余珍珠是英文演講,送抗議書去國務院的是錢致榕,大家分批去的。我們由Yale開了幾十輛車子去華盛頓DC遊行,總共大概四千人的樣子。西雅圖的張智北還把婚禮改期飛過來。那個時候每個人寫文章罵,你看《戰報》的粗野,你不能想像,那是劉大任他們。 李雅明:對,劉大任、郭松棻搞的。 項武忠:各個地方寫的東西,那天遊行我記得有人到日本大使館去演講,還有中國大使館去演講,四、五個人演講。 李雅明:我們不是派代表進大使館了嗎? 項武忠:大使館有秘書見,可是日本人根本不理我們,不見啊!日本人把抗議書撕了放在字紙簍,根本沒有理我們。這個時候,大家愈來愈生氣,你知道那天夜裡遊行完了就到了馬里蘭。 李雅明:我知道,我是負責接待的。 項武忠:大家那時講要組黨。 李雅明:剛開始說要組全美聯絡中心,後來好像也沒通過,李我焱也不肯接。 項武忠:開始的時候,所謂的左右派還滿和合的,大家都一起。《戰報》他們在搞,劉大任進來像英雄一樣的,這一搞以後問題大了,開始分裂,還沒有真正分裂。你們假如將來要搞運動也一樣,不進則退。要搞這種運動都非常非常危險,到最後像美國的運動一樣,我們的一個大數學家那個時候反越戰講了一句話:「現在非死個人,不死我們就完了。」你的運動到某個地步,非死人不可,不死就完蛋了。施明德那個(指紅衫軍)你們去了沒有?到了他走兩三次以後,你沒有真的暴力,這是好處、這了不起,可是一定完了。運動像氣球一樣,吹了一個大氣球,一個針一插,破了以後絕對無希望。四月遊行以後到布朗大學開會。(未完, 待續, 謝謝!) |
|
| ( 在地生活|北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