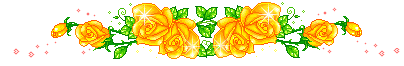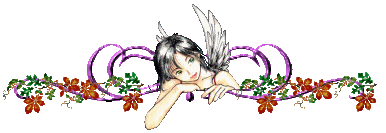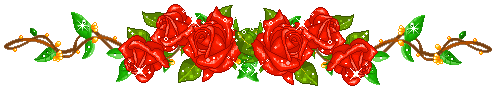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3/05/08 09:01:24瀏覽1707|回應1|推薦0 | |
保釣大將項武忠和他的狀元夫人郭譽珮(3)
李雅明 教授 Joseph Ya-Ming Lee, Ph. D. Physic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USA, 1972 (美國馬里蘭大學物理博士)
• 釣運的左右分裂 李雅明:對,布朗大學開會是八月二十一、二十二號(按:1971年)。 項武忠:謝定裕他們組織在Brown開會。Brown開會的時候,基本上很左派了。 李雅明:就已經吵得很兇了。 項武忠:已經分開了。所以魏鏞他們來了。沈君山那個時候沒有參加? 李雅明:因為我第一次去是去Princeton所以我比你晚大概一年。 (註:大風社在Princeton開會,大約比在Morgan Town開會晚一年) 李雅明:對,他沒去。 項武忠:魏鏞來了。那時候我剛剛由歐洲回Yale,我帶了我的兒子、老婆開車到布朗去開會。開會的時候我們也輪著做主席,吵啊鬧啊。那天半夜我就被叫去聽電話。那時候沒有手機,所以打電話要到哪個辦公室或哪個家裡。項武義打電話來,我說:幹嘛?項武義講:「你明天小心,我剛剛做了一個夢,你一身血。」因為那個時候我太引人注意,我想這事情不會發生的。我也有另外一個好朋友,他跑到華盛頓DC的大使館,也打個電話給我,說他們下令暗殺我。國民黨做事是認為搞掉一個人就好,認為我太引人注目了,又粗魯。這些地方加起來,我恨他們把白色恐怖搞到這個地步,過火了。他們一直認為我們受中共的控制,根本沒有那回事。我想廖約克他們可能跟中共有點聯絡,我後來跑去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去跟他們談 的時候,他們搞文革搞昏了頭了,釣魚台是什麼都不知道。所以國民黨在台北跟共產黨在北京都完全落後太多了,我們夾在裡面莫名奇妙,自己糊裡糊塗搞出來的問題。這是江南事件發生以前很久的事,他們(國民黨)認為搞掉一個人又怎麼樣?他們以前在大陸一天到晚幹這事,所以他們就想到這個。你要這樣嚇唬我,嚇唬不了的,我愈來愈火。布朗完了以後又在安娜堡(Ann Arbor)。 李雅明:對,九月三號到九月五號。 項武忠:我們開車去的,兩邊都不正派,我們這一邊和所謂的愛盟都做了一些鬼事。 李雅明: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我那個時候算是自由派,所以我兩邊都沒有參加,當然也不會去參加他們事前的討論。你們左派有沒有事前討論? 項武忠:我沒有,他們不相信我。現在我發現,他們不相信我,因為我是過於體制內的人了(too much an establishment),可是他們想利用我。我事後想,我那篇懺悔文章上沒有提到那麼仔細的細節,你問得太好了。所以他們講,唱秧歌,跳秧歌,這不對的。我想那天大家很高昂,唱了「東方紅」,可是沒有跳。 李雅明:不是每個人都要跳,我去我也沒跳,我也沒唱「東方紅」。有人唱「東方紅」,可是不是強迫每個人都唱「東方紅」。 項武忠:那個時候大家在那辯論,我跟沈君山辯論,開始吵啊鬧。第二天他們夜裡開會,曉得劉志同他們來了,也不曉得派多少人。 李雅明:三、四十個。 項武忠:來了之前,討論的時候李我焱他們想怎麼對付愛盟,我沒有參加。開會的時候,兩邊都各個地方混在角落裡面,對吵對叫。在開會的時候,我今天坦然提起,那個時候李我焱他們胡鬧到什麼地步呢?第一天我做主席,最後一天應該是他做主席,要通過一個決議。李我焱跑來找我。他們商量好了,他想我這個大嘴巴,聲音又大,很容易被激怒。他說:「我喉嚨壞掉了,我今天跟你做共同主席,你陪我上去。」我就上去了。一上去以後他就往後面一退,就坐在椅子上,讓我一個人來處理。所以沈君山他跑來了討論大陸人民的營養每天有多少卡路里的問題,叫了半天。我就跟他對辯,又吵起來,所以李我焱他們要通過五條,我都忘了前面四條了。 李雅明:不可以有兩個中國、中國領土不可分裂、不接受一中一台,最後一條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項武忠:我事先跟他們為這件事情有過很大的爭執,我非常猶豫,我說這事情我不能做。可是沈君山一鬧一吵把我惹火了以後,「啪!」就通過了。這一條在我手上通過的,所以國民黨吊銷我的護照、要通緝我,完全合理。因為畢竟我做主席把這條通過,在我手上通過的。所以我那篇懺悔文章寫說他們講革新保台,事實上是對的。我搞昏了頭,做了這件事情。通過了以後,國民黨簡直不能原諒我。 李雅明:稍微打個岔,我聽說,有人說因為那年中共要進聯合國,所以中共從加拿大的使館好像透過李我焱、廖約克他們,最好能夠在國是會議裡面通過支持中共加入聯合國決議案。 項武忠: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我相信他們是對的。這件事情完了以後,事實上71年年底,什麼時候楊振寧去大陸? 項武忠:那是後來,他一回來的時候,他們就知道,這個時候他們要去看楊振寧,楊振寧其實很右派的。要看楊振寧願意回中國如何如何。那時我已經搬到普林斯頓,很投入釣運,根本沒做什麼研究。他們打電話來叫我去約楊振寧,所以我們開了幾個車去跟楊振寧討論他到中國旅遊的觀感如何。他們到加拿大拿了五張空白的入境證,在車上一路上不肯講他們那裡來那五張,就說:「我們一起到中國去看看。」就是要把我拖進去,因為那時候已經通過了那五條,所以那時候已經跟他們有聯絡,沒話說了。那時候中共還沒進聯合國,他們到了加拿大拿到那五張空白的入境證。他們在加拿大,是不是中共有指令我不知道,可是他們很想把我弄到中國去,本來那五個人裡面當中有一個是我,因為我在他們裡面地位最高,所以 叫他們把我拖去,我就一直沒答應。開到楊振寧辦公室,跟楊振寧談,楊振寧簡直是把中國講的好得不得了。舉例講:中國的環保好到什麼地步?煉油廠煉油,煉完的水都可以養金魚;所有的人,包括大教授都去作工,工農兵跟教授都在一起,好得不得了,講的天花亂墜。是我手寫的筆記,他講的興奮的不得了,簡直活像我們中國人造了烏托邦,講得好的不得了,還有說蘇州河已經清了。我在上海住過,不可能把蘇州河清了,清了蘇州河那簡直是上帝了。後來我80年去,蘇州河根本沒清。 李雅明:楊振寧他的岳父是杜聿明,你也曉得,他的原來立場會那麼左嗎? 項武忠:沒有! 李雅明:他什麼時候變得那麼左的? 項武忠:楊振寧是很精明的,他左的原因是希望中國好。早期中國接近楊振寧被拒絕,後來他講72年第一次看到他爸爸(按:指中共佔據大陸之後第一次),其實他57年就看到他爸爸了。中共把他的爸爸送到Geneva,想把他拉回去,他不去,他要在美國。到72年的時候因為他爸爸年紀大了,他想回去看一看,這是可以想像到的,去了以後人家想盡辦法招呼他。你知道中共招呼他的情況簡直荒唐得不得了。所有的報紙,他們內部的報紙全部知道他跑那去,所以到了上海燒餅店裡面吃早餐,他為了裝假,不讓中國人知道,穿個布鞋不穿皮鞋,去了坐下來吃了以後發現坐著幾個很漂亮的女孩子高談闊論世界大事,我們中國人多好多好,怎麼樣幫第三世界忙…多好多好。講了半天以後楊振寧越聽越起勁,他自我介紹:「我是楊振 寧。」回來以後就告訴我內部事情,中國的工人有這樣的水準,我們到哪去找啊?簡直把他講上天了。所以我記了筆記,就是他在那個時候自己想要回到中國,他認為他可以幫中國人做點事情。他以前非常右派,事實上他現在想法也是非常右派,他是很自我中心的。 那個時候天天開會,左右打架打得要死,劉志同就在外頭打架。我的筆記被李我焱拿去複印,複印散了全美國都是,每個地方都散滿了。楊振寧講的金言玉語、項武忠的筆記,那你還有什麼可以講的?所以影響所有的學生。這一散楊振寧怒極了,他怕FBI來找他,他雖然去了做了briefing,他事實上小心得很。他回來以後打電話給國務院,告訴他們說「我去過中國回來了」。尼克森那時候還沒去,他告訴美國人他那邊怎麼樣,所以他可能已經有contribution在這裡。他打電話給我,說「項武忠!你把我跟你講的話全部記的散了一地」,大罵了我一頓。這個事情以後就愈來愈騎虎難下了,人就相信這個東西。 接著我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為什麼,第一點:我在歐洲時去跟巴黎中國大使館談一談以後,發現他們完全不曉得釣魚台幹嘛的。這天上掉下來的,怎麼台灣所有留學生一下子左傾起來了,他們也不曉得怎麼處理。 我為什麼懷疑呢?因為在那個時候,日本的首相田中角榮去了中國以後跟周恩來談,周說不要談釣魚台的事情,擱置起來,我們將來再談。我就很火了,中國又把田中住的地方安排在釣魚台賓館,你什麼地方不可以住讓他住釣魚台賓館,我就很生氣,我跑到聯合國跟他們爭,講了半天。後來我問了他們一個問題,我說:你們怎麼看林彪?林彪林副主席多好多好,他過了一個月死掉了,現在講他怎麼壞,這怎麼回事?那個時候美國要找我帶科學院的人去中國,我說我不要去。可是我幫我這些朋友找到了簽證,那個時候中共已經進聯合國了。 簽証的時候FBI注意了,馬上到我家來,問那天你的車停哪?我停在中國聯合國辦事處附近ABC那個電台的地下停車場,問他「你怎麼知道?」「那你就不要管了」。他說:「你是不是要回中國去?你是不是跟錢學森一樣要回去?」我說:「第一點:我回不回去是我的事,我不必告訴你,我大概不會回去。」因為我沒有決定,還沒看懂,為什麼?因為我去跟黃華他們談的時候,一個月之內就把林彪從天上丟到地下。這太可怕了!怎麼搞的,最高的副主席一下子就死掉了還變成混蛋,這太可怕了。我說我不要去。項武義就帶了一幫人西部的教授去中國。 李雅明:大概記得是1972年嗎?還是1971。 項武忠:72年。去了以後,項武義回來跟我打電話,我說:「不對、不對、問題多了。」一跟我講,跟我寫的楊振寧筆記走的路完全一樣。因為我是粗中有細,我一聽,我說:「你走的就是中朝公社嘛!」看見這麼漂亮的地方搞了半天,就這個公社嘛!你去的油廠基本上一條路嘛!這是餵你的嘛!這裡頭造假太多,所以我一直沒回去。所以這一邊國民黨把我家裡搞的天昏地黑了,但同時我對中共起了極大的懷疑。 左右分了以後,多了一萬塊錢,那一萬塊錢他們就吵這錢要拿回來用,分給花俊雄、程君復他們,要用來對付台灣、要做統一。我就跟他們吵起來了,這不可以的!這強姦民意。當時我們參加的有左有右,右邊也捐了錢,這個錢一定要還給他,你怎麼把人家錢拿來用,雖然只有幾塊錢的事情,二十塊錢,要還人公道嘛!所以這個就掉在我身上,慘了。他們說,好吧,那你去還。我不碰錢的,我告訴你名單找到以後你幫忙寄出去。這個糟糕了,因為暑假過了一陣子以後全部研究生從A搬到B,全部亂掉了,太難找了。 這裡面我覺得對楊振寧跟陳省身怒極了,他們要把剩下的錢要回去。譬如說捐了二十五塊,用掉十塊,要我寄十五塊回去給他們。爲什麼?那時候台灣把這種黑名單的東西交給了美國的FBI,他們知道。我們被約談,也可能去找他們。所以楊振寧他們要在政治上跟我們割清,要把錢要回去。錢大概只有發回去兩、三千塊,後來那個錢一直出大問題。不知道怎麼用掉了? 我那個時候發現左派的人已經對右派不公平,我說我不要再幹了。可是我那個時候還做了一些事,因為他們沒有工作沒有錢,沒有辦法找到工作。研究生全部糟糕得不得了。開了個東風書店,他們有些人像劉大任他們都進了聯合國。我說:「你們進聯合國這個事情也不太對啊,你們怎麼拿中共的錢了?」我說你們要開個書店我倒也贊成,所以東風書店最大的股東是我,而且無息的,用了好久。結果我說:「你們天天開會吵架,我已經不行了,已經搞兩年了,你們愈來愈亂了。」所以我回來做我的數學了。他們吵架吵太多了,整天開會,幾千人的在開,《群報》、阿花他們吵太多了。 李雅明:那個時候不是徐守騰鬧一個自白書,窩裡反,你知道不知道? 項武忠:完全不知道。我說你們怎麼鬧翻了。因為還有一個事情,因為William Hinton 寫《翻身》那個人。你去看寫的《翻身》,他們八股到這個地步,整天講四人幫,我怎麼受得了?我不能忍受。然後沈平跟余珍珠她老公吵架。 李雅明:余珍珠的老公是? 項武忠:胡比樂,沈平是另外一個人。他們吵架整天就講中共多好多好。讀書會,我們跟研究生一起唸書。結果我發現一樣事情,我們看了個電影叫做「紅旗渠」你看過嗎? 李雅明:我看過,我都看。 項武忠:我說:這我覺得太假了。怎麼可能有電影機,他們說這是完全紀錄片,中國你看多好,把石頭搬了以後運到大寨,我說這有問題,講這是紀錄片絕對是不對的,絕對不對。窮到這個地步,山上打開要種水稻,多麼困難,每個人都背個東西,居然一個攝影機在等待你,你不是造假是什麼呢?為這個事情和沈平他們吵架,他說:你是做教授的,所以你這個人一定是中毒太深,就大罵我。 李雅明:你跟沈平也吵?沈平那時候在幹嘛?沈平是香港來的對不對? 項武忠:不,沈平是台灣來的。 李雅明:他們怎麼跟我說是香港來的呢? 項武忠:現在在香港做教授。他曾在Exxon做事,研究生時唸物理的。沈平不是壞人,他們都不是壞人,問題是相信這些東西。這個時候我開始愈來愈多懷疑,我是個教授,整天下來跟你們唸這些東西,那沒關係,我認為我應該平等。可是整天吵,我不能相信啊,我已經開始不能相信了。我說尤其毛澤東的批判,他批判三家村有些問題。我想他沒有批判以前,我看不出毛病,批判以後他講的也有道理,但是我不能受人家這樣控制。所以後來唸了幾個月以後就停止了。後來他們在紐約吵得一塌糊塗。 我發現鬧得太厲害了,我要離開了,我請他們把借給他們的錢拿回來,一萬塊兩萬塊錢的事情,也不少,一棟房子大概三萬塊錢的樣子。他說我沒這個錢,這個錢我沒辦法還你。 當時挖掘出有些唐朝骨董金碗,中共作了八個仿造的金碗,他們跑來拿給我,說要拿金碗抵這個錢。當時我因為在普林斯頓買一個房子,那個時候大概兩萬五千塊錢、三萬塊錢一個房子,結果我買了一個八萬塊錢的房子。那個時候馬英九他們在波士頓(Boston)天天寫文章罵我,叫我「項八萬」。那個時候八萬塊的房子就跟現在的兩、三百萬塊錢的樣子,比別人貴。罵我說你這些走資派的,我說我拿個金碗擺家裡不就死掉了,我絕對不能要這個玩意兒。(未完, 待續, 謝謝!)
|
|
| ( 在地生活|北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