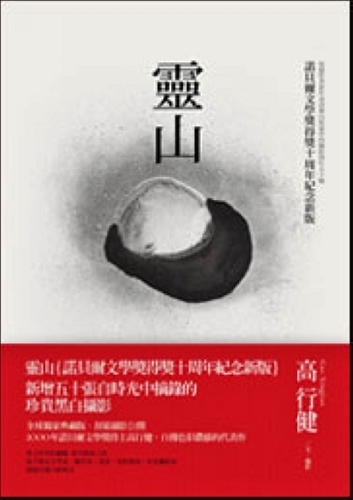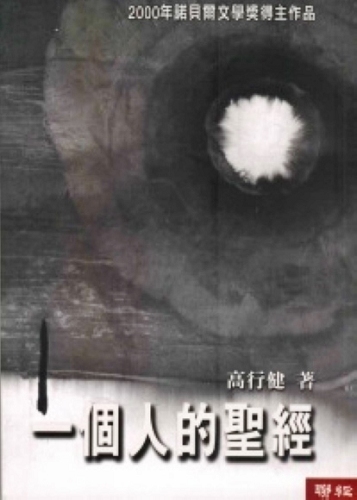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1/11/28 11:04:01瀏覽5768|回應11|推薦156 | |
普濟:《五燈會元》卷第九,問:如何是自己?慧清禪師曰:望南看北斗。威爾斯(H.G.Wells)說過:「一個人的傳記應該由一個誠實的敵人來寫。」,解答了我的疑問:「為何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不自己寫自傳?」 本書並非刻板地依坊間紀實性傳記寫法,書中包含三種境像,形成對話與反詰:高行健的文學敘事,作者的話語及高行健親友的追憶,不乏闡釋及批判的說文解義,形成三重對話結構,是一種新的傳記文體,讀來即使並未實地讀過高行健作品,依然可透過作者輕盈絕美的散文、古詩和禪語的空靈意境對高行健作品的創作元素和內涵底蘊有更深層的體驗,令人浸淫在文學之美渾然忘我,是一本鑽研高行健作品不容錯過的極品,好書值得再三品味。
(左: 作者沈衛威與高行健2010東京相聚) 2011年2月,立緒文化事業初版,作者沈衛威先生,現任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全書長達378頁。作者第一次讀高行健作品,是1982年《絕對信號》《現代小說技巧初探》,直到《靈山》才真正一窺高行健的寫作全貌,就《靈山》目前已閱讀第五次。2006年在韓國外國語大學執教時,全面閱讀高行健的所有研究著作,與韓國學者共同指導來自台灣的高行健碩士研究生,之後在南京也指導過博士生。2009年開講高行健的小說和「高行健研究」的選修課。這幾年並與高行健的親屬、美術啟蒙老師有多次接觸,深入實地查訪,將談話內容融入書中,增添傳記的真實性。
翻開作者的著作赫然發現早期對胡適也有相當研究,難怪書中盡是行雲流水的白話文,不見咬文嚼字,更嗅不出任何中國慣用語彙,一度誤以為出自台灣作家之手。秉持英國名傳記作家里敦.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的忠告:「傳記作家的第一個責任是簡潔,第二是保有自己的自由精神。」,除了旁徵博引高行健作品經典佳句,同時融入自己多年習禪的領悟並與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詩學關聯做比對呼應。如作者書中所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司馬遷語),「掬水月在手,弄花衣滿香。」(于良史詩)。心中盈滿靈山路上的寂靜之音,沉澱浮躁的心情,如入無我之境,從而感受高行健作品和禪學文獻的崇高意境,所謂「君心若似我,還得到其中。」(寒山詩)。
(左:高行素,中:母親,右:高行健) 寫作和繪畫都是高行健從小的興趣,習慣已養成,很難離開。「藝術家不拯救世界,只完成他自己,他把感受、想像、白日夢、自戀和自虐,以及未能滿足的慾望與焦慮,實現在他的藝術創作中。」藝術家不是代言人,也不是救世主,只是審美和創造美的脆弱的個人。藝術有自在才會有自我,有自我才會有思想,有思想才可能不是風中的蘆葦。 作家因脆弱而顯示本性,因意識到自己的脆弱而找到自我,對自我的重新認識和自悟中超越內心,即是解脫。高行健說:所謂作家,無非是一個人自己在說話,也可說是把語言當成一種行為,只面對語言的現實。自言自語,在語言的世界裡獨自流浪。作家首先必須感受到寫作的必要,有一種內心的需要,且因這樣強大、頑強的需要使得你義無反顧。
高行健說:「用小說編寫故事作為小說發展歷史上的時代早已結束,用小說刻畫人物或塑造性格現今也已陳舊。就連對環境的描寫如果不代之以新鮮的敘述方式,同樣令人乏味。」。他把「故事」和「人物」淡化,追求「語言」本身。認為:「小說這門語言的藝術歸根結柢是語言的實現,而非對現實的摹寫,小說之所以有趣,因為語言居然也能喚起讀者真切的感受。」,作家的關注和傾聽是潛心的內視並傾聽內心正在說出的聲音。正如同許多人說語言,但不是文學,更不是小說。只是實現語言作為交流工具的基本功能。
(左: 作者與 右: 高行健弟弟高行素攝於2007年) 高行健曾歷經文革被下放,文中常嘆自己是一個脆弱的人,一個孤獨的行者,寂寞行走在文學的長河裡,意識到流亡才是唯一的出路,後流亡法國。「只有在逃亡時才感到我活著,才得到言而無忌的自由。逃亡也是我們寫作的目的。寫作可以逃逸到更深的感受中。」,從貧乏的現實逃到想像中,進而獲得自我充實。 曾被誤診罹患肺癌,彷彿死裡逃生,對生命有了更深的體認,決心要換一種活法面對人生。是這種精神的超渡孕育了《靈山》,成就了直通諾貝爾明心見性之路,映證了「飄如遊雲,矯若驚龍。」奇蹟中的奇蹟。曾說:「藝術家總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路,等他終於走過了漫長的一段,便又發現前面依然無限幽深,如果不就此卻步,還得再走下去,就有所領悟。」,「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王維詩)。
(左: 兒子高杭, 右: 繪畫老師惲宗瀛)
(1991年高杭繪 <清涼山的掃葉樓>) 與前妻離婚,兒子高杭是前妻一手帶大,在前妻眼裡高行健是一個對婚姻不負責任的丈夫,想到婚前歷經十二年愛情長跑和家庭、外力反對才結婚,卻輕言放棄,心中埋怨可想而知。如今兒子已成人,回憶兒時害怕父母離異的一段話令我啼笑皆非:「小時候的記憶太深刻了,老是覺得父母吵架,是因為我不夠好。有一次繪畫在日本得獎了,拿給他們看,結果,還是離了。」。父子倆都拜惲宗瀛先生為師習畫,看見父親的畫卻驚呼連連:「畫和人不一樣,真是判若兩人。人那麼外向,開朗、熱情,有時候像個外交家。這畫都是無言、無象,潑墨的,黑暗的,冷色調的,就是他所謂的冷吧!」,高行健冷的文學和冷的繪畫,來自冷的理性,像無光的冷月,或被黑墨映襯為寂靜的冷色。畫境即心境,這正是思想和藝術的穿透力。
作者說存在愛情與友情之間還有一種東西叫曖昧,積極和消極之間還有一種東西叫無聊。曖昧、無聊這兩個詞,最難用語言說清楚。其內在的涵意也許就在說不清楚之中。說不清楚和想說清楚本身就是一種狀態。想弄明白這種狀態,就又陷入無聊之中。高行健在《夜遊神》中的夢想者有一段說詞:「這是一個無聊的世界。你思想,無非你自虐。你同樣無聊,你也深深知道,你知道你已經不可救藥!」發現無聊、感覺到無聊和承認無聊,是現代都市生活,特別是精神陷入困境的知識份子的一種常態。是反抗、介入主流意識形態和合謀、共存主流意識形態的兩類知識份子之外的另類狀態。無聊的自覺與虛無的清醒,共同交織在這種生存狀態中。「走哪算哪」是最自我、最自在的處境。「溪花與禪意,相對亦忘言。」(劉長卿詩)
您曾探討過文學和藝術的價值嗎?高行健認為「表現人性,見證人性」,身為作家、藝術家之所以活得更人性,是在藝術創造中,保存和實現個人的獨立。盡可能真實地呈現大千世界和人類生存困境,及自身種種困惑,超越政治的侷限,超越是非倫理。對他來說文學是非發洩不可的苦難記憶,是自我滿足,超越生存、性等欲望的本能衝動。在充滿意識形態的時代,他希望文學與政治保持距離,進而凸顯人性。因為他堅信只有文學才能說出政治不能說的或說不出的生存真相。說:「卡夫卡出現之後,作家如果還只有浪漫激情,就顯得膚淺。」
「寫作是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靈山》是為我自己寫的。」,高行健因《靈山》獲諾貝爾文學獎,其實是一本逃亡的書,一段靈魂漫遊的歷史記憶,一串串優美、原生的歌謠,一幅幅自然壯美的山水畫,融合自然、人文、歷史、考古、民俗、宗教等多種元素重疊拼貼的藝術,兼具小說與戲劇氛圍,除了歌詠真實的自然之美和自我自在,進一步呈現生命、生存、虛幻、陌生和疏離交織與互文性的多處滲透,「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在《沒有主義》一文中提到:「我把文學創作作為個人生存對社會的一種挑戰,那怕這種挑戰其實微不足道,畢竟是一種姿態。」脆弱的個人,一個作家,孑然一身,面對社會,發出自己的聲音,我以為這才是文學的本質。 這幾年高行健從戲劇轉向電影,親自執導了兩部電影:《側影或影子》《洪荒之後》,高行健把這種實驗和創作稱為「電影詩」。談到另外兩部片原來有法國和德國製片商有興趣,最後放棄,因為歐洲人還是想看有中國元素的電影現實主義的東西,無法接受那種沒有對白,用大量空鏡頭等等。他認為電影應是一種三元藝術,包括語言,聲音和畫面。現在一般認為電影是視覺和聽覺的二元藝術。如果可以像寫詩一樣拍電影,電影不再是複寫現實的,它是虛構的藝術,就像詩般自由,可能性就變得很大。
從本書可以了解到高行健原創精神、動力與內涵,追求獨立自由,描寫人性,至而空靈、寂靜、禪意的揮灑,融合文學、繪畫、戲劇、電影,多元創新,追求一個平靜的內心,迎接廣大無設限的創意空間,給我深刻的衝擊和莫大啟發,頻頻回首與深思,日後當親自賞讀更多高行健先生作品以體驗個中滋味。
我需要一個可以交談的對手,而寫作是我唯一可以做這種對話的手段。 ~高行健 作者簡介 沈衛威 高行健年表 ‧ 1940年1月4日,出生於江西贛州,父親高運同曾是銀行行員,母親顧家騮,曾服務南京腦科醫院公職。1941年弟弟高行素出生,其後成為音樂教育家。1950年高行健全家搬到南京。 高行健著作
‧ 《靈山》長篇小說,1990年,台灣聯經出版社出版 註: (1) 高行健先生年表和著作引用維基百科. |
|
| ( 創作|文學賞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