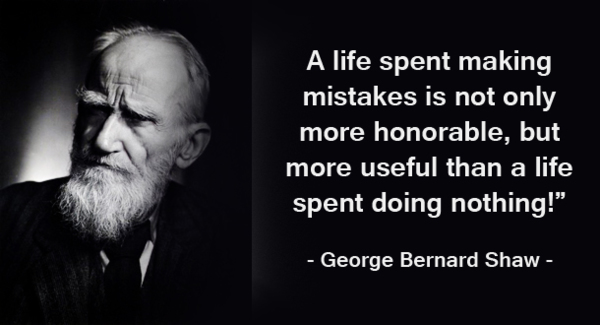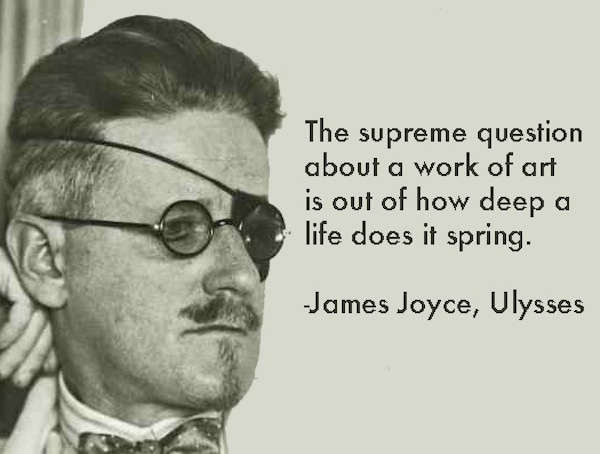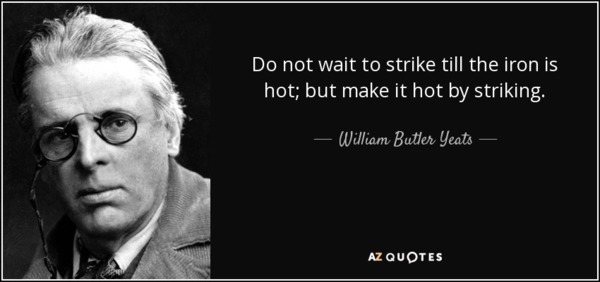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5/07/16 18:51:00瀏覽2970|回應14|推薦190 | |
愛爾蘭的心一無所有,除了想像 ˙蕭伯納
年輕時,愛爾蘭歌手 U2 與恩雅那響徹世界,穿透人心的歌聲與魅惑讓我一直對這個陌生國度產生莫名的好感。恩雅在歌中唱著:
誰能說你的愛(好感)是否滋長 ……… 請攜我上波浪 到我從沒去看過的地方 Carry me on the waves to the lands I’ve never seen.
存在多年的好奇心直到在愛爾蘭任職的女兒邀我去都柏林一起度長假,才能趁機掀開面紗一睹其廬山真面目。
曾被英國長期統治過的「翡翠之島」在我心裡一直是謎樣的國家,除了產生過包括甘迺迪在內的二十幾位愛爾蘭裔美國總統外,本身從「歐洲乞丐」到「歐盟模範生」再到「塞爾特之虎」也是一部傳奇的故事。不可否認,之前的印象有受到蕭伯納那句話的影響:「愛爾蘭這個地方不可避免的事從未發生,但預料不到的事卻經常出現。」出發前後歐洲正好發生幾件重大的公投案:愛爾蘭的同性婚姻公投、蘇格蘭的獨立公投與希臘的紓困公投。瞧!人家是為政治的獨立與經濟的危機而傾全國之力上街嘶聲吶喊,愛爾蘭人則是為同性戀的芝麻蒜皮問題而上街敲鑼打鼓兼吹號,我心頭也跟著打著鑼鼓,終於響(想)通了,原來英國俗語裡的「Irish bull」是其來有自的。可是,當親臨斯土親炙一些文人事蹟後,我又另有深刻的想法。
一八五四年出生於都柏林的王爾德,處處展現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語言機鋒,讓我想到魏晉時代口吐玄言、瀟灑不群的嵇康,兩位不但對現實高視闊步的輕蔑,回過頭又以嘻笑怒罵來反社會的偽善和庸俗,都是高呼人格大解放,為反抗而存在的狂生閒士,所不同的是王爾德犯了當時社會所不容的同性戀「罪行」而遭拘禁審判。他面對法庭為自己辯解那世人不敢說出的同性之愛,應如同在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裡才找得到的愛,是一種精緻、美麗、高貴的形式,但此心靈之愛在本世紀卻被誤解了,徒令如此高雅的同志之愛成為眾人的笑柄!他的滔滔雄辯被認為是詭奇之辯反而被判苦役兩年,以致銳氣盡銷而無立錐之地,此審判成為英國司法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案件之一,也是同性戀平權運動史上被引用最多的案例。 1900年他以四十六歲英年客死於巴黎左岸。他那膾炙人口的「終生的愛情與短暫的迷戀,唯一的差別在於迷戀比較持久。」且不論同性之間的「愛戀」到底是愛情還是迷戀,讓我感受到在大街小巷裡為同性戀是否合法而聲嘶力竭甚至吵到要訴諸公投,不也應證了他嘲諷的「我們都在陰溝裡,但仍有人仰望星空。」Irish young bull 為這一般世人都「預料不到的事」而奮鬥不懈,好像極力要把這位「愛爾蘭才子」從陰溝裡翻身,討回一百年前的公道!(與他同時代的「詩人會社」創始人之一 強森 Lionel Johnson 也有斷袖之癖,享年僅得三十五)。
還有一個不出世的文學怪胎喬伊斯,對語文的運用,常會在生活中將挫敗與絕望藉著藝術表達自戀或自憐而達到一種出陳入新效果,他專注於表現內心深處的火花掠過大腦時隱約傳遞出無數資訊的「意識流」,常獨處在書房中安靜的描繪那單純又難以捉摸的瞬間訊息,這是「唯一允許自己使用的防衛武器:沉默、流亡與狡猾。」他的文字艱澀難懂,曾被視為文學界的叛徒,連他的妻子諾拉也惱火地斥責道:「你就不能寫一點別人看得懂的東西嗎?」《尤利西斯》於1922年出版後命運多舛,在英美的英語世界到處遭禁,當時在劍橋留學的徐志摩曾讀到了這部禁書,並以詩人特有的激情奔放的語言稱讚該書「像牛酪一樣潤滑,像教堂裏石壇一樣光澄,像一大匹白羅披泄,像一大卷瀑布倒掛,絲毫不露痕跡,真大手筆!」英雄果真能以慧眼視英雄。
喬伊斯一生憎恨其出生地都柏林充滿了麻木與令人窒息的 Philistine 氛圍,說過「我不會服務不再相信的家鄉、祖國或教堂,我將在生活與藝術形式中,盡我所能的全面自由。」果其然,他一生自我放逐在 歐洲大陸且處處無家處處家,可是創作的小說裡卻清一色以都柏林人為主角,文學舞台則全以都柏林為背景。現實上,都柏林對他雖有避之惟恐不及的厭離感,但心靈上,羈旅的鄉愁卻仍舊有剪不斷,理還亂的牽絆!
愛爾蘭人不但以他為榮,還把《尤利西斯》主角布魯姆一天全部活動的六月十六日定為布魯姆日(Bloomsday),該節日後來成為了規模僅次於國慶日(三月十七日 Saint Patrick’s day)的大節日,我躬逢其盛,也跟著穿百年前時裝的人潮在布魯姆之路慶祝,全世界大概只有愛爾蘭人以如此方式向文學家致敬,這個民族實在太可愛了!
有一天在全歐最大的市內鳳凰公園 健走(Phoenix Park 1663年設立,七百多公頃,約二十七個大安森林公園大),後方忽然傳來馬蹄的踢踏、踢踏清脆聲,一輛馬車自遠而近,這聲音是否為塞爾特踢踏舞的靈感來源不得而知,但來了一趟寶山總不能空手回,觀光部門有句宣傳詞寫著:Come and dance with me, In Ireland. 門票早已預購,特地去觀賞那聲名遐邇、原汁原味的 Riverdance,其舞技之精采自不在話下,當帶著興奮與讚嘆的餘韻與大群觀眾走出劇院時,心理起了個問號,如今,都柏林還會庸俗到令人窒息嗎?早年喬伊斯曾吐嘈:「你知道,是的,都柏林,從來沒變過,始終如一。」你錯了,真的,在這個人口不到一百二十萬的都市裡擁有一千兩百多個樂團,除了U2、恩雅、西域男孩外,大河之舞的呈現已夠令人感覺到迷眩,都柏林已蛻變成一個很有文化、很有活力、也很有魅力的世界舞台。啊!魂兮魂兮,喬伊斯,你在何方? You sould come to dance and sing with Dublin。
離開都柏林的前一天,女兒邀我去三一學院及附近的聖史蒂芬綠色公園散步,行經一處大建築物(出來後才發現是愛爾蘭國立圖書館),忽見葉慈150週年誕辰紀念展,雖離閉館時間不到一個鐘頭還是喜出望外。
葉慈顯然與喬伊斯不同,他曾寫道:「我們應當在我們熱愛、熟悉的景觀上作詩,而不是在令我們目眩神迷的稀奇風光上寫詩。」他是當年愛爾蘭仍在大英帝國淫威下喚醒文藝復興運動的重要推手。展場的 3D 銀幕牆正交叉放映著影片與詩句,而且以陰陽頓錯的聲調朗誦一首我最喜歡的詩:《一位愛爾蘭飛行員預見死亡》(An Irish Airman Forsees His Death),當讀到熟悉的兩句時,感覺像觸電一般:
A lonely impulse of delight Drove to this tumult in the clouds; I balanced all, brought all to mind, The years to come seemed waste of breath, A waste of breath the years behind In balance with this life, this death.
據說飛行員的母親葛瑞格里夫人一直在金錢上支持葉慈,在從事愛爾蘭戲劇活動上也鼓舞他釋放創作精力,少校飛行員是夫人的獨子,飛往義大利不是為了憎恨敵方,也不是為了保衛所愛的家園,只是覺得生息中的浪費已付之飄風,明知是趕赴死亡的約會,仍執意前往,尋求一種屬於「孤寂而且愉悅的衝動」,最後在「不可避免的預料中」取得恣性與豁達的平衡,也超越了淒美與悲壯的生命意義,此放手一搏終至在義大利上空墜機身亡。生命的果實在成熟後會自然掉落,卡謬指的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可能就是指這類形式的「自殺」行為。藝評家咸認該詩是英詩中的一大傑作。
葉慈從事創作,認定生命僅僅是生息上的虛構,藝術才是至高無上的現實,但藝術的追求猶如在黑暗中摸索,必須面對生活的困頓、靈感的煎熬、名利的喧擾、甚至愛情的折磨(苦追茉德˙岡十多年仍無法修成正果),在《抉擇》一詩中寫道:
人的智慧被迫選擇 生命或作品的完美, 選擇第二項,則必須拒絕 天國的巨邸,在黑暗中發怒。
「自從亞當墮落以來,凡美好的事物莫不需要諸多辛勞」,當這艱難志業的美妙時刻降臨時,詩人以優美的詩回報恩典,他的詩是從殘酷的儀式中精雕出來的晶瑩藝品,能穿透世人的感官進入靈魂,如果把「愛爾蘭」的成份抽掉,葉慈的偉大將所剩無幾,難怪英詩人奧登在悼詞中寫道:「瘋狂的愛爾蘭將你刺傷成詩。」(Mad Ireland hurt you into poetry.)
大英帝國時代曾雄霸寰宇,如果說當時的英格蘭是右腦,政經科技皆領導世界,那麼愛爾蘭就是左腦,除了音樂、舞蹈、詩人等藝術家輩出外,王爾德的機智,蕭伯納的幽默,喬伊斯的冷酷,葉慈的浪漫,新愛爾蘭的文學想像與文藝復興就是由他們共同編織出來的,如果再以人口、面積而言,除了葉慈、蕭伯納外,加上貝克特(Samuel Beckett)和當代詩人希尼 ( Seamus Heaney ) 等四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比例而言,那頂皇冠上的藍寶之燦爛是獨步全球的了!
˙ 2015年5月24日,愛爾蘭公投結束,同性婚姻合法化公投案獲得62%的支持通過。愛爾蘭成為首個以公投方式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 三一學院已有423年歷史,擁有全歐最大圖書館,與牛津、劍橋其名,王爾德與貝克特皆畢業於此。
|
|
| ( 心情隨筆|心情日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