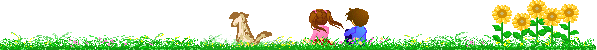.
聯考後的期待 08. 04(日) 晴 (美惠、戴天和老師來信)
有三個多月沒記日記了,今重拾起筆來想寫點東西都不知該如何寫法好,想不到腦子幾天不用竟也生起鏽來,真是可悲。
「期待」這字眼在我心目中就如同「虐待」一樣,不可否認的,自從聯考結束後,我沒有一天不期待著。換句話說,我沒有一天不是受精神虐待的。啊!廿六日,離今尚有二十來日,真不知要如何來打發這些日子,可憐的期待者......
今晚月色很好,春梅來找我聊聊,說得適當些,我們像是楚囚相對,只差沒掉眼淚,因為沒必要,就是說把眼淚掉光了於事又何補?堅強是對的,可憐的期待者,期待吧!雖然那是痛苦的,但卻是必須而且現實的呢。
【註】以前大專聯考都採人工閱卷,放榜時間較今或遲一些,因此考生也要在這方面多受到一些時日等待放榜的煎熬。
音樂的陶冶 08. 05(一) 晴
早晨起來時,肚子突然出奇的不舒服,吃了點藥後便又繼續睡,這一覺睡得很好,不像昨晚直作惡夢。九點起床,毛病已消失了,幸甚。不過情緒仍然不見安定下來,這些日子可真夠我受的,飲食不安,起坐無常,在這種情形下,也怪不得平日少毛病的我會突然生出毛病來了。
在無可如何之中,找慰藉倒是需要的,做什麼呢?看書,不錯,這是我的嗜好,學幾句英語會話,或許將來會用到的。說起來也真可憐,學了六年的英文,而連最基本的會話都不會,這方面實應加強才好呀。再就向收音機求援,但討厭地,一扭開便是商家大打宣傳鼓,什麼新保力達、口味兒的,真有他們的一套。不管,喳!聽我的古典音樂去了。我由衷的敬佩那些音樂家,真不知他們是如何創造出那美妙的弦律的,把偉大的字眼冠在他們頭上,是當之無愧的,偉大啊!巴哈、貝多芬、海頓、莫札特......
黃昏時,心血來潮,洋馬兒一騎,找幸齡去,我們已整整三年沒見過面了。我們閒話家常,談得很投機,時間關係,半小時後,我告辭了。在途中,和風習習,不勝涼快,身心確是輕鬆多了。
【註】當年的英文課從未安排會話課,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下,學生開不了口,也就不足為奇了。
為蕉樹整容 08. 06(二) 晴 (給May信)
這幾天也許是父親特別開恩,沒把我調到田裡工作,當然在家裡不一定比田裡輕鬆,不過我寧願留在家裡多做些家事,而不願到田裡受罪。但好景是不會常有的,上午我便奉命到香蕉園為香蕉樹整容打扮去了,據說它們打扮好了(割掉枯葉子)準備灑些香水呢(噴農藥是也)。這工作雖然輕鬆,但太陽伯伯可一點不容情,晒得我豆大的汗粒直往泥土裡滴,無怪乎人人要說農作物是血汗的結晶哩。
近來母親心裡似乎很不舒服,我知道嫂嫂的作風是讓她不高興的最大因素,我為自己無能勸她感到十分的遺憾,我能對她說什麼呢?
折磨 08. 07(三) 晴 (友佳來信)
昨晚沒睡好覺,一起床便有頭重腳輕之感。用過早餐後,先挑好水,然後洗衣服,包括那些小傢伙一家十口的衣服,可真夠我洗一陣子,手心都洗痛了,還好沒其他工作。不過頭腦仍昏昏沉沉的,想睡,又睡不好,時而由夢中驚醒。看書嘛,背不了幾個單字,看不了幾行英文,又想睡了。天老爺,這是不是所謂的「折磨」呢?
收到友佳的來信,首先叫我嘆服的便是他那俊拔的筆跡,寫字方面我確是望塵莫及了,書法我想再攻十年再談吧。信上有提到他父親(即三叔),據他說他與父親同是那一類型的--唯我獨尊的獨裁者。當然的,有其兄必有其弟,不過有其父必有其子,在我看來,是不會有的,也不希望有。
下午與母親到野外打柴,去的時候蠻輕鬆的,但回來可不同了,任重而道遠,年紀輕輕的我終覺有點吃不消,何況年過半百的母親。我真佩服她那股忍耐的毅力,我但願也有那股潛在的毅力,這對坎坷的人生之旅是有很大的助益的。路途遙遠,也總有走完的時候,不是嗎?看,院旁那叢翠竹已隱然可見了,漸漸地,由模糊而清晰,它在微風中輕輕地搖曳著它那苗條的身軀,好似在歡迎我們娘兒倆的滿載而歸呢。終於我們完成負重的行程,放下重擔,輕輕地舒口氣,這種感覺確有異樣的舒服,非當事者是難以體會的。
很遺憾的,我又要提到大嫂,她對家中的每一份子都不滿,連母親也不例外。如友佳所說的:「我真想爆炸。」對她,我也時有這種感覺,總有一天,我會爆炸的.......,愛因斯坦說的,世間每一事物都是相對性的,她對我們不滿,我們何嘗就對她滿意過?
訪友 08. 08(四) 雨後新晴
僅僅為了一堆廢東西,可被那唯我獨尊的老子罵個夠,簡直氣死了,他把我看成連一堆舊東西都不如,真那麼慘嗎?
為舒舒那口悶氣,自行車一騎,到旗山去兜兜風,此行的目的有二,一是還書,一是順道訪友。一路上內心感到無比的舒暢,那口悶氣很自然的煙消雲散了。
首先是看看彩蘭,老樣子,活潑中帶點憂鬱貌,不過髮型變了。其次是貴梅,已長得亭亭玉立。接著就是宮雲、柯末、惠美、秋美,她們多少有些改變,態度方面,不用說更加親切了,這也是極其自然的感情的流露,以前在學校時也是有的,只不過不為大家察覺罷了。在惠美家小坐了一會,然後便到學校去,在那兒又遇到戴先合老師及林崇漢等幾位負責做同學錄的同學。有位工友見了我便來了一句:「唷!頭髮都燙起來了,以後應叫劉小姐了。」真是缺德鬼,連老師也笑起來了,我可窘得不知如何是好,而他們卻在一旁樂開呢。
中午在三嫂家用午餐,兩點多又開始我的訪友活動。第一個是美英,她現在正學裁縫,與她一起的聽說有秀蓁、春玉,她們是在林崇漢的姊姊那兒學的。這位裁縫師與她弟弟一樣,富有幽默感,又平易近人,與她相處頗有意思。在那兒耽到五點,才往旗尾去。途中遇到豐蘭及楊、黃兩人,我幾乎認不出來,因為她們都變了,很時髦,不過仍有點稚氣。別了她們,我逕往玉凰家,剛好她挑了蔗葉回來,那樣子與我年少時一樣,很可愛。我把春梅向徐郎雄借的書託她帶還他。在那裡我又見到靜卿妹,她永遠是那樣天真活潑。
離開玉凰去找玉蘭,不在,只好去訪我最後要找的一位朋友玉雪,路上遇到初中同學麗月,我對她確有十分的好感,我永遠不會覺得她有什麼缺點,是朋友中最難得的一位。因時間的關係,我們沒有多談,互道再見後,我匆匆地又趕到玉雪家,她似乎又高了些,標致動人。回家時,她送我至旗尾橋上,此時落日的餘暉照在河水上,涼風習習,一切顯得那麼動人,但我們臉上卻蒙上淡淡的哀愁。唉!夕陽無限好,可惜近黃昏。儘管我們彼此都有許多話要向對方傾訴,但我們還是默默的分別了。

.
(刊頭圖片取自網路)
.


 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