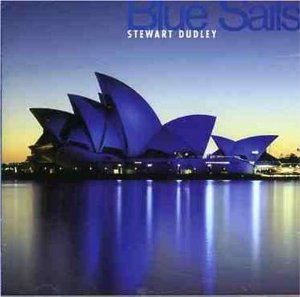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5/07/01 14:56:41瀏覽1192|回應0|推薦28 | |
這一日的酷熱,像不老的詩意。我想起在雪梨買的這片CD.... Rene 的男人乾瘦,帶著深度眼鏡,黑框後沉沉的那種。 當我成天幻想著享受死的快感時,他找上了我,這肯定是 Rene 促成的。 他要我挪出時間給他,然後,在診間開始對我催眠,因為他是身心科醫師。 說真格的,要不是他那一身貼合的白袍,我還真覺得他像極了在市場叫賣鳳梨的。 催眠完了,像場白日夢,似夢似醒。我只記得診療室裡迴盪的曲子很美,這我想起了曾在喜馬拉雅山脈下遠眺的魚尾峰。 我的夢靨還在,一如他的頹喪與無奈。 然後,他和我談了很久很久,話題都圍繞在他死去的父親。還有西藏生死書,關於索甲仁波切的死亡遷徙。 1998 那年冬天很冷,沁到骨子裡的那種冷。我愛的Rene心更冷。 2/16 情人節的隔兩天,她那像賣鳳梨的男友去南亞開完醫學研討會要回國。 我陪著她去了大園,我搶過她手上的車鑰匙,堅持由我開車,因為全台各媒體都陷入了華航空難的悲傷裡。 我沒有眼淚,天生就沒有眼淚,我第一次為此感到傷心,因為我居然沒有能力陪Rene一起哭。 他的殘肢吊掛在大園的枯枝上,根本不需要DNA確認。因為他那無名指上翠綠色的愛情戒是Rene給的獨一無二,也成了最後的死亡見證。 他,走了。我的西藏生死書都還沒來的及看完呢,像賣鳳梨的他就已經走了。 生,與死。到底誰說得準呢 ? 又是誰說得才算呢 ?
|
|
| ( 休閒生活|雜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