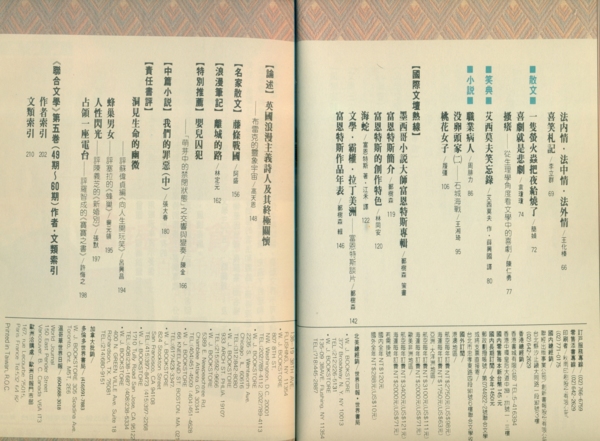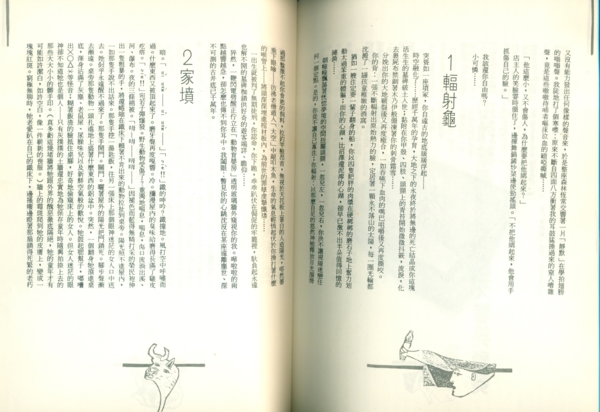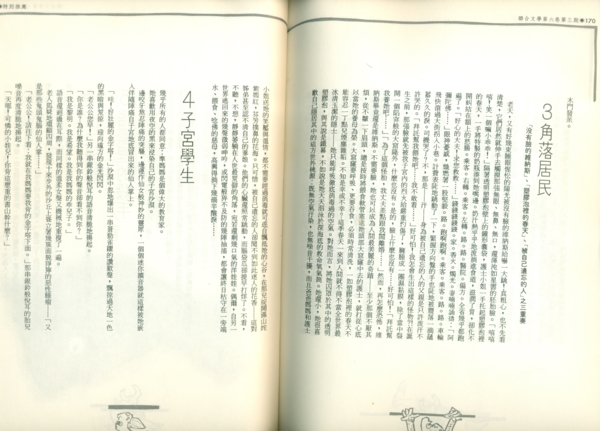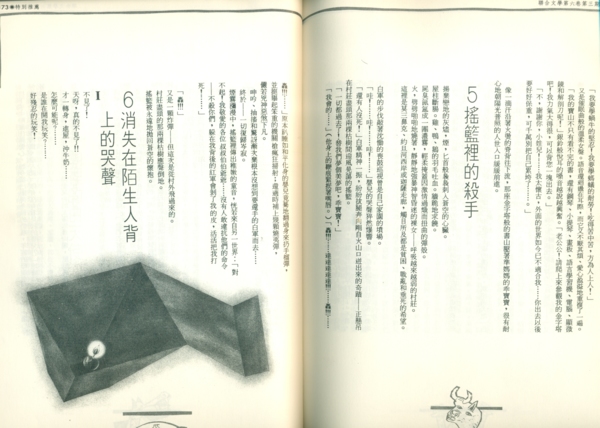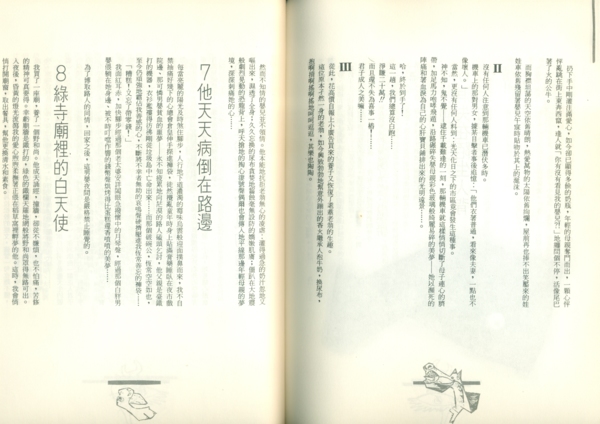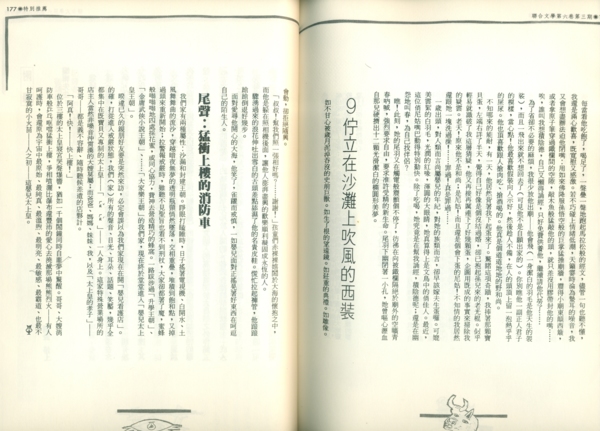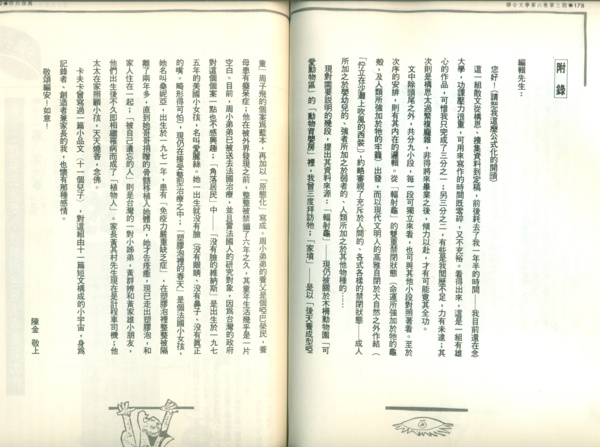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2/03/26 17:10:24瀏覽755|回應0|推薦35 | |
嬰兒囚犯 陳 今 ——「萌芽中的禁閉狀態」之交響與變奏 前奏:非自願的幫兇 在店主人雙手的靈巧包紮下安全躺平,你猶如一件貴重易碎的禮物悄悄泊靠進我懷裏。那麼嬌嫩,那麼純,一向剛強似鐵的我覺得自己好像一下子柔化了,化成一汪海水,輕輕環擁住你這朵正盛開著潔白大花瓣的溫熱睡蓮。 沙發是座風平浪靜的港。港內,你是我這艘即將揚帆向夢鄉的船上唯一的乘客。忐忑著連自己都感到驚訝的慈愛目光俯望你,全然不知自己這條小命已落在陌生人——我——手中的你,唉,我不得不默認:雖然還算溫暖,我的懷抱卻不適合當搖籃。一向對「被愛」缺乏自信的我,突然害怕起「承托你」的這項嶄新使命。 而你,依然安靜地沈澱入夢鄉,什麼也沒感覺到。那麼安靜,活像一塊柔軟的岩石。 你的鼻息,平和、悠長。一吸:酣渾飽滿;一吐:理直氣壯——充斥人世的暴戾之氣彷彿都在你這一吸一吐間給篩濾一空了…… 「為什麼?……」「怎麼會這樣?……」「是誰?……究竟是誰幹的好事?! ……」——並未受傷,你的雙手卻被白紗布給緊緊纏綑著,一手一團雪,像西伯利亞和南極洲,像兩顆巨大的蠶繭。無名之火驀地在我體內爆燃,迅速流竄,甚至燒痛了我前幾天做的那場夢: 夢中的我跌跌撞撞闖入一座森林。周遭半明半暗,窒人的嘈雜聲猛捶我的耳鼓。樹長得很茂密,一棵毗捱著一棵,但都不及我高。樹上的枝椏,末梢都圓瞪著一顆大眼睛,沈甸甸地垂吊在半空中,有的還碰觸到地面,走近一看才知道是鳥巢。透過紗簾般封掩住巢口的層層蠶絲,我可以清晰瞧見巢內的小生命和燭火般隨風搖曳的微光。我一會兒看看這邊,一會兒瞧瞧那邊,恍如置身於奇妙的「雛鳥王國」,而一股股正在蓬勃發育的溫熱氣息則不斷自鳥巢內吹到我身上。所有的雛鳥都赤裸裸的,還睜不開眼睛。怪的是,幾乎每一隻都不像鳥:有的像蜥蜴,拖著一條長尾巴;有的像魚,有鰓也有鰭;有的像獅子,滿頭亂蓬蓬的鬃毛;也有的像老人,臉上龜裂著深深的皺紋……這些被囚禁在鳥巢內的迷你怪物,牠們都張嘴拚命嘶喊,狀極悲淒,卻又沒有能力發出任何像樣的聲音來,於是整座森林恆常交響著一片靜默在學拍翅膀的嗡嗡聲。我陡地打了個寒噤:原來不斷自四面八方衝著我的耳鼓猛捶過來的窒人嘈雜聲,竟是這些嗷嗷待哺者嘔沫泣血的喑啞嘶喊…… 「他這麼小,又不會傷人,為什麼要把他綁起來?!」 店主人的笑臉霎時僵住了,邊揮舞鍋鏟炒菜邊使勁搖頭。「不把他綁起來,他會用手抓傷自己的臉!」 我該還你自由嗎? 小可憐…… 1 輻射龜 突聳如一座墳冢,你自遠古的地底緩緩浮起—— 時空融化了……歷經千萬年的孕育,大地之下的永夜終於將無邊的死亡結晶成你這塊活生生的墓碑破土入世;黏附在你甲殼、四肢、頭頸上的青苔開始微微抖簌,流淚,化去裹屍布禁錮著木乃伊般僵凍著你的刺骨霜雪…… 分娩出你的大地皸裂後又再度癒合,一如吞嚥下血肉的嘴巴咀嚼後又再度撕咬。 你的背:一張不斷輻射出原始熱力的臉,定居著一顆永不落山的太陽,每一圈光輪都沈澱了一罈孩童稚嫩的酒窩。 猶如一艘注定要一輩子翻身的船,你以四隻肥胖的肉槳在硬邦邦的磨石子地上奮力划動太過笨重的體軀;而你的心湖,比沼澤還泥濘的心湖,卻早已激不出半朵值得回憶的漣漪…… 朝幢幢飄蕩著恍惚夢境的空間扭擺頭頸,一忽兒左,一忽兒右,你決不讓視線迷戀任何一個定點。是的,你從不讓自己專注;你輻射:以那麼自足的悠然神態釋放目光溜滑過那盤激不起你食慾的飼料,拉釣竿般昂首,無視於天花板上蒼白的人造陽光,嗒然萎垂下眼瞼——彷彿老僧遁入大空中敲叩木魚,生命的氣息輕悄起伏於你捶打著什麼的喉管上——將頭深深埋進棺材板內,為前世的罪孽虔摯懺禱…… 一出生就被判了無期徒刑,你認命,你下跪,乖乖趴伏在侷促的甲殼牢籠裏,馱負起永遠也打不開的墓碑枷鎖供好奇的遊客端詳、瞻仰…… 猝然,一鞭閃電驚醒正佇立在「動物育嬰房」透明玻璃牆外窺視你的我。嘩啦啦的雨點越響越急,卻怎麼也傳不到你耳中。我闔眼,讓自己逐漸沈澱入宇宙的內在世界。在那邊,我似乎瞥見你的心跳隱匿在某囗荒山幽井底已千萬年…… 2 家墳 暗。「ㄍㄧˇ ㄍㄨㄞˊ——ㄍㄧˇ ㄍㄨㄞˊ——」「ㄅㄧㄤˋ!!」鐵的呻吟?鐵撞地!風打空中呼嘯而過。什麼東西又被頂起來了。磨牙聲再度嘎響。冷。瀰漫屋內的臭味給磨得長滿了雞皮疙瘩。「ㄅㄧㄤˋ!!」宛若子彈爆發。野生動物受傷了?重濁地喘息,喘息,傷口流淌出溪、河、瀑布。夜的三條棉被。「呣—呣——呣呣——」因褪色而藍得無精打采的榮民袍伸出一隻粗暴的手,將還蜷縮在鐵床下賴著不肯出來的動物拉扯到桌旁。陽光照不進屋內,一如那隻手說不出話來。那隻手挖一湯匙飯,往另一張床上那個眼神迷茫的女人的口中送去。她似乎永遠醒不過來了。那隻手開門。關門。曬著屋外的陽光把門鎖死。腳步聲漸去漸遠。桌旁那隻動物一頭扎進地上盛著什麼東西的鋁盆中。突然,一個翻身牠滾進桌底,渾身沾滿了灰塵、老鼠屎、尿臊味兒以及新鮮空氣般的歡悅。牠鼓起腮幫子,嘟嚷出×○△*等怪音;糊著飯渣的臉抵住桌腳,好奇地偷窺床上的女人。但女人迷茫的眼神卻不知道牠也是個人——只有灰撲撲的土牆還忠實地為牠保存了童年時隨興拍捺上去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髒手印。(真多虧這幾堵牆將牠跟外界的醜惡徹底隔絕,牠的童年才有可能如許潔白,如許空白,像一件嶄新的喪服。)牆上的霉斑爬到牠的皮膚上,變成一塊塊紅斑。窮極無聊時,牠老愛趴在自己的鐵床下,邊搔癢邊瞪著那扇鎖得死緊的老朽木門發呆。 3 角落居民 ——「沒有臉的維納斯」、「塑膠泡裏的春天」、「被自己遺忘的人」之三重奏 老天,又有好幾束睡眼惺忪的陽光被沒有臉的維納斯給嚇一大跳!真粗心,也不先看清楚,它們居然就伸手去觸摸那張無眼、無鼻、無口,還渾沌如星雲的胚胎臉。「嘻嘻嘻!笑一個嘛小乖乖!」隔著透明塑膠泡壁上的鐘形囊袋,護士小姐一手托起塑膠泡裏的春天,一手將特製的奶瓶湊到她嘴邊。奶汁熱呼呼地流淌進食道,滋潤了胃,卻化不開糾結在額上的愁腸。乘客。右轉。乘客。左轉。路。路。醫院。偏方。全省幾乎都跑遍了。「好心的大夫!求您救救……」錢錢錢錢錢。家。香火。燭光。妻喃喃誦禱:「阿彌陀佛……」眼神憂戚,熾燃著一股堅毅。路。跑啊跑啊。乘客。乘客。路。路。車輪飛快滾過大街拐入小巷。計費表陡地跳動了一下,緊握方向盤的手也陡地被震落了一滴蘊蓄久久的淚。司機哭了?不,那是——汗——身為被自己遺忘的人的父親是只許流汗不許哭的。「拜託幫我餵她吧……我不敢看……」好可怕!我怎會生出這樣的畸形怪物來?!在誕生之前,那張臉就先被我子宮內的烈火給嚴重灼傷了,臃腫成一團濕黏膜,除了當中裂開一個陷穽般的大窟窿外,什麼也沒有。是的,我親生女兒的臉上居然什麼也沒有……好可怕!「拜託幫我養她吧……」「為了這個怪胎,我丈夫差點跟我鬧離婚……」然而,再怎麼恐怖,維納斯畢竟還是維納斯。不需要臉,她也可以成為人間最美麗的奇蹟——至少那個不厭其煩,從不皺一下眉頭,總是按時將餵食軟管塞進她頭部大窟窿中去的護士,就打從心底以當她的養母為榮。大窟窿要呼吸、更要吞食,必須時常清洗,一如塑膠泡裏的春天不能容忍一丁點兒煙塵雜垢。不知是幸或不幸?這季春天一來到人間就不得不當全世界最冰清玉潔的隱士——她只能呼吸徹底消毒過的空氣。對她而言,將她囚罩於其中的透明塑膠泡,與其說是鐵幕,不如說是她天天泅泳於深海底的救命氧氣筒。她還小,她很喜歡自己隱居其中的這方「世外桃源」:既無空氣汚染,也無噪音干擾,而且爸爸媽媽和護士小姐送她的笑靨與溫情,都不需要經過消毒就可逕自飄抵她的心谷,在那兒綻開滿山姹紫嫣紅、芬芳撲鼻的花海。只可惜,被自己遺忘的人卻聞不到如此迷人的花香——這對姊弟甚至認不清自己的爹娘。他們的心臟還在照常跳動,而腦袋瓜卻提早打烊了。不看,不聽,不想,靜靜萎躺在人世最荒僻的角落裏,宛若還剩下幾口氣的洋娃娃。偶爾,自另一世界逃回來的幾聲微弱呻吟,或閃電般猝不及防的幾陣抽搐,都會讓終日枯守在一旁端水、餵食、唸佛的慈母,高興得淌下幾滴辛酸淚…… 4 子宮學生 幾乎所有的人都同意:準媽媽是個偉大的教育家。 她喜歡用夜空的黑來浸染自己的子宮沙漠。 邊咬牙熬忍陣痛的突襲,邊運作仙女那魔力般的靈犀,一個個迷你擴音器就這樣被她嵌入伴隨陣痛自子宮地底冒出來的仙人掌上。 「哇!好壯麗的金字塔!」沙漠中忽地爆出一串蒼勁雀躍的讚歎聲,飄掠過天地一色的黑暗與荒涼,迎向遠方的金光閃閃。 「老公公您早!」另一串銀鈴般悅耳的語音神祕地揚起。 「你是誰?為什麼我聽得到你的聲音卻看不到你?」 「我是黎明。我是希望。我是我媽螞的乖兒子。」 語音還迴盪在耳際,而同樣的溫柔女聲又機械地重複了一遍。 老人狐疑地環顧四周,發現十來步外的沙丘上聳立著幾簇面貌猙獰的「惡性腫瘤」——「又是那些鬼頭鬼腦的仙人掌!……」 「老公公!請您往下看:我就在我媽媽要我背起來的金字塔下面。」那串銀鈴般悅耳的胎兒嗓音再度揚起。 「天哪!可憐的小娃兒!你背這麼重的金字塔幹什麼?」 「我要學蝸牛的堅忍!我要學螞蟻的耐勞!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又是催眠曲般的溫柔女聲。語音還迴盪在耳際,而它又不厭其煩、愛心盈溢地重複了一遍。 「我媽媽送我的金字塔真的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寶山,裏面堆滿了一輩子都看不完的書,還有鋼琴、小提琴、畫板和各種美麗的顏料、語言學習機、電腦、顯微鏡以及解剖刀!」銀鈴般悅耳的嗓音越說越興奮。「老公公!請您爬上來參觀我的金字塔吧!我力氣大得很,可以背您一塊出去。」 「不,謝謝你,小娃兒!……我太懷古了,外面的世界如今已不適合我……你出去以後要好好保重,可千萬別把自己累垮了!」 像一滴汗沿著火燙的脊背往下流淌,那座金光閃閃的金字塔壓著準媽媽的乖寶寶,在天地一色的黑暗與荒涼中,很有耐心地朝陽光普照的人世入口緩緩前進…… 5 搖籃裏的殺手 揚棄戀地的灰燼,煙,匕首般裊裊刺入蒼空的心臟。 屋柱斷腸。雞、鴨、鵝的羽毛吐血。牆跪地求饒。 屍臭氤氳成一團濃霧,輕柔掩蓋因激情過熾而扭曲的彈殼。 火,劈劈啪啪地燒著,靜靜地強暴神智昏迷的裸女——呼吸越來越弱的村莊。 這裏是莫三鼻克、約旦河西岸或迦薩走廊,觸目所及都是貧困、戰亂和垂死的希望。 白軍的步伐敲著沈慟的喪鼓巡視曾是自己家園的墳場。 「哇!……哇!……哇!……」嬰兒的哭聲猝然爆響。 「還有人沒死!」白軍精神一振,紛紛拔腿奔向彷彿剛自火山口迸出來的奇蹟——正懸吊在村莊盡頭那兩棵枯樹間迎風晃蕩的搖籃。 「一切都過去了!替我們夢個美夢吧,乖寶寶!」 「我會的!……」(嬰兒背上的鞭痕緊閉著嘴唇,深深烙印著紅軍所遺留下來的岩漿般的威嚇聲。)「轟!!!……達達達達達!!!……轟!!!……轟!!!……」原本趴睡如和平化身的嬰兒竟驀地翻過身來扔手榴彈,並挺舉起笨重的機關槍瘋狂掃射,間或補上幾顆燒夷彈,儼若兇神惡煞下凡。 呻吟、抽搐和驚訝漸漸棄根本沒想到要還手的白軍而去…… 終於——一切復歸岑寂…… 煙霧瀰漫中,搖籃裏傳出稚嫩的童音,恍若來自另一世界:「對不起!我敬愛的各位叔叔伯伯爺爺!……沒有人敢違抗他們的命令——不殺你們,躲在我背後的紅軍會剝了我的皮,把我活活打死!……」 「轟!!!」 又一顆炸彈猝然爆響——但這次是從村外飛過來的。 村莊盡頭的那兩棵枯樹應聲倒地。 搖籃被永遠地拋回蒼空的懷抱…… 6 消失在陌生人背上的哭聲 I 不見了! 天呀,真的不見了!! 才一轉身,進屋,沖牛奶…… 怎麼可能呢?!…… 是誰在開我玩笑?…… 好殘忍的玩笑! 扔下手中剛灌注滿愛心、如今卻已顯得多餘的奶瓶,年輕的母親奪門而出,一顆心怦怦亂跳在街上東奔西竄,逢人就「你有沒有看見我的嬰兒?!」地纏問個不停,活像一頭尾巴著了火的公牛。 而胸襟坦蕩的天空依舊晴朗,熱愛萬物的太陽依舊絢爛,屋前再也捧不出笑靨來的娃娃車依舊殘留著嬰兒午寐時貼吻於其上的涎沫。 II 沒有任何人注意到那輛機車已潛伏多時。 機車上的那對男女,據某目擊者事後追憶:「他們衣著普通,看來像對夫妻,一點也不像壞人。」 當然,更沒有任何人會料到: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市區竟會發生這種事! 神不知,鬼不覺——逮住千載難逢的一瞬間,那輛機車就這樣悄悄切斷了母子連心的臍帶,加足馬力咆哮飛遁,沿路輾碎失嬰母親彩色玻璃般綺麗易碎的美夢——她以瀕死的陣痛和著血淚為自己的心肝寶貝鋪排出來的光明遠景…… 終於到手了! 這一趟,我們總算沒白跑…… 淨賺二十萬,而且還不失為喜事一樁!…… 的確如此:所謂「君子成人之美」嘛…… III 從此,花高價自報上小廣告買來的養子又恢復了耄耋老翁的生趣。 這位原本孑然一身的老翁,如今興致勃勃地幫意外蹦出的香火繼承人泡牛奶,換尿布,抱啊揹啊搖啊搖地呵呵逗逗,其樂也陶陶。 然而不知情的嬰兒並不領情。他本能地抗拒老翁無心的凌虐:灌得過急的奶汁忽地又嘔出來,濕透了全身;久久忘換的尿布貪婪地齧蝕毫無設防的嬌嫩肌膚;僵趴在大地震般劇烈晃動的恐龍背上,呼天搶地的掏心淒號聲偶爾也會傳入地平線後面那位年輕母親的夢境,深深刺痛她的心…… 7 他天天病倒在路邊 每當亮麗的陽光及時煞住腳步,人行地下道濃濁的霉味烏雲般迎面撲鼻而來,我不自禁抽痛好幾下的心總會倉皇伸手探進褲袋,徒然攪亂童年時身上貼滿膏藥睡臥在夜市戲院邊、那可憐男嬰貧血的噩夢——始終永不知疲累地朝茫漠的路人磕頭乞討,他的父親像一台鐵打的機器,衣衫襤褸得彷彿剛從垃圾島中亡命出來……而那個破碗公,恆常空空如也,至今仍頑強地霸佔我善感的心,不斷將不幸者無助的哀鳴聲硬擠壓進我恆常善忘的褲袋裏…… 「糟糕!又忘了帶零錢出門了!」 我面紅耳赤,加快腳步經過那個老太婆安詳闔眼急撥懷中的月琴聲,經過那個白胖男嬰偎躺在她身邊、被不時叮噹作響的錢幣聲烘烤得比蛋糕還香噴噴的美夢…… 為了在白天博取路人的同情,回家後,這男嬰夜間是嚴格禁止睡覺的。 8 綠寺廟裏的白天使 我買了一座廟,養了一個野和尚。他成天誦經,撞牆,卻從不嫌煩,也不怕痛,苦修的精神可真要得。幸虧廟牆是鐵打的,綠色的鐵欄天羅地網般將這野和尚罩得無路可出。入夜後,昏黃的燈光流瀉我的愛心煦煦柔撫著正偎在稻草窩裏孵夢的他。這時,我會悄悄打開廟窗,取出餐具,幫他更換清水和素食。 每當看他吃飽了,喝足了,一聲疊一聲地跑起馬拉松般的經文,儘管一句也聽不懂,我還是滿心歡喜,既寬慰又感激。若不巧碰上情緒低潮,天籟霎時淪為蟄耳的噪音,我又會想盡辦法迫他閉嘴:用如來佛降服孫悟空般的巨掌猛捶廟牆,震得小廟東顛西簸,或者拿原子筆穿過鐵欄間的空隙,敲木魚般猛敲他的頭,就只差沒用膠帶封他的嘴……唉,誰叫我想積陰德,自己卻又懶得誦經,只好繼續供養他,請他代勞了…… 為了省掉不必要的麻煩,我很少放他出廟——他會飛(一身潔白的羽毛是他天生的袈裟),而且一飛出來就不想回廟裏去了(可見他不是自願出家的)。你別瞧他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樣,當心點!他最喜歡假裝向人示好,然後趁人不備,飛上人的頭頂在那兒留下一泡熱呼呼的屎尿。他也頂喜歡跟人搶肉吃、搶酒喝的。他真是個道道地地的野和尚。 不知哪來的能耐,有一天,他居然背著我下起蛋來了。驚睹這項奇蹟,我捧著那顆寶貝蛋,左端右詳了老半天,覺得自己好像是個沒結過婚,卻已抱起孫兒來的老光棍。似乎輕易就識破了我這層猜疑,他又再接再厲連下了好幾顆蛋,企圖用既成的事實來掃除我的疑雲。老天!原來他不是和尚;是尼姑!而且還是個會下蛋的尼姑!不知情的我居然還跟她一塊洗過澡!……罪過!……真是罪過啊!…… 一歲出頭,對人類而言尚屬嬰兒的年紀,可對她的族類而言,卻早該嫁夫生蛋囉。足以媲美雲絮的白羽毛,光潤的紅喙,渾圓的大眼睛,她真算得上是文鳥中的俏佳人。最近,這位俏尼姑嘴巴動得特別勤快。除了吃喝,她究竟是在幫我誦經、積陰德呢;還是在幽怨地叫春,為自己找伴侶? 瞧!此刻,她的尾羽又在觸電般震顫個不停了,彷彿在向被鐵欄隔絕於廟外的空曠青春吶喊,強烈要求自由,要求伴侶,要求讓她准許受精,以便孕育下一代的新生命。尾羽下幽閉著一個小孔,她曾嘔心瀝血自那兒硬擠出十二顆光滑潔白的橢圓形美夢…… 9 佇立在沙灘上吹風的西裝 如不甘心被歲月泥淖吞沒的史前巨獸。如生了根的望遠鏡。如莊重的典禮。如雕像。會動,卻拒絕隨興。 「叔叔!請幫我們照一張相好嗎?……謝謝!」孩童們赤裸裸嬉鬧於大海的懷抱之中,而他則是躲在照相機後面讓他人澎湃盡興的歡樂順利凝固成永恆的人。 驟湧過來的浪花伸吐出雪白的舌頭差點舔濕了他的名貴皮鞋。慌忙拉起褲管,他踉踉蹌蹌倒退了好幾步。 面對愛尋他開心的大海,他笑了,雀躍而戒慎,一如嬰兒面對正搖晃著好東西在呵逗自己的陌生人那樣。 尾聲:猛衝上樓的消防車 我們家有兩種屬性:沙漏和封建王朝。睜眼打瞌睡時,日子搖著電視機、白開水、土風舞舞曲的流沙,穿越暗夜缺少美夢的透明瓶頸悄然墜落,交相重疊,堆積到飽和點,又掉過頭來重新開始;拉警報戒嚴時,雖聽不見聖旨也看不到刑杖,大家卻都彷彿著了魔,蜜蜂般嗡嗡嗡地四處採花蜜,或同心協力,費神去營造精巧的蜂窩。一路跋涉過「升學王朝」、「金庸武俠小說王朝」、……「大家樂王朝」的我們家,現在終於堂堂進入「嬰兒太上皇王朝」。 睽違已久的親朋好友要是突然來訪,必定會誤以為我們家現在在開「嬰兒看護店」。的確,打從進入戒嚴狀態,我們家的所有聲音、目光、耳朵、話題、笑靨,幾乎全都集中在既寶貝又專制的太上皇——「ㄏㄠˇ ㄏㄠˊ」——一人身上。這家特殊營業場所的店主人當然非嗓音沖霄漢的大嫂莫屬;而爸爸、媽媽、妹妹、我,以及「太上皇的孝子」——哥哥——都是義不容辭、隨時聽候差遣的店夥計。 「阿真!快!——快上樓!」 位於三樓的太上皇寢宮哭聲爆響,猶如一千個鬧鐘同時自噩夢中驚醒。哥哥和大嫂消防車般乒乓哐噹猛衝上樓,爭相噴灑比瀑布更豐沛的愛心去澆滅那場熊熊烈火——有人呵護時,會還原為宇宙中最原始、最純真、最溫煦、最明亮、最敏感、最霸道、也最不甘寂寞的小火苗——人之初——這嬰兒太上皇…… 【後記】 這一組散文除頭尾之外,共分九小段,每一段可獨立來看,也可與其他小段對照著看。至於次序的安排,則有其內在的邏輯。從輻射龜的雙重禁閉狀態(命運所強加於牠的龜殼,及人類所強加於牠的牢籠)出發,而以現代文明人的高雅自閉於大自然之外作結(〈佇立在沙灘上吹風的西裝〉),約略審視了充斥於人間的、各式各樣的禁閉狀態:成人所加之於嬰幼兒的、強者所加之於弱者的、人類所加之於其他物種的…… 現對需要說明的幾段,提出其資料來源:〈輻射龜〉——現仍被關於木柵動物園「可愛動物區」的「動物育嬰房」裏,我曾三度拜訪牠;〈家墳〉——是以「後天養成型啞童」周子飛的個案為藍本,再加以「原態化」寫成。周小弟弟的養父是個啞巴榮民,養母患有癡呆症;他在被外界發現之前,整整被禁錮了六年之久,其童年生活幾乎是一片空白。目前,周小弟弟已被送去法國治療,並且當法國人的研究對象,因為台灣的政府對這個個案一點也不感興趣;〈角落居民〉中的那個「沒有臉的維納斯」是出生於一九七五年的美國小女孩,名叫愛麗絲。她一出生就沒有臉(沒有眼睛、沒有鼻子、沒有真正的嘴。畸形得可怕),現仍在接受整型治療之中;〈塑膠泡裏的春天〉是個法國小女孩,她名叫桑妮亞,出生於一九七一年,患有「免疫力嚴重缺乏症」,在塑膠泡裏整整被隔離了兩年多,直到她哥哥捐贈的骨髓移植入她體內,她才告痊癒,現已走出塑膠泡,和家人住在一起;〈被自己遺忘的人〉則是台灣的一對小姊弟,黃群辨和黃家雄小朋友,他們出生後不久即相繼罹病而成了「植物人」。家長黃其村先生現在是計程車司機。他太太在家照顧小孩,天天燒香,念佛。 卡夫卡曾寫過一篇小品文〈十一個兒子〉。對這組由十一篇短文構成的小宇宙,身為記錄者、創造者兼家長的我,也懷有跟卡夫卡對他的那些「兒子」相類似的感情。 (原載《聯合文學》第六十三期,一九九○年一月)
|
|
| ( 創作|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