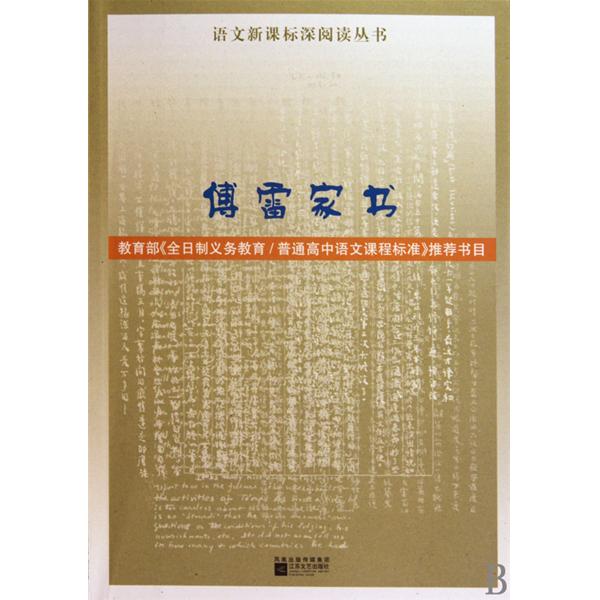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3/11/02 10:44:30瀏覽527|回應4|推薦21 | |
|
終於看完了托爾斯泰的三部巨著:《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還有前幾天才讀完的《復活》,在前兩部書里三位男主角《戰爭與和平》裡的安德列與皮埃爾、《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列文,一生都在謀求生命的意義,通過不同方式尋找內心的平靜與幸福,經過無數的思考與掙扎,通過見證死亡,最終他們都找到了,那就是愛,就是信仰上帝。人生的終極意義,我想大師的作品會給我們指引,看到答案,有些啼笑皆非的感覺。而看完《復活》,更是如此。前兩部是通過信仰上帝來達到內心的平靜,後一部竟然變成解決社會矛盾的利器了。 聶赫留朵夫為了得到生命的“復活”,他決定拯救瑪絲洛娃,因自己引誘致其懷孕卻又拋棄了她,導致她成為妓女,在審判她被誣謀財害命并冤判苦役時產生愧疚,決定與之結婚并幫她翻案,在翻案的過程中,他接觸到了從政府到監獄、從城市到鄉村處處殘酷黑暗等種種現象,他反思土地私有制是產生農民貧窮的根源,抨擊貴族與官員的道德敗壞虛偽自私,他尊敬同情革命者與政治犯,在幫助那些囚犯與政治犯的過程中,他的心靈得到凈化,精神得到拯救,他看到了激烈的社會矛盾以及產生矛盾的根源,但他解決的方案卻是無力虛軟的,就是信仰上帝,人人按照《福音書》的戒律去做,愛自己的仇敵,打了右臉送上左臉等,如果都執行戒律,“人間就會建立起天堂,人們就能獲得至高無上的幸福”。 大師給出的出路對我幾乎沒有借鑒意義,宗教到了作家那裡竟然變成萬能的,對於我這個從小受馬哲教育堅信馬哲宗教觀的人來說,很難認同。大師反對法律,因為執法的人草菅人命腐敗冷酷,但他忽略了一個問題,戒律難道不是相當於法律一類的東西嗎?區別在於不是強制執行而已,即使《福音書》的戒律是萬能利器,怎麼能保證人人都會執行?靠傳教嗎?靠強制嗎?如果宣傳與強制都不行呢?懲戒該不該有?如果沒有的話,怎麼對待違反戒律的人?司法機關應該不應該存在?這些深層次的問題作家并沒有思考,他可能是期待人人都像聶赫留朵夫一樣自我覺醒自我拯救吧。對於怎樣達到內心的平靜還有解決社會矛盾,我也沒有多少思考,只能說托爾斯泰指的出路我不認同。
傅雷像
西文文學藝術裡關於宗教的思考比比皆是,甚至無處不在。想起去年所看的《傅雷家書》,著名的翻譯家傅雷先生,他與其子傅聰的通信中也探討過宗教的問題,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與二月七日傅雷老師寫給傅聰的信中,因對巴赫音樂風格的分析寫到基督教對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影響,又延伸到我們中國對於宗教的態度;傅雷先生大概闡述了自己對貝多芬音樂的主題沖突的理解,進一步提到基督教的影響,又用更多的筆墨比較了我國歷代對於宗教與西方的不同。這是非常長的兩封信,讀後非常震動,也曾零星思考過宗教的一些問題,也一直再想,如果沒有天堂地獄前世今生這些宗教教義描繪出的兩世世界,會不會約束或者誘惑更多的信眾呢?就如傅雷老師所言,“造出許多極樂與極可怖的幻象來一方面誘惑自己一方面威嚇自己”,如果沒有極樂的誘惑或者極可怖的威嚇,關於宗教的信仰能給那些信眾帶來無比的精神安寧嗎? 但有眾多人說只有相信科學,加強文化教育才能改變這種情況,以前深以為然,但現在想想也不盡然,比如西方社會是教育普及程度最高的,但科學技術的進步與虔誠的宗教信仰卻並行不悖,還有一些知名的科學家老年又沉溺於有神論的怪圈,比如牛頓,所以說這種複雜性連傅雷老師都想不通,知識淺薄的我就更想不明白了,也許因為人性本來就是複雜豐富的,人類做選擇做判斷並不唯一依靠理性和智慧吧。 但不管怎樣,即使科學與宗教能達到並行不悖也好,教育的普及總是沒有壞處的,不說藏傳佛教,就說身邊,近年天主教還是基督教也搞不清,在農村地區卻又大行其道了,一些老年婦女又像搞傳銷一樣積極不懈地發展起信徒來,她們宣傳的重點不過是末日拯救天堂地獄之類,這被無數次事實證明過的謬誤。雖然已經渡過傳說的末日2012,末日說還會依舊有市場,但此說尤其是在老年婦女中大行其道,不能不說教育的缺失是最大的因素。 我是信馬哲的,辯證法告訴我們任何事物都一體兩面,宗教有宗教自身存在的價值,宗教產生幾千年來,確實撫慰過無數受難的心靈,也許信眾真能通過他們堅定的信仰達到內心的平和與安寧,但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沒有宗教信仰群體中的一員,對於宗教更看重其中的哲學意義,宗教有信的自由也有不信的自由,有全信的自由與有選擇性接受的自由,有理解但不認同的自由也有堅決反對的自由,我只能說,認可任何一種自由。
附《傅雷家書》選節
基督教本是歷史上某一特殊時代,地理上某一特殊民族,經濟政治某一特殊類型所綜合產生的東西;時代變了,特殊的政治經濟狀況也早已變了,民族也大不相同了,不幸舊文化——舊宗教遺留下來,始終統治著二千年來幾乎所有的西方民族,造成了西方人至今為止的那種矛盾,畸形,與十九、二十世紀極不調和的精神狀態,處處同文藝複興以來的主要思潮抵觸。在我們中國人眼中,基督教思想尤其顯得病態。一方面,文藝複興以後的人是站起來了,到處肯定自己的獨立,發展到十八世紀的百科全書派,十九世紀的自然科學進步以及政治經濟方面的革命,顯然人類的前途,進步,能力,都是無限的;同時卻仍然奉一個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神為主宰,好像人永遠逃不出他的掌心,再加上原始罪惡與天堂地獄的恐怖與期望:使近代人的精神永遠處於支離破碎,糾結複雜,矛盾百出的狀態中,這個情形反映在文化的各個方面,學術的各個部門,使他們(西方人)格外心情複雜,難以理解。我總覺得從異教變到基督教,就是人從健康變到病態的主要表現與主要關鍵。 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上午 我相信,要不是基督教思想統治了一千三四百年(從高盧人信奉基督教算起)的西方民族,現代歐洲人的精神狀態決不會複雜到這步田地,即使複雜,也將是另外一種性質。比如我們中華民族,盡管近半世紀以來也因為與西方文化接觸之後而心情變得一天天複雜,盡管對人生的無常從古至今感慨傷歎,但我們的內心矛盾,決不能與宗教信仰與現代精神自我擴張的矛盾相擴張比。我們心目中的生死感慨,從無仰慕天堂的極其煩躁的期待與追求,也從無對永墮地獄的恐怖憂慮;所以我們的哀傷只是出於生物的本能,而不是由發熱的頭腦造出許多極樂與極可怖的幻象來一方面誘惑自己一方面威嚇自己。同一苦悶,程度強弱之大有差別,健康與病態的分別,大概就取決於這個因素。
另一方面,佛教影響雖然很大,但天堂地獄之說只是佛教中的小乘(淨土宗)的說法,專為知識較低的大眾而設的。真正的佛教教理並不相信真有天堂地獄;而是從理智上求覺悟,求超渡;覺悟是悟人世的虛幻,超渡是超脫痛苦與煩惱。盡管是出世思想,卻不予人以熱烈追求幸福的鼓動,或急於逃避地獄的恐怖;主要是勸導人求智慧。佛教的智慧正好與基督教的信仰成為鮮明的對比。智慧使人自然而然的醒悟,信仰反易使人入於偏執與熱狂之途。——我們的民族本來提倡智慧。(中國人的理想是追求智慧而不是追求信仰。我們只看見古人提到澈悟,從未以信仰堅定為人生樂事(這恰恰是西方人心目中的幸福)。 一九六一年二月七日 。 . .
|
|
| ( 心情隨筆|心情日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