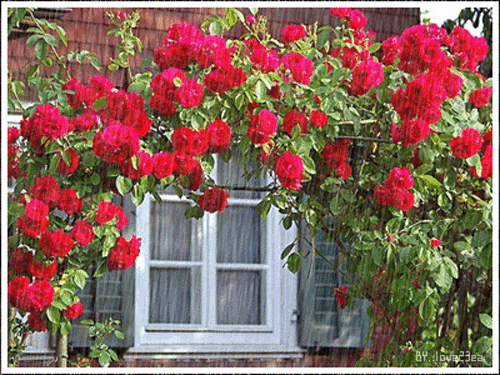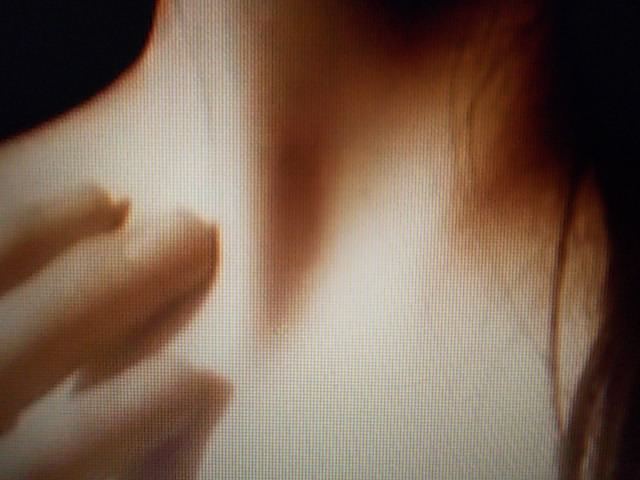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4/03/23 00:04:12瀏覽9389|回應200|推薦454 | |
深夜的艾蜜莉
睡前;她反復咀嚼一位極負盛名的幽默作家所寫的有關愛情的箴言,她開始有捉摸的不詳預感―― 戀愛的人哪,你必須是個迷信的人哪,因為你進入的世界,是一個充滿妖女,蠱,天使,狐貍精,孤魂野鬼,狼心與狗肺的世界,不相信的人,是進不去的,你以為聊齋志異寫得是什麼?當然是愛情。 戀愛的人哪,你萬勿做迷信的人,看看神里頭,最精彩的希臘眾神吧,沒有一件愛情被他們搞好的,至於其他宗教的那幾位,只要是上得了臺面的,都盡管逼著你愛他,不教你愛人的。 她嘆口氣。 愛人左心房和右心房間,永恒而徒勞的辯證,可不是嗎? 就像她總是不確定要不要在睡前把電話;手機全數關掉一樣,關了嘛,至少切斷了他習慣在深夜求救於她的聯系,因為她深切地明白,其實她不是他的歸屬,只是一個情緒的渡口,差不多周期性地;他會在某個關卡上過不去,然後極盡無理取鬧跟蠻橫地強迫要見她一面。 在他剽悍的七尺昂然之軀中,根本就躲著個內在小孩,永遠長不大似地。 但如果讓任何一扇方便之門開著,尤其在深夜,無疑暗示著自己的一份妥協,然這份妥協的意義甚至都是她想像的;附會在他們之間那份難以定義的關系中。 她看看鬧鐘,已近午夜兩點,此刻的他,絕對又在某一家他經常光顧的PUB里,他曾經帶她去過那地方,一進門她便被眼前的景象攝住――在類似非洲原始叢林音樂的激盪鼓聲節拍中,只見一高挑冶艷的金髪女郎正站在吧臺上;搔首弄姿作勢跳著脫衣舞,圍觀的羣眾瘋了似地鼓噪叫好,對那樣沸騰的夜,她滿是陌生。 在她還恍然之際,忽已不見他的蹤影,等再定睛找到他,竟發現不知何時他也色膽包天地跳上了吧臺;跟著金髪女郎女子的肢體擺動,配合著她象征做愛的姿勢,忘情挑逗地扭著。 她本能地臉紅了,膝蓋亦微微發著抖,直到她猛然被排山倒海的醋意與怒意擊中神經,她才力排眾人擠到臺前,伸手去拉他的褲管,并投以那金髪女郎輕蔑的一瞥。 女郎對他附耳悄悄說了幾句話,只見他猛搖搖頭,從他的表情大概可以得知她的弱勢地位。 稍晚在角落里,她直視著他那雙不安份滴溜轉的黑眼睛,感受到他年輕的身體里飽脹著一股熱,她不由得想起自己脫光衣服後的平板身材,發黑的乳頭,有著妊娠紋的小腹。 她泄氣地問:“你跟那女的說什麼?” 她問我妳是誰,我說妳是我的英文老師。” “英文老師?――”她無意識地重復著。 “難道不是嗎?”他的兩眼仍在整個PUB穿梭,時而舉杯跟她視線來不及追蹤的一些人打招呼。“不然呢?”他朝著經過的金髪女郎也舉舉杯,那女人回給他一個飛吻。 是啊,她無聲地瞅了瞅緊捏著酒杯使得根根青筋浮現的手背,猶記得出門前他還在門口倏地就反身堵住她;愛戀地將她圈在懷中微笑道:“妳早該照我的意思打扮打扮了,真高興終於妳拿掉那愚蠢的厚眼鏡,瞧現在的妳――多迷人啊――” 她輕巧地挽著他的手臂,仰著臉,一時間仿如回到了高中時代,且自信自己會是舞會中最教人羨慕的女主角,但此刻的她,完全被一波又一波涌入,就在眼前來來去去那麼多年輕,嬌艷,有著豐腴肉體的年輕女孩嚇到了―― 就算不照鏡子,她也莫名地覺得自己整個人簡直像張折了又折的;過期舊報紙,更恐怖的是,她幾乎感到一切裝飾都在坍塌,包括攏好的頭髪,假睫毛,粉粒,唇膏,它們受著可恨的地心引力一路拖曳著她矮到腰桿下,為他的視線再也不及。 即使是身上的迷你裙裝扮――他為她挑選的,現怎麼看都有如拉過皮般,異樣的青春中總透著一股老態,她無端地忽然憶起了那遁世已久的嘉寶。 “你――要在這――待多久?” “到天亮,”他灌下雙份威士忌,毫不遲疑說:“ 既然來了,就玩個痛快,妳看妳,光杵在座位上,一點音感都沒有嗎?亂掃興一把的――” “跳啊,”她被自己的聲音嚇了一跳,好似靈魂忽撞回軀殼里,努力一震精神:“不就是來瘋狂一下的嘛,呵――” 在狹小的舞池里;她緊挨著他跟前跟後賣力地跳,基本上她是非得佔據今晚那個女主角的位置的――那象征著一個遙遠的;對得起自己的義無反顧。 半瞇著被汗水泌進的眼,她想到了教他英文的第一天,她正襟危坐,他卻百般用眼神和肢體干擾她。 “妳知道為什麼在這麼多應征者中我選了妳嗎?” 她搖搖頭,心暗忖著,真是有錢人家孩子的口氣啊。 “因為妳跟我一樣,都戴著面具過日子――”他見她不語,接續道:“我知道我一無是處,就是個大家眼中的紈绔子弟,我也很清楚我父母對我期待不小,尤其我爸,但是――我真的不想繼承他的事業――妳看看,這國貿英文書多厚啊,讀的真無聊,如果是――教我一些莎士比亞十四行英文詩還有點意思――” 桌面下,他的腿有意無意地與她的相觸,她話說著回著也不知怎地猝然跌進空白,接著,一股憾人的熱力導電般通身穿過,她吃驚地抬眼望他。 他的手居然放在她的大腿上,一對黑眼珠牢牢盯著她。 “你這是幹什麼?拜托,你爸媽還在客廳里――” “怕啥?”他的眸子閃耀著狡獪,滿不在乎:“我看得出來妳很寂寞,何必不承認呢?妳――是不是一個人住?” “問這個幹麻?” 她讀出了他眼中的意思,壓低嗓門微微厲聲道:“休想!” “晚上回去後等我電話。” “少來這一套。” “等我電話,我會去找妳――”幾近命令的語氣。 “你瘋了!” 但事實證明,是她自己瘋了,因為就從這個晚上,她開始了漫漫長夜的等待,其實第一夜,他根本沒來,而她居然失眠了許久。 再見他時,她隻字不提,奇怪的是他好像也全忘了,道別之際,只見他行色匆匆,急著去赴不知那個人的約。 清晨近四點,他的電話來了,背襯的是PUB里吵雜的音樂,他像坐了一晚,等不到馬戲團開場的小孩:“今天這里的生意真差――無趣極了,我好想妳,怎麼辦?――我現在馬上去找妳好嗎?” “不好!”她喉嚨沙啞,僵硬地說:“我不會允許你這麼做。” “妳在生氣我上次沒來?” “我不懂你在說什麼?以後你――” 他打斷她:“因為妳認定我會來的,但我只是說教妳在家等我電話,沒確定是那一天啊,其實妳――還在等我是不是?” 她呆了呆,憤而掛了電話。 電話又響了,她開始數――響到第十九聲時,她再也按奈不住接起。 “響十九聲是妳的原則?”他在那頭輕笑。 她深吸一口氣:“你是個魔鬼,我上次看過一本書,你有反社會人格,其實你不知道自己是誰,因為你身體里住了個惡靈,老天保佑你――” “我老媽也一天到晚替我燒香拜佛,哈,真高興他們就要出國環逰世界了,好啦,不跟妳廢話,我馬上過去――” 她嘴里詛咒著,行動卻一點也不含糊,光著腳板跳下床,翻箱倒柜找著某件記憶中買了一直沒穿的性感睡衣,從那活潑的舉措中;她有種羞恥的快樂,但事實上,她似乎并不想仔細分析自己的心理。 他一進門就踉蹌地撲到她身上,夾帶著一股沖鼻的酒氣:“我討厭那些女人,亂七八糟什麼玩意嘛,為什麼她們個個都那麼主動?我――又不懂得如何拒絕――事實上我不喜歡和每個都上床,真的――” 他渾身滾燙,像害了熱病一樣,她吃力地扶著他到沙發上躺下。 “我――先去替你倒杯水――” 他一把拉住她:“不許走――告訴我,怎麼才能拒絕――她們?——” 她一時又羞澀不已,覺得自己身上的睡衣簡直正昭告全天下;有關她的癡心妄想和欲望難挨,他口中的“她們”,難道沒有“她”的成份嗎? 隨手抓了件外衣披好,她坐到他身邊,她內在那個其實也始終存在的天使部份因為他的受害而煥發了,她拍拍他的手安慰著:“在你――不肯定愛上一個人之前,試著不要隨便和她發生關系――因為那只是――發泄――真正的愛情是――不止發泄的――” 他依舊苦惱地看著她:“什麼才是――真正的愛情?――我不懂,或者我根本就――不會愛人――”他點點頭,似乎更確認了:“對,我會做愛,但不會愛人――” “不,你會的――”她握緊了緊他的手鼓勵:“但――這需要時間――需要自己去經歷一些――考驗――” “妳愛過人嗎?”他打岔:“我怎麼覺得――妳好像都――不相信男人?” “至少我不相信只有三更半夜才會來找我的男人。”她苦笑笑。 “那――我們――可以――白日見面,一起去――看電影,一起欣賞――夕陽――養一個可愛的狗狗――生一個寶寶――來疼他――”他的眼皮逐漸沉重,口齒也開始不清:“反正――不準妳――離開我―――” 熟睡的他,又恢復了個孩子樣,但這就是她的罩門;她多需要去疼愛一個孩子啊,然基本上那樣的疼愛也無法祛除等待那孩子長大後的曖昧私心,就有如她不困難地扮演著天使;或說接受這樣的自我暗示時,她的情欲之眼仍透過匙孔在努力張望他誘人的肉體,現在她總算比較明白何以她會如此看似輕易地淪陷了,很簡單,就只是;這麼多年來,還沒一個男人就直接相信她是寂寞地戴著面具的――即使寂寞之說已經這般地陳腐,甚至帶點唯物。 還有就是他青春的生命所散發的一股躁動,那股什麼大事都由明天擋著的只為今朝而醉的無謂,不然以她經年累月的沉穩,根本不可能有那麼多的蠢事可做。 這個夜,變得安靜而善意,她換了居家服,從書柜中拿了一本英文原文小說,作者是美國的福克納,翻到書簽處,正是“給艾蜜莉的玫瑰”,很久很久前她看到一半,福克納筆下的艾蜜莉有個年輕的情人,但兩人并不被祝福,其實她深諳不被祝福的東西,多半都為了成全人們自認為的幸福―― 夜深人靜,只有翻書的輕微沙沙聲,但故事到了結尾,她還是沉重了,就在這時,他也醒來,然後他好像什麼都想不起來地問:“我――怎麼會在這里?” “因為――你――醉了――”想想她平靜地加了一句:“我覺得你需要我,不是嗎?” 他起身,在她疑惑的目光中環顧著四周,接著讓她鬆口氣地說:“妳的――書真多耶――我喜歡愛看書的女人――” 她笑了,那應該是她的強項:“怎麼樣,想不想到我的世界里來――觀摩觀摩?” 他半認真半興味地聽她夸夸其談那些差不多滾瓜爛熟的各種故事,每個故事里仿佛都有她的影子,或是她深入後相依的靈魂,而在他聽來,也好似半真半假地的某個她,偶爾他會好奇地插句:“那個――黛絲姑娘怎麼會――如此傻啊?” “或許,男人不喜歡太聰明的女人――”她不正面回著。 “蛤,只是相處了幾天,這叫梅根的女孩就認為找到了真愛?” “有時,不是時間的問題,或者――愛情就是如此奇妙,沒道理的――” 聽得最入神的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他的面目因為劇情中人性的激烈衝突而有了一點世故的線條。 “看來――”他最後說:“我以後――應該會是妳一個最忠實的聽眾――”他張開雙臂,“來,為這些勇敢的主角們――” 他一直張著雙臂,於是她很自然地走過去,投入了他的懷里。 他們抱在一起,互拍著對方的背,但拍著拍著卻沒及時分開,或許這一切都是順著他們銜接了故事而內心有了本能續演的騷動。 續演下去就是雙雙倒到了床上,好似在補償著最初和最後的一點什麼,已經沒了誰主動誰被動的問題,但這真的不是她的本意,尤其在這樣美好的對愛多一點認識的時機――難道在自己說的未愛上一個人之前的所有還會為愛守貞的情操就如此瓦解?-- 她壓抑了生理的歡愉,因為無法不自責,在他軟癱在她身上時她忍不住落淚了,他先是訝異,後就用力緊緊抱住她,這一抱,又似有了天長地久。換他安慰她:“哭什麼啊,傻瓜,我又不會離開妳,妳別怕啦――”。 似乎是怕她的拒絕引來他的掃興;亦是怕她的應和引來他的輕視?她突然發現自己無論如何其實都是怕的――
------------------------------------ 但他真的沒離開她,至少在夜晚他會出現,但也是夜晚的一切替代了所有的白日活動,包括有一搭沒一搭的英文課程。 夜更深時,很多時候他并不想做愛,只想枕在她腿上,聽她的愛情故事,聽她將自己化為艾蜜莉的對年輕愛人的那些細碎絮語―― 她仿佛意識到;她必須和“那些只會跟他做愛的對像”有所區分的為他佈置一個別出心裁的帷幕,將他的好奇圈住,事實證明,他也確實被那些困頓的魂魄吸引,當他煞有介事地關心著艾蜜莉的愛人到底怎麼失蹤之際,她就覺得一絲兒希望隱然萌芽,甚至覺得,他和她之間,也不無因為做愛而更行放鬆或更加親密,這,未必需要太悲觀看待。 一次他要求她;能否教他寫一封英文情書,當在文中他提示加進“一起去看夕陽”等類似他說過的像承諾的話,她的心不免怦然而跳。 “――愛妳至天荒地老――”他喃喃照念著尾句,既而低頭稍縱即逝地閃過一個奇特而溫柔的微笑表情。 再見到他時已是一星期後的事了,當然還是深夜,一通電話讓她發了瘋似地趕到了醫院,卻意外地發現那個在PUB中的金髪女郎已先行一步到達;正被擋在手術房前,只聽見她對著緊閉的門大聲泣訴:“都是我不好――我不該跟你吵架的,不應該出手打你,更不該搞失蹤――你走後我才看到你給我的情書,你寫得真好――我也愛你,Michael,我是真的愛你――我知道你受不了那個糾纏你的老女人――沒關系――等你復原了,我們一起離開這兒――” 她佇立在一旁,下意識瑟縮著,接著茫然地伸出手,似乎想扶住什麼,又似乎忘了想扶住什麼,忽地眼前一黑,就滑進了一片空白中--- 待她幽幽轉醒,映進眼簾的是一位剛剛進門準備來替她量血壓的護士。 “啊,妳醒啦?還好――妳的傷不算重――應該是車子的安全氣囊保護了妳――” 她尚有點昏沉,皺起眉:“安全氣囊?――我――很久沒開車了――這怎麼回事啊?” 女護士耐著性子據實以報:“妳昨晚――深夜開車時――呃,撞傷了一名男子,如今他的――昏迷指數只剩三,尚未脫離危險期――小姐,妳都――記不得了嗎?其實他也在我們醫院里――目前我們已從他的外國女友那聯系到他的父母――” 她呆愣了許久了才木木地問:“而我――也是一直昏迷到現在嗎?” 護士點點頭:“嗯,救護車送妳來時妳已經昏迷了,就一直躺在這,醫生跟我都有來看過妳,妳有輕微的骨折現象,所以不能亂動哦――” “我--”她努力回溯著一些東西――手術室,金髪女郎,情書,老女人,離開這兒,天荒地老,――以及――那通詭異的;致命的深夜電話―――及此,她突地被記憶的黑洞捲回至一聲伴隨著緊急剎車;裂帛般尖叫的停格上,她四面八方地尋聲而去,終於發現了;一面正在碎裂中的鏡子里的自己-- 如同被毀容一般的從來也沒這麼恐怖難看的自己-- “小姐,據目擊者說,當時妳的車子開得很快,而且――好像被妳撞到的人――本來是想上前跟妳說話的,因為有看到他――在跟妳揮手―――妳卻――呃,妳真的什麼都――記不起來了嗎?” 護士等了她許久,她才慢慢地,慢慢地搖搖頭,然後無辜地望向眼前的世界――― 是的,她-什麼――都――記--不--得――了――。 她唯一只記得,艾蜜莉的地下室,躺在的是;她已經死去多年的年輕情人。每天到深夜,她都會送一束美麗的玫瑰花去;一起在那靜靜地陪伴著他。 在那樣的時刻,她覺得自己挺美。
第一第二張圖片來源:感謝函吉子先生提供。 黛絲--“黛絲姑娘”,哈代著。 梅根--小說“蘋果樹”中的女主角”。 |
|
| ( 創作|另類創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