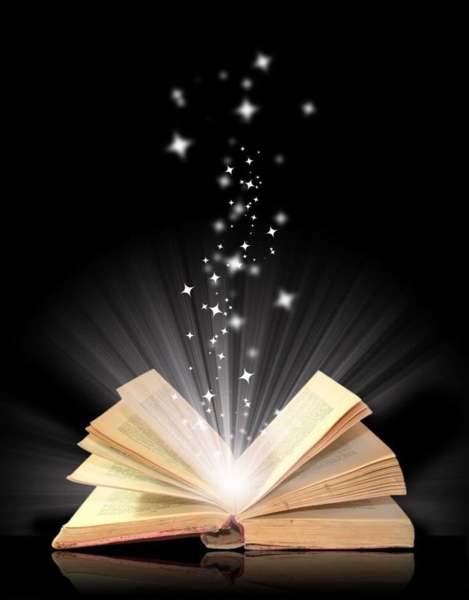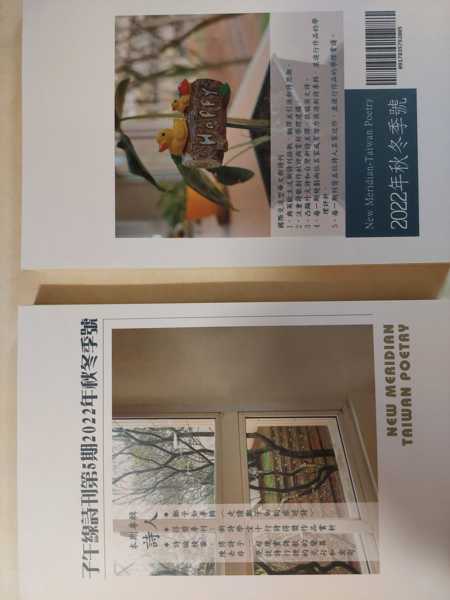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3/02/12 18:21:21瀏覽80|回應0|推薦0 | |
〈漫談詩行裡的亮句和金句〉 ∕陳去非 無論傳統詩詞或新詩,舉凡能夠流傳開來,成為膾炙人口的詩詞作品,檢視這些作品時,絕大多數詩行裡都必定有「擲地有聲」的亮句,甚至是沁人心脾的金句。而這些亮句和金句,在詩行裡不僅有「點石成金」或「化腐朽為神奇」的魔力,更重要的是,它們往往會烙印在讀者腦海裡,即使不記得整首詩的脈絡,起碼記住了這些閃閃發光發亮的佳句。 讀者或許會問:「如果詩行裡,找不到這類具有亮度的句子,結果會如何?」筆者就學理和創作經驗如實回答你:「這樣的作品,頂多就是分行散文,連散文詩都搆不上。」,任何一首被讀者稱許為佳作的詩詞,大抵都必須有一兩句以上的亮句或金句撐場面,對於詩人詞家而言,在詩行間布置亮句或金句,不只是創作策略上的必要條件,幾乎已成為基本配備了。詩行裡的亮句和金句越多,相對的詩的質感越佳,可讀性越高。 亮句和金句如何區分呢?按筆者讀詩和寫詩經驗,亮句是指「詩行裡具有審美價值的句子,語意儁永,值得玩味」,金句則是指「有亮度的句子,語意警策,發人省思」。金句是比亮句更具有暗示性,語意更豐富深刻的亮句,也就是精華版的亮句。以下這些詩例,都還只是亮句而已: 鄭愁予的〈山外書〉末段: 我是來自海上的人 山是凝固的波浪 (不在相信海的信息) 我的歸心 不再湧動 「山是凝固的波浪」是這段落裡的「亮句」,它的亮度來自視覺上的「形象化隱喻」,藉由「類似聯想」,把「山」和「凝固的波浪」聯結起來,產生美感。 又如管管的〈蟬〉 他把今年在對面山上 裝進錄音機的蟬聲 拿出來 讓孩子們 烤火 這首短詩亮度很高,語意耐人尋味,美感來自兩個方面,其一是經由感官移覺,聽覺的蟬聲轉化為視覺和觸覺的烤火;其二為能量轉化,由聲波轉化為熱能,這已是蒙太奇的奇幻表現手法了。 又如洛夫的〈金龍禪寺〉: 晚鐘 是遊客下山的小路 羊齒植物 沿著白色的石階 一路嚼了下去 如果此處降雪 而只見 一隻驚起的灰蟬 把山中的燈火 一盞盞地 點燃 洛夫這首名作,整首詩裡亮句至少有三處,讀者你能找出來嗎?讓筆者一一為你解讀: (1)晚鐘/是遊客下山的小路 這兩句,其實是從一句分拆出來,為強調「晚鐘」而作此分行。這句子的亮度來自化聲為形的通感,把屬於聽覺的晚鐘,悠長的餘韻,聯結上視覺的下山的小路。如果你不懂「通感」辭格,就會被句中的「是」誤導,以為這句只是尋常的隱(暗)喻。 這三句,先使用擬化法裡的「物擬他物」,把羊齒植物(蕨類)擬化為羊,然後才有「一路嚼了下去」這個延續性的動作。如果把動詞「嚼」字,改為「蔓延」,就會變成尋常的視覺摹寫,原先的擬化法裡「羊群嚼草」的動作消失了,「別開生面」的趣味就跟著不見,可見「羊齒植物∕一路嚼了下去」這組亮句,在這小段裡,對讀者具有「清新耳目﹑提神醒腦」的作用。 (3) 一隻驚起的灰蟬∕把山中的燈火∕一盞盞地∕點燃 一隻驚飛起的灰蟬,竟然能夠點燃山中的盞盞燈火,這畫面相當奇幻,正是洛夫式的超現實魔幻筆法。因為魔幻,能夠吸引讀者的眼球,這類型的句子往往會有令讀者耳目一新,甚至瞠目結舌的效果,當然也是具有亮度的句子。
候鳥的來臨
二、讀者如何認定詩行裡的亮句和金句? 讀者閱讀詩詞文本時,究竟如何發掘並認定某些行句有亮度呢?多數讀者會說:「就是讀到那幾句詩行時,有不同於散文句的感覺啊」,再問讀者「到底有哪些不同的感覺」時,讀者往往不能具體的回答,因為他們多半並沒有接受過修辭學訓練的背景,也就是他們的閱讀,因為所受的訓練有限,理解能力相較於詩人和詩評家是薄弱的、含糊的,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 三、亮句或金句怎麼創造出來? 「散文化」是每個詩作者,面臨讀者質疑時,必須應對的課題。解決「散文化」的辦法,不外乎在詩行間,適當地使用一些具有提升詩句質感的表現手法(形式設計和表意技巧),創造出一兩句以上的亮句或金句,以取得美感上的加分效果。詩作者如果不熟悉且不會應用這些表現手法,而只停留在尋常的感官摹寫和比喻,那麼他所寫出來的文字,就會缺乏詩句所具有的質感,淪為白描下的記敘性質的散文,即使勉強分行徒具新詩的外觀,也不會被讀者接受,被詩評家認可。 幾乎沒有例外,任何一首膾炙人口的新詩,詩行裡比定有至少一兩個具有審美價值,也就是亮度較高,讀起來有感覺的詩句。很難想像一首詩,詩行裡的句子均平淡無奇,甚至枯燥乏味,卻還能令讀者留下深刻印象,認可為佳作的案例。絕大多數讀者初讀完一首新詩,能夠在腦海裡回想到的,首先就是詩行間那閃閃發光的金句或耐人尋味的亮句。有亮度的詩句,從表現技巧層面考察,毫無例外地都必然有一些修辭格的運用:主要為表意方法,次要者為形式設計。表意方法諸如初階的「摹寫」﹑「擬人」、「隱喻」﹔中階的「轉品」、「示現」、「雙關」、「借代」、「反諷」、﹑「對比」﹑「拈連」、「映襯」、「互文」、「設問」、「婉曲」…以及「虛實互補」等﹔高階的「通感」、「誇飾」、「象徵」和「超現實」。從語意層考察,這些有亮度的句子都不會只是簡單平直的白描:感官摹寫或淺顯的明喻。 亮句和金句,所具有的意象美感和動人心弦的語意,正是從表現技巧而來。筆者按照前面所提示的三階表現技巧,分別舉例並分析這些亮句裡的亮度和含金量。 (一)﹑初階表現技巧︰使用摹寫﹑比喻或擬人等辭格 詩人接連使用三個比喻,三個比喻形態各自不同,「神祕似夜」是明喻,「神祕是魔」是暗喻,「神祕 一隻黑蝙蝠」,則是略喻;「纏住你我心中的黑洞」是喻解。詩人熟諳比喻的不同形態,由淺顯的明喻到深暗的略喻,層層提升比喻的層次,就語意的由淺而深,這段詩行也可算是另一種「層遞」形態。由於比喻使用得層次井然有序,使得詩句呈現層次的質感。
和悲涼-白靈〈金門高粱〉 金門高粱,味道辛辣酒質醇烈,「每一滴都會讓你的舌尖/舔到刺刀」、「入了喉,化作一行驚人的火」,這兩處的味覺摹寫相當地形象化,舌尖舔刺刀是形容高粱的辛辣,而喉嚨如烈火在燒,則是形容酒質濃烈。 2「太師椅」被賦予人性,開始緬懷昔日的光榮。這是無生物的擬人,可以使原本冰冷無情的古董,變得溫馨且具有人性。緬懷昔日的光榮是人們共通的弱點,當太師椅被「人性化」,「他」就同樣地具有人性和人性的弱點:念舊和沉緬於美好的往昔。 (二)﹑進階表現技巧︰使用轉品﹑示現﹑反諷﹑對比﹑雙關﹑互文﹑虛實互補…等辭格 「星空,非常希臘」是詩人余光中早期的「名句」,「希臘」原是名詞,在此被轉類為「形容詞」,意思也變成「浪漫」、「典雅」。此句若還原為「星空,非常浪漫、典雅」,則變得平淡無奇。 2)懸想 寒風像死亡一樣吹著的大街∕混入千千萬萬雜亂急促的呼吸中∕千萬種陌生的語言,湧進我們之間∕你不安地醒來。-鴻鴻〈今夜你側身而臥〉 這段詩行充分運用同時異地的「懸想示現」,把身處不同空間的人事物,以隔空揣想的方式敘寫出來,「今夜,假如你側身而臥」後面所敘述的景物和事件,毋寧都只是作者的想像。直到「當你睡得更深,我已經走上/寒風像死亡一樣吹著的大街」,才拉回作者現在的空間,敘述作者現在的行止和活動。「懸想示現」是空間的穿梭轉換,尚不涉及時間點的易動。
分給相好與不相好的男子∕穿窄窄的法蘭絨長褲的男子∕打網球的男子,吻過就忘的男子∕負心的男子。只是瑪麗亞,你不知道∕我真發愁靈魂究竟給誰才好-瘂弦〈瘋婦〉 這首詩給筆者的感受是「笑中帶淚」,心情錯綜複雜。詩人刻意以第一人稱的角色,來擔綱演出「瘋婦」,瘋婦自然是精神狀態時好時壞,所以詩人講話的口吻有時必須故意「顛三倒四」,有時卻得「一本正經」,「顛三倒四」的言語固然令人為之捧腹,但即使「一本正經」地說:「我的眉為古代而皺著/正經的皺者」、「我真發愁靈魂究竟給誰才好」,還是沒有讀者會把她的正經話當真。整首詩的氣氛是詼諧的,由瘋婦的自言自語一段一段帶出情節,但故事的背後,詩人的用心卻是人道且悲憫的,詩人知道我們的社會並不曾公平、正面地看待「瘋婦」、「棄婦」這些卑微而弱勢的人們,詩人要讀者在「笑聲裡反省」,我們該如何幫助社會上,這些卑微而弱勢的人們。 「雙關」的語詞,不必然帶有「諷刺性」,必須從語詞上下文的語境裡去推敲。這首短詩,從詩題「政客」和「銅幣」這個隱喻,以及「你漸漸/喪盡顏面」這個「喻解」去推敲,讀者會發現「銅幣」不僅具有多義性,諸如:「從政理念逐漸模糊,不再堅持理想和立場」、「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越來越不要臉」;而且語意深層還含蘊著對政客「喪盡顏面」的「非議」和「嘲諷」。 「隱花植物」此一主題,即寓有兩個不同的命題:「隱花植物的本身屬性:不能開花」及「被壓迫的卑微的人們:不見天日」,這兩個命題,性質上有著「物理的共通性」和「命運的共通性」,足以引起讀者自然地聯想,而推理出隱藏在主題背後的詩人原意。在這首詩裡的「隱花植物」並不是「先天」就是隱花,它是長期被無情地覆蓋、打壓之後,才逐漸退化為「隱花」的狀態,從首段「每一次開花/就被覆蓋在灌木葉下/見不到陽光」的線索,即可推理得知。
∕從民生路到民權路到民族路∕僵持在潮濕的夜色裡-李敏勇〈戒嚴風景〉29 此段詩行裡所呈現的是「平民與軍警」的對比,亦即「手無寸鐵和瓦斯槍催淚彈」的「對峙」。在戒嚴時代後期(約1980年以後),群眾的「街頭運動」逐漸湧現,此詩記錄了這一段抗爭年代的歷史。時至今日,台灣的民主政治逐漸成熟,街頭運動(示威或抗議遊行)已經司空見慣,執政的政黨不再隨便動用軍隊包圍彈壓示威抗議群眾,警察也不再扮演鎮壓角色,頂多只是「維持現揚秩序」或「避免立場相左的雙方群眾爆發肢體衝突」。
3)嗅味覺轉移 「髮香蜿蜒而來/如清泉流過唇際」是香味與味蕾在想像中的遭遇,嗅覺往味覺的挪移與混合。善用感官挪移(通感),可以激發創意、導引聯想。詩人用鼻子湊近去嗅妻子的髮香,卻把髮香比喻成清泉,蜿蜒而來流過唇際,可以真實地嚐到,這樣的手法,的確令筆者激賞。 初讀此段,會誤以為這只是尋常的視覺摹寫,透過明喻的形態來聯結兩個視覺意象。其實,詩人使用了「通感」,把對乳房的柔軟「觸覺」,透過明喻轉形為「視覺」的青草地。「春天的青草地」雖然性質上偏向「視覺意象」,但意義相當豐富而多元的,如茵的綠意是「視覺」的,青草的芳香氣息是「嗅覺」的,青草的柔軟觸感則是「觸覺」的。如此,在解讀這個「觸覺轉形為視覺」的通感時,就不能畫地自限,只留意青草地的「視覺」部分。 5)感官多重交感 共傘的日子∕我們的笑聲就從未濕過∕沿著青桐坑的鐵軌∕向礦區走去∕一面剝著橘子吃∕一面計算著∕由冷雨過度到噴嚏的速度-洛夫〈共傘〉 這首短詩也是使用「通感:感覺交錯」的實例,「我們的笑聲就從未濕過」,是將聽覺意象(笑聲)和觸覺意象(潮濕)相接合,以與前句「共傘」相互呼應。「由冷雨過度到噴嚏的速度」則是反過來將觸覺意象(冷雨)和聽覺意象(噴嚏聲)相接合,形成類似物理學上的「可逆反應」,這種結構設計,相當罕見。足見詩人洛夫除善長使用「夸飾辭格」之外,對於「通感:感官交錯」的掌握也相當老練。 直到一盞茶也清醒了∕故事是雪釀的,火鑄的∕說出來:如煙-李進文〈如煙〉 「故事」本是偏向「聽覺」的意象,詩人卻以「雪釀的」味覺形容詞和「火鑄的」視、觸覺形容詞來隱喻,使得這個故事變得不僅有味道和觸感,而且還是火辣辣、熱騰騰的。這裡已從「聽覺」向「味覺」、「觸覺」和「視覺」做了感官的挪移。詩人意猶未盡,又來個兼具「視覺」和「嗅覺」的「如煙」的轉形,所有「通感」的感官全數派上用場,形成多層次的感覺挪移。短短三行,就能把通感的手法一網打盡,可見這段詩行的語意是非常豐富且耐人尋味的。
被整座空山接住-余光中〈山中暑意七品:之「空山松子」〉 這段詩行的前半,感覺若說書人的「故佈疑陣」,而「說時遲/那時快/一粒松子落下來/被整座空山接住」則是故事突然揭起的一個「高潮」橋段。一粒松子落下,詩人沒伸出手或者來不及伸出手去接住它,於是在它滾落山谷發出幽幽回音之際,才醒轉過來,以另一種寬懷的心情去面對方才小小的突發事件。詩人使用空間的擴升式誇飾,說整座空山攤開手掌去接住一粒落下的松子。這種想像奇詭雄偉,頗能撼動人心。 往往,末班車過後∕天地之大也不過剩下∕一里半里路外∕遠屋的犬吠,三聲兩聲∕只有燈能體會∕這時辰,燈下的白頭人∕也是一頭無寐之犬∕但守的是另一種夜∕吠的,是另一種黑影∕只要遠一點聽∕─ 譬如在一百年外∕就聽得清清 楚楚-余光中〈山中暑意七品:之「不寐之犬」〉 這段詩行裡,詩人先使用「空間縮降式誇飾」:「天地之大也不過剩下/一里半里路外/遠屋的犬吠,三聲兩聲」,把天地這個巨大空間朝向「聲音」來縮降,這也是「變形式誇飾」,犬吠聲音的由遠屋傳來雖然是距離的測度方式之一,但同時天地卻不可能凝縮成「三聲兩聲」犬吠,足見它含有「性質轉換」的變形成分。後面詩人又再次使用「變形式誇飾」:「只要遠一點聽/─ 譬如在一百年外/就聽得清清楚楚」,用時間(一百年)做為測量距離的計算單位,作為飾體的「變形意象」:時間和屬於本體的「基底意象」:距離,兩者顯然不是同一性質的意象語,所以這也是「變形式誇飾」(超現實的時空交錯)的手法。 3超現實演出 1) 變形式組合 「變形式組合」意指不同性質的意象,比方時間、空間、距離、聲音、光線等等,經由刻意地組合後,產生出新奇且具有美感的變形畫面,傳達出「無理而妙」的意境。 山深夜永∕萬籟都渾然一夢∕有什麼比澈底的靜∕更加耐聽的呢?∕再長,再忙的歷史∕也總有這麼一刻∕是無須爭辯的吧?∕可是那風呢,你說∕風嗎?那是時間再過境∕引起的一點點,偶爾∕一點點回音-〈深山聽夜〉∕余光中 「可是那風呢,你說∕風嗎?那是時間再過境∕引起的一點點,偶爾∕一點點回音」,從風吹來時引起的回音,察覺到時間正在過境,這不是單純的感官挪移或者化聲音為形體的通感,因為時間並無具體的形象,這顯然是經過物質轉換後,變形式的意象組合。 2)蒙太奇剪輯 蒙太奇剪輯擺脫了時間和空間的線性束縛,把不可能同時存在的畫面接合起來,賦予新奇的創意。蒙太奇剪輯手法,使用在新詩創作裡,往往能創造出許多出人意表的新奇畫面,在台灣新詩人中,洛夫是使用這類表現手法,成就最為突出的詩人。 她 ∕被一根繩子提升為 ∕一篇極其哀麗的 ∕聊齋 循著簫聲搜尋 ∕每一個窗口都可能坐著 ∕她那位進京赴試的 ∕薄倖書生 ∕風來無聲 ∕她閃身躍入∕剛合攏的那本線裝書-〈女鬼(二)〉∕洛夫 一個上吊尋短的女子,這畫面何等悲悽,但是接下來的畫面卻剪接上「一篇極其哀麗的∕聊齋」,稀釋了讀者的悲悽情緒,同時把焦點轉移到哀麗的聊齋故事裡。「風來無聲∕她閃身躍入∕剛合攏的那本線裝書」, 閃身躍入線裝書的動作畫面,類似三D特效鏡頭,這已不是誇飾詞格所能解析,而是蒙太奇的剪輯手法。 3)超現實演出 超現實的演出手法,本身就具有不合常理的荒謬性,類似魔術師的變魔術把戲,但這類荒謬的畫面卻能被讀者的美感經驗接納,原因是它提供讀者一些有趣味性的言外之意,即使「荒謬無理」卻「妙趣橫生」。 下午。池水中∕擁擠著一叢叢懷孕的布袋蓮 這個夏天很寂寞∕要生,就生一池青蛙吧 唉,問題是 ∕我們只是虛胖-〈布袋蓮的下午〉∕洛夫 懷孕的布袋蓮竟然生出一池青蛙,這種無厘頭的連續畫面,不是物象的誇飾,而是超現實的玄思異想了,可讀者並不排斥這樣的奇詭想法,反而覺得新奇有趣。 久晴不雨∕此心早已龜裂∕如果你是凝聚不滴的淚∕我多麼想∕化為你眼中的魚啊-〈不雨〉 ∕洛夫 「我是你眼淚裡一條游動的魚」,這當然也是超現實的想像,但是這樣的超現實意象,卻給讀者一種蘊含深情的美感,讀者不需要以理性的思維去排斥感性的想像。 從前面列舉的諸多詩例,讀者似乎察覺到,詩人所使用的表現技巧如果越高階,詩行裡的亮句,意境層就會更豐富多元更耐人尋味,甚至成為金光閃閃﹑擲地有聲的金句。有心於新詩創作的文創者,借鑑前輩詩人不同層次的表現技巧,可以從中領會亮句和金句,如何從詩人的腦海裡推敲形成,從筆尖裡琢磨而出。筆者深信,這些亮句和金句多半不是「妙手偶得」,僅憑靈光一閃的靈感就能如願產出,而是詩人經過嘔心瀝血的推敲琢磨,適當地活用各類表現技巧,這其中蘊含詩人的生活閱歷和美感經驗,因為「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本文發表於子午線台灣新詩刊第五期
|
|
| ( 創作|詩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