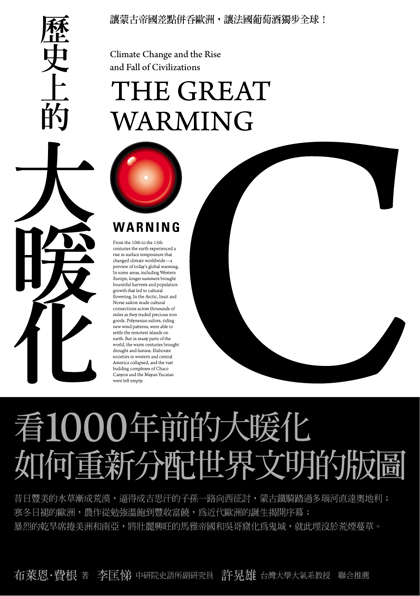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08/05/18 21:47:18瀏覽1404|回應1|推薦2 | |
第三章 上帝的連枷 在中世紀歐洲人眼中,向東方延伸的歐洲平原是個幾近陌生的國度,平原緩緩起伏,消失於遠處,最後沒入亞洲。那兒人煙稀少,居民大多居無定所,在很大程度上隨著乾濕週期變化而遷徙。 沙漠和半乾旱環境對降雨量極為敏感,即使是些微的變化,都會引發環境改變。降雨量多個二十五公釐,就可能讓沙漠邊緣內縮數百平方哩;幾代以來不見一滴水的地方,可能會出現死水潭。假設連續數年降雨量都稍高於從前,屆時會有牧草地突然冒出、成群羚羊在不久前還乾旱一片的地方吃草、游牧民在水坑附近和有青草的地方放牧綿羊和牛。然後雨量漸少,溪床乾涸,水坑消失,青草枯萎。憑著歷代傳承的經驗,牧民把牲畜趕到沙漠邊緣,趕到較有水的地方。乾草原、沙漠之類的乾旱地方,就像一具大幫浦。雨量即使只是些微增加,都讓沙漠迸現生機,從而吸引慕水、草而來的動、植物和人。這具幫浦就像個巨肺,或許可以屏住氣息一段時間,但最後仍舊要吐出氣息。於是乾燥天候重新降臨,把游牧民、牲畜、羚羊趕到沙漠邊緣。 歐亞乾草原是個殘酷的環境,易遭乾旱和豪雨之害,酷熱和嚴寒交逼。雄才大略的征服者成吉思汗就誕生於此,在中世紀溫暖期期間建立迅速擴張的大帝國。 橫掃千軍,所向披靡 成吉思汗自稱是「上天的連枷」。他是殘暴的戰士,以殺人如麻、堅不可摧的武力,橫掃中國與中亞的定居文明。一二二○年,他在中亞布哈拉(Bokhara)城的中央清真寺的講道壇上,向驚恐萬分的城民說:「各位要知道,你們已犯下滔天大罪,你們之中有頭有臉的人已犯下這些大罪。如果問我憑什麼這麼做,我要說因為我是上天降下的懲罰。」話語之中,顯示他非常熟悉被征服者的心理。 成吉思汗似乎就和旱災、瘟疫一樣,是上天懲罰的工具。他所到之處,基督徒和穆斯林無不恐懼臣服。成吉思汗展現了高超無比的征服本事。他「身材高大、孔武有力、體格壯碩,毛髮稀疏而灰白,有貓一般的眼睛,眼神散發出專注、精明、過人本事與理解,他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屠夫,公正果決的摧毀敵人者,大無畏、好殺戮、殘酷。」他比較希望敵人自行投降,如果不從,他只好訴諸殺戮。位於今北京附近的金國富庶城市中都拒降,成吉思汗即下令攻城,把俘虜放在第一線當攻擊部隊,然後把敵人的首級擲向敵軍陣地。幾年後,來到此地的某位穆斯林注意到重建的城市附近有座白丘,乃是中都陷落、放火燒毀全城時,數千名被屠殺者風化的骨骸。這位蒙古最偉大的征服者,率軍所到之處,無不血流成河。 這位偉大征服者出身寒微,靠著過人本事和心狠手辣爬上高位。當時,遼闊的歐亞乾草原上,散居著共約兩百萬人的游牧部族,他最初只是其中一個部族的首領。對游牧民而言,打仗是生活的一部份,他們騎馬作戰,能在馬兒全速奔馳時,從馬背上往任何方向射箭。他們是經驗老到的劫掠者、心狠手辣且極為獨立的戰士,聽從部族首領指揮。牲畜是他們的財富,部族首領只在積累這財富時,才跟其他部族結盟。一二○六年,成吉思汗獲推為蒙古大汗,一統漠北。他深富謀略,又善於行軍作戰、攻城掠地,也同樣精於管理。他很快就打破古老的部落結構,將部隊組織成如臂使指、掌控嚴密的標準部隊。他以十人組成十戶,作為基本作戰單位,然後依照十進位制,依序組成百戶、千戶和最大的萬戶部隊。部隊作戰,層級分明,命令層層下達不超過十人。蒙古兵能在駕馬全速奔馳時向任何方向射箭,以此著稱於世。每名騎兵身穿絲質上衣,外罩鎖子甲或厚皮衣,能有效防護箭頭刺入;頭戴皮盔或金屬盔,佩戴兩只以木頭和犛牛角製成的複合弓(composite bow)和至少六十支箭。有些蒙古兵帶著粗重的長矛、棒及短彎刀,還有些帶劍和長槍。作戰士兵攜帶自己的糧食、炊煮器具和其他裝備,全裝在一件用母牛胃製成、可吹脹的鞍囊裡。蒙古軍隊靠機動、計謀、聲東擊西,靠火藥製成、讓敵人震懾的鞭炮,攻城掠地。他們知道自己讓敵人聞風喪膽,善用這威名,加速取得戰果。 成吉思汗靠著個人威望、軍事才華,還有大家憧憬著征服、劫掠定居聚落能取得超乎想像之戰利品的心理,建立了王國。但最初,那只是由一些部落統合而成的王國。成吉思汗的部隊只花了二十年,就以驚人的速度和無情的效率,橫掃整個乾草原,並揮軍往南。一座座著名城市被夷為平地,經過千百年歲月發展出來的伊拉克灌溉體系,也被徹底摧毀。 成吉思汗的過人之處不只在於能征善戰,還在於他理解到帝國不同於王國,其運作有賴於穩定的政府、有效率的管理、乾草原與定居文明間繁榮的貿易,以及法律與秩序。他將日益擴大的蒙古版圖轉化為大帝國,帝國各地靠有效率的交通工具往來,靠隱而不顯的軍事威脅和其部隊的殘暴威名維持秩序。成吉思汗告訴其部隊,先征服再劫掠,而非征服、劫掠同時來。叛亂分子和被控叛國的首領,受酷刑懲罰。有時用毯子裏住他們,任由馬匹踩踏,或者像庫德族某首領,被五花大綁,抹上綿羊脂,然後任其挨餓,被蛆蠶食。 成吉思汗自認是上天施行懲罰的工具,但其實他迅如閃電的征討,有很大一部份不只要歸功於他的領導長才和領袖魅力,還得歸功於中世紀乾草原的氣候和倚賴機動、馬匹獨特生理結構的生活方式。沙漠的消長變化,引來乾旱、熱浪、酷寒與洪水,游牧民族的生活節奏則因應這消長而改變。這些生活節奏淵源久遠,在乾草原進入中世紀溫暖期那四百年的許久以前,就已出現。但成吉思汗的過人之處,在於努力讓所轄土地擺脫馬與無情沙漠的宰制。就此而言,他和他的繼任者至少局部獲得了成功。 變化莫測的歐亞乾草原 游牧民的舞臺是由多種地形構成的大片遼闊地區。它起於多瑙河畔,呈帶狀往東逶迤,愈來愈寬,成為伏爾加河東側中亞乾草原的一部份,最後止於七千多公里長的中國長城。乾草原涵蓋了多得驚人的不同環境,包括水源較豐、有蓊鬱林地的森林乾草原、開闊的草原、河谷、沼澤地與山脈。乾草原不適人居的北界,則有沼澤、開闊的凍原與綿延不盡的森林。在南邊,草原和沙漠從東邊的天山、祈連山往西,沿著烏滸河、伊朗高原延伸,最後止於黑海、喀爾巴阡山、多瑙河這些天然屏障。但乾草原的中心地帶,向來是沿著天山北緣和阿爾泰山南緣而分布的牧草地。一千五百多年前的錫西厄人時代,騎馬的游牧民族就已經策馬通過這些山脈的低矮山口,從亞洲進入歐洲。 歐亞大陸的大陸性氣候向來嚴酷,平均氣溫由西往東遞減。平坦地形、低降雨量、乾風頻頻吹送,使樹木無法生長。冬季長達八個月,乾燥、嚴寒、刮大風。無休無止的風,改變了覆雪的分布,但只是短暫改變。夏季酷熱,熱浪和乾旱司空見慣。往東越過烏拉山,氣溫降得更低,冬雪留在地面更久,氣候則乾燥許多。整個乾草原地區,植物以深扎入土的根系因應乾旱的環境,大部份的小型動物棲居於地下。古代的乾草原上有野馬、野驢,還有賽加羚羊,以多達千頭的群體成群移動。牠們只適度啃食乾草原上叢生的禾草,因而未危害到禾草的生存。但如今,牧草地被過度啃食(特別是春季土壤富含水分時),水分快速流失,青草幾乎蕩然無存。 乾草原生活不易,即使最有本事的游牧民也莫可奈何。成吉思汗能橫掃千軍、推翻國王,卻無法控制乾草原的現實環境,無法擺脫讓軍隊能閃電突擊的馬所加諸的限制。 對蒙古人而言,馬就是一切。馬提供肉、奶、乳酪、酸奶,甚至是酒的來源——馬奶發酵釀成馬奶酒。馬是財富、威望與強大的武器,最重要的是,馬讓人自由而機動。成吉思汗一統漠北之前,精壯結實的蒙古馬成為乾草原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已至少有四千五百年。 馬在西元前約三五○○年時馴化,比牛、山羊、綿羊晚得多。馴化的地點在乾草原邊緣,很可能在黑海地區,也可能在阿爾泰山(如今仍幾乎是考古發掘的處女地)。馬適應酷寒、積雪的能力,比其他家畜都高得多,而且從冰河期以來一直如此。冰河期時,草原上掠食者甚少,馬是這些掠食者最中意的獵物之一。然後,約西元前三三○○至三一○○年間,較冷、較乾的氣候週期降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同時發生大旱),使馬的馴化更為普及。不久,馬就成為乾草原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並改變了歷史。 騎馬是人類運輸方式順理成章的改變,也是革命性的改變。它縮短了人在乾草原上移動的時間,人們得以利用散布於廣大土地上的食物資源,活動地盤擴大為五倍,以往的行動限制變得可笑。乾草原上的開闊河谷等特定地方,食物資源可能很豐富,但這些地方之間隔著貧瘠、時而危險的大片土地。能夠快速橫越此一阻隔者,就能在乾草原上存活,但整個社會形態也隨之改變。此後,人可以輕易運送大量食物和其他物資,特別是除了騎馬,還搭配牛拉車之時。財富將根據馬匹多寡來衡量,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如此;相鄰部落間和部落與定居農民間的互賴程度提高,因為馬讓長距離貿易容易許多,從而成為奇貨可居的商品。特別重要的是,馬使劫掠者得以襲擊遠處的敵人,然後安全撤退,讓徒步追擊的敵人忘塵莫及。到了成吉思汗的時代,劫掠、偷襲和戰爭早已成為乾草原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延續了數千年。他的前輩是更早之前就縱橫乾草原的錫西厄人,也就是盤踞文明古典世界的典型北方「蠻族」。希臘旅行家希羅多德寫到他們殘暴的殺伐,描述他們割下敵人頭皮,把敵人的顱骨做成飲器,鑲上金子,掛在腰帶上。受攻擊時,他們立即逃入遼闊的乾草原,消失無蹤。 乾草原游牧民居無定所,因為久居一地,牲畜將過度啃食脆弱的環境,後果不堪設想。他們靠牲畜和馬過活,有時在適於栽種的地方種植穀物,然後置之不管,幾個月後再回來收割。但由於馬兒有天生的劣勢,牠們也配合氣候鐘擺的擺動,作出複雜的因應措施。 馬是便捷的代步工具,但因為低效率的消化特性,牠們也可能成為大累贅。牛進食有效率,排泄時只排泄掉所攝取蛋白質的四分之一,表示牠們攝食乾枯而低蛋白質的草,依然可以存活。馬吃進的蛋白質只有四分之一為牠們所攝取,其他四分之三全排泄掉。牛和馬都利用堪稱是發酵桶的東西,將植物性蛋白質轉化為能量。牛的發酵桶是瘤胃,位在體內食物尚未消化之處。在此,細菌分解植物性蛋白質(有不少藏在植物的細胞壁內)。剛分解的植物性蛋白質進入十二指腸,進一步分解為氨基酸。接著蛋白質進入小腸,被血液吸收,用在像是增長肌肉、提供胎兒營養等重要用途。馬的瘤胃位於後腸,食物到此之前已經過十二指腸和小腸,因此馬製造的氨基酸不多,不透過腸壁吸收大量蛋白質。馬攝取的植物性蛋白質在形同無用的位置被細菌分解,成為富含氮的蛋白質。這種蛋白質有益於土壤而非動物。 在正常情況下,乾草原上草料不虞匱乏,牛或馬都不需要留住所攝食的所有植物性蛋白質。但乾旱時,植物性蛋白質供應不足,青草有約一成五的蛋白質,枯草只有約百分之四。乾旱讓青草枯死時,保留蛋白質就變得極為重要。牛能保留的蛋白質比馬多兩倍,使牛在乾旱時更占上風。 從軍事或負重的角度來看,馬比較好用,但光是一季寒冬或一場夏季大旱,就可能死掉數十匹馬,特別是地面為深積雪所覆蓋或冬季草料短缺時。母馬無法哺育幼馬,沒東西可吃,幾個月後便開始死亡。乾旱不只讓具繁殖力的馬喪命,還使游牧民失去奶、乳酪和酸奶的重要來源。游牧民不得不食用馬屍。乾旱如果持續兩、三年,災情會更慘重。屆時游牧民找不到食物,馬兒又死光,又無法抵禦敵人入侵、劫掠他人,除了加入其他部族或餓死、遷徙,別無選擇。幾年後,會有數千匹馬死去。解決辦法只有一個,就是遷徙到水草較豐美之地,而這種地方通常在南方,位於農民墾殖土地的邊緣,或往往就在農民墾殖的土地上。
危及性命的乾旱 乾草原上的乾旱通常是北極區持續籠罩高壓系所造成的。這些高壓系有時停滯不動很長一段時間,使通常帶來降雨的鋒面系統無法通過,並從北方海域帶來極乾冷的空氣。凜冽的北極空氣加遽乾旱。例如一九七二年,中心籠罩莫斯科的一道反氣旋(即高壓)持續整個夏天不退,使大西洋的低壓無法通過。伏爾加、烏克蘭等地近乎沙漠的極酷熱天候,導致夏季降雨只有平均降雨量的兩至三成,相對濕度變得非常低。氣溫比正常值高出攝氏三至七度,帶走留在地面的水分。類似的大旱,無疑在這之前的幾百年裡也發生過。 中世紀游牧民很清楚年復一年的氣候變化。漫長而多雪的冬季,使牧草地寸草不生。寶貴的冬季草料得省吃儉用多捱兩個月,或者以愈來愈少的配給撐過好幾個月。牛靠著鋪在地上睡覺用的草料勉強填飽肚子,愈來愈瘦;有些虛弱得要靠游牧民幫忙才能站起;小牛死亡數目遽增;消瘦的牲畜凍死或死在深厚的雪地裡。碰上特別寒冷的冬天,人和牲畜都大量死亡;夏季則來得非常突然。雪迅速消融,草原變成爛泥地,溪水暴漲,妨礙游牧民移往夏季草場。氣溫遽升意味著少有水分滲進土裡,草長得差,夏草怎麼樣都不夠。面對這類災難,唯一的自保之道就是遷徙。在乾草原中部地區,游牧民於寒冷月份盡可能往南遷,好讓牲畜在最短時間內吃光草場的草。夏季時,他們北移至具有地利且遮蔽良好的河谷,因為那裡雨量稍多、草較豐美。 在乾草原上,水和水的分布也是攸關生存的變數。每個部族都以河域為中心――特別是河在乾草原上切割出來的凹陷河谷,來劃定地盤。河谷形同部族地盤的生命線。他們在低於草原的河谷蓋屋過冬,春季時北遷。在暖和的年份,有時二或三月就北遷,寒冷的年份則拖到五月才遷移。季節性北遷途中,若碰上不錯的草地,會停下一段時日再開拔,有時卻被暴漲的河水阻攔。最後,牲畜將抵達豐美的牧草地大啖青草,牧草地可能廣達八千四百平方公里。在暖和的年份,游牧民會播下穀子,然後置之不理,直到快南遷時再來收割。在乾冷的年份,他們沒有栽種機會,因為抵達夏季草場時,播種已太晚,若屆時還播種,尚未長成,就會在寒冷的天氣中夭折。 每一次的氣溫變化和雨量變動,都大幅改變游牧民與所在環境的關係。較乾燥的時期會出現可能危及他們性命的乾旱,牧草發育不良,畜群十之八九死亡,要到更遠的地方尋找水草,必然會入侵鄰近部族地盤,而入侵往往是動用暴力。在水分較多的時期,牲畜數目增加,草場承載能力大為提高,地盤縮小,戰爭隨即減少。千百年來,居住在乾草原邊緣的人,時時生活在兇狠游牧民的威脅下,游牧民尋找豐美的水草時,會毫無預警地出現,燒殺擄掠一番。 索爾達夫序列 令人遺憾的是,可供我們查證成吉思汗時代氣候變化的替代性資料,少之又少。 涵蓋此前一千年歲月的氣候紀錄,猶如古氣候學界的羅塞塔石碑,十分有助於我們破解過去的氣候,但這類紀錄鮮少得到編年史家應有的科學尊重。即使那些只是替代性紀錄,亦即古代氣溫和降雨的間接紀錄,仍然大有助益。對於尋找十年間氣候變化,和中世紀溫暖期之類上百年氣候變化的考古學家和史學家,這類紀錄序列是罕見的珍寶。欲探究成吉思汗展開殺人如麻的征戰時的歐亞乾草原氣候,相關紀錄仍然付之闕如,只有粗疏的推論和一、兩個樹輪序列可資運用。 紐約拉蒙特-多爾蒂地球觀測所(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樹輪實驗室的研究小組和國立蒙古大學人員,從索洛戈提恩.達瓦(Sologotyn Davaa)的五百年西伯利亞活古松,收集了多個樣本。那個地方又名索爾達夫(Sol Dav),位在蒙古中西部塔爾瓦加泰山高處。該地的生態環境極嚴峻,樹輪年年都受氣溫變化的影響。經過數月研究,該小組根據已有五百多歲(從一四六五到一九九四年)的活古松,得出一氣溫曲線。然後他們返回當地,從死去已久但保存良好的木頭中取得更多樣本,將從中得到的樹輪與活古松的年輪相連結。如今,氣候的紀錄序列已擴大回溯至西元八五○年,較不可靠的序列則回溯至西元二五六年,也就是羅馬帝國國勢正盛、錫西厄人活躍於歐亞乾草原的時代。 索爾達夫的古樹確切無疑證實了今日地球的暖化,因為一九○○至一九九九年該地樹木生長的速度最快。但西元八○○年左右,也有一些顯著的高溫期。整個序列裡,八一六年的氣溫最高,甚至比今日還高,但過去一千年裡,氣溫最高的一年是一九九九年。九世紀的溫暖期和十五世紀初另一個溫暖期,正前後概括了中世紀溫暖期那幾百年。一一○○年左右有段較低溫期,可見暖化時期並非只有高溫。接著,漸漸降溫的小冰河期降臨,地球進入升降溫變化不定的五百年,而以十九世紀期間酷寒的天候為最低點。 索爾達夫序列不只提供了中世紀的暖化證據,且該序列的變化,與著名的曼恩序列記錄的過去至少四百年北歐、西歐的氣候變化,正好吻合。透過保存良好的蒙古古松,我們得知成吉思汗東征西討時,正處於一漫長的溫暖期,期間頻頻降臨的乾旱可能大肆摧殘了乾草原牧草,使游牧民賴以維生的馬和各種牲畜面臨糧食不足的危機。若僻處一隅的蒙古樹輪序列,確切說明了成吉思汗時代氣溫、雨量的週期性變化(我們有充足理由認定確是如此),那麼很明顯的,乾草原的氣候幫浦發揮了數千年來未曾中斷的作用,促使游牧民在乾草原上不斷遷徙,使他們與南方鄰居起衝突。不同的是,這次成吉思汗在天候較乾燥、乾草原草場縮小之際,打敗了南方鄰族,稱霸天下。游牧民襲擾南方定居文明,自古以來屢見不鮮。但這一次,有位卓越的領袖應運而生,將原本相互殺伐的部落和各行其是的首領,統合為龐大的征服部隊。「上天的連枷」徹底撼動亞洲與歐洲。 從蒙古樹輪得出的漫長溫暖期,與成吉思汗殘暴征伐的時期正好一致。當時較熱、較乾的天候,意味著饑荒可能發生,社會日趨不安,促使殺伐更為頻繁。一二二○年和一二二一年,他入侵中國華北(金國),無情摧毀中亞塞爾柱土耳其人的花剌子模帝國,使蒙古勢力深入定居文明區。 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在去世前不久,吩咐諸子:「靠老天的幫助,我已透過征服,為你們建立一個龐大帝國。但我壽命太短,無法完成征服天下的大業,這就交由你們來完成。」他死後,蒙古人繼續東征西討。一二三六年,他第三個兒子窩闊台將帝國版圖更往西擴張。不久,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便攻占克里米亞半島,劫掠現今保加利亞和十四座俄羅斯城市,將這些殘破不堪的征服地納為附庸國。接著他將目光轉向歐洲,打算直抵「彼端最遠的大海」。驍將速不台統率的蒙古軍,兵分三路,征服波蘭、匈牙利,攻入奧地利,一二四一年準備直搗歐洲心臟地帶。就在這時,傳來窩闊台駕崩的消息。拔都有志爭奪大汗之位,旋即撤軍回到乾草原。最後他未獲選,轉而專注於鞏固烏拉山周遭的征服地,統治庫曼(Cuman)乾草原和數個俄羅斯王國,未再投身征戰。 差點併吞歐洲的蒙古帝國 拔都撤軍之際,正值較低溫、多雨的天候重返乾草原,使牧草地更為豐美之時。他的王國(欽察汗國)經歷數個世代的水草豐美期,戰爭不興,國內昇平。拔都一直未打消再度西征的念頭,但國內牧草豐美,使其子民擁有伏爾加河、頓河到保加利亞的廣大牧草地。牧草既充足,與南方的貿易又發達,征服的野心自然平息。 如果當時氣候鐘擺未擺盪到另一頭,乾草原的旱情加遽,情勢會是如何?根據更早的歷史來研判,戰爭和居無定所的遷徙會繼續,且幾乎可以確定拔都和麾下將領會重新西征。他先前派出的斥候,已讓他清楚掌握所要交鋒的王國底細,摸清那些王國軍隊的實力。那些軍隊配備一身厚重盔甲的歐洲騎士,根據以往的對戰經驗,根本不是蒙古弓箭手和騎兵的對手。他很可能會按照當初速不台所擬的計畫,先入侵奧地利、摧毀維也納,然後對付日耳曼諸公國,接著揮軍南下,入侵義大利。若一切順利,他接著會進軍法國、西班牙。不消數年,可能在一二五○年,歐洲就會被併入龐大的西蒙古帝國版圖。 這真的會發生嗎?蒙古人已在匈牙利平原的幾場決定性激戰裡,打敗驍勇善戰的歐洲軍隊,殺敵數千。蒙古人打仗如何殘忍、屠殺如何不分男女老幼的恐怖事蹟,歐洲人早已聽聞,在宗派林立和世仇宿怨而四分五裂的歐洲,這大概會讓他們未戰即心怯。拔都若真的攻下歐洲,當時的蒙古人不只會得到豐富的征服經驗,也將在同化、包容其他文化與宗教方面積累豐富的經驗。若中亞歷史可作為指引,隨著新征服者漸漸融入當地社會,歐洲文明會繼續繁榮。 但有趣的問題來了。歐洲屆時會成為伊斯蘭大陸,或者向來包容其他宗教的蒙古人會讓天主教繼續存在?如果蒙古人牢牢掌控了歐洲、歐亞統一在一個大帝國下、歐洲人走陸路就可以抵達亞洲,那麼,歐洲探險家和商人還會想開闢橫越大西洋和繞過好望角抵達印度的新航路,好繞過伊斯蘭世界汲取亞洲的財富嗎?蒙古人若入主穆斯林掌控的西班牙,會帶來什麼影響?由此幾乎能重現中亞的歷史進程,即伊斯蘭勢力大振,甚至往北擴張,越過庇里牛斯山。 或許在蒙古鐵蹄抵達大西洋之濱或更早之時,蒙古人會放慢征服的腳步。氣候鐘擺若沒有盪回到另一頭,蒙古人不會想回到飽受乾旱肆虐的乾燥家鄉,和平也不會降臨乾草原。 氣候鐘擺若沒有擺盪到另一頭,蒙古統治勢力的消長有部份將取決於游牧生活的現實情況,一如數千來一再上演的情形。水草豐美,和平就降臨;氣候惡化,乾旱摧殘乾草原,戰爭就爆發,定居文明的居民恐懼、戰慄。溫暖、寒冷的氣候,豐沛降雨、乾旱,豐美牧草、寸草不生,不斷交替,成為推動歷史的一大動力,其影響力和經濟變化、政治陰謀、個別領袖的才華一樣巨大。叱咤風雲的成吉思汗和軍隊,還有遼闊乾草原上最微不足道的部族,都擺脫不了氣候週期變化的制約。乾草原爆發乾旱的同時,造成社會動盪、出現不世出的將才,歷史於焉有了翻天覆地的遽變。要不是乾旱適時中止,歐洲文明呈現於今者可能是不同的風貌。
摘錄自野人出版《歷史上的大暖化》 |
|
| ( 時事評論|環保生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