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09/09/08 00:47:47瀏覽2100|回應15|推薦220 | |
「橫塘碧色逢霖雨。苒弱含方土。 怎忘得、水塘廬墓。血濺雙孤女。 四月,薄暮。 空闊僻靜的小蓬茅,清涼的薰風拂過廬舍前一池市畝盛開的荷塘,吹皺出層層漣漪。斗室前的曠地,茂樹的林蔭下,兩個八、九來歲的小女娃正乘著花棚下的秋千上下擺盪,沓沓笑語,不知不覺間那晃搖的小手竟顯得又急又快,偶而秋千相互碰撞,發出啪噠、啪噠之聲,兩女童更是一陣嘎嘎笑個不停。 當中著綠色布衫,垂著兩束辮子的娃兒,興奮地仰起粉嫩的俏臉向在旁的玩伴叫道:「姐姐,再來──再來──」只見紅衫女孩將小小身軀挪移了半寸,隨著下降的圓線適時擦過,臨危的樂趣讓兩娃兒玩到渾然忘我,仍覺得意猶未盡,欲罷不能。 兩名幼女是同父異母的姊妹,長女叫褚薇香,偏房庶出;么女褚菱香。兩人不過相差一歲。終日形影相隨,結伴嬉遊,倒也氣味相投,和樂融融,鮮少為芝麻小事爭鬧不歇。 褚薇香登時雙腳止於地,停下了秋千,輕蹙眉山,遲疑一陣才道:「妹子,有一件事……」這頭褚菱香仍接連回盪。未幾,她才綻開甜笑,露出了面頰上的小小梨渦,道:「什麼?」褚薇香望向妹子的黑溜骨碌的眼睛,搖了搖頭,半晌不語,心中暗想:「這件事還是不要讓妹妹知道好了,免傷兩人和氣。」
這時,窗外星光燦亮,碧華清冷地灑下一片銀輝,看來黑夜仍長。褚薇香輕拍了兩頰,旋即起身朝門外漫步走去。 直直來到爹爹褚尚鏗房外不遠處,一個嘶喝的女子聲音道:「老爺,來人是什麼人,您會不知道?」這語聲不單柔弱又甜美,如新鶯出谷,還入耳動心,十足扣人心弦。褚薇香知曉聲音主人正是褚大娘尹曼萍,亦是褚菱香的母親──一個年過三十卻風韻猶存的美婦人。 褚薇香一陣納悶,心道:「這麼晚了,爹爹、大娘怎麼還未安歇?」由於敵不過自己的好奇心,她悄悄蹲在窗櫺下,專心致志地向室內聆聽著的父親與大娘談話。未免諳武的父親察覺,褚薇香不敢過於貼近,只能屏氣凝神的遠遠蹲著。 此時只見褚尚鏗斜臥攲案,不斷把弄套在大拇指的韘,望著妻子身前方几上的瑯函與斷指呆呆出神。心中暗想:「信中寫道:『當月十二,必取褚氏五口。』明日不就恰好是十二?想我『毒王』褚尚鏗叱吒風雲三十多年,殺人越貨,無惡不作。平生仇敵不可勝計,一時間竟也想不起來欲滅我全家性命的兇手。倘若硬是要說,唯有十一年前……為了六萬兩黃金及數卷武學手稿便賣掉三瓶家傳秘藥『五毒兒甜釀』一事……這其間不但害死百多條人命啊……」 「五毒兒甜釀」,猛烈無比的毒液。昔年「褚家莊」傳子不傳女的獨有之物。遽聞此毒無色無臭,滋味醇厚回甘,還略帶蜜香。中毒後半個時辰內便會招來龐大蟲蟻兵團上身覓食,直到尸首腐蝕潰爛,化成一灘爛泥,連帶啃咬的蟲蟻亦會因餘毒而斃命。可謂殺人不見血,「毒王」褚尚鏗臭名遠播前,不少武林正道泰半喪生此毒之手。 褚尚鏗心中一動,暗忖道:「難不成……難不成那廝竟還活著?還記得當年販售五毒兒甜釀的時候,因懼買家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於是暗中減低了毒物的配量。這毒性雖不致死,卻也能讓尋常漢子抽蓄三日,直至全身經脈受損,武功盡廢,淪為非人啊…… 十五年前,青海白嶽門少門主解灁殺人之前,往往會差遣黃童小兒捎來戰帖,宣示內外。不過江湖謠傳白嶽門解家早已絕跡有年,連以記史的「雲家莊」屢屢派出探子勘查,皆是空手而回;而大夥兒這些年也不見門人出沒,更沒有解灁的形跡,是死是活一切成謎。 而眼前這『銀鷹公子』的行事風格或出身來歷,就猶如層層雲團遮蔽了毒花花的太陽般,令人摸不著頭路,是近日種種臆測不脛而走的主要因素。既然白嶽門少門主解灁吉凶未卜,而此致書人『銀鷹公子』又是誰化名? 啊,是了……這人明白有的,第一、除非『解灁』尚於人世,否則這封戰帖便是有心人特意匿名偽造;第二、這人必定和我有些恩怨、過節或者血海深仇;第三、這人肯定知道我賣藥始末,而且,清楚了解我後福家財散盡,遯跡山林過著隱居生活的來由;第四、這人武功不弱,恐怕在我之上;第五、這人確實是『解灁』,含垢忍辱多年,以『銀鷹公子』化名,到底展開一場雪恨……」 那邊尹曼萍遲遲等不到丈夫回話,熟知仇敵恐怕大有來頭,不覺手足發軟,渾身打噤,竟要淌下淚來。褚尚鏗起身扶住髮妻,語態和緩道:「娘子,事已至此,也不必過於擔憂、畏懼。一切都由為夫一人承擔,為夫的『蠙珠來入掌』雖不能睥睨天下,卻也非花拳繡腿、不成器的軟膿包。」褚尚鏗畢生雖惡貫滿盈,死有餘辜,但對夫人尹曼萍可道是全心全意,體貼入微,十足言聽計從、百依百順。 話說早年「褚家莊」是由一群褚氏綠林大盜所構成的幫會組織,平日靠做些歹事來維持家計。褚尚鏗從小便是血氣方剛、好勇鬥狠的少年郎,時常與生死弟兄一塊打家劫舍,幹盡所有姦淫擄掠的勾當。直到一日他洗劫龍塘埔,將若干女人擄回莊園肆意狎褻。那日,他不僅連尹曼萍的衣袂都沒摸著,還中了她的計中計,讓尹曼萍清清白白地逃脫「魔手」! 事後,褚尚鏗自然淪落成眾人茶餘飯飽的笑柄,暗暗吃了悶虧,為了湔雪前恥,他發奮圖強跟隨父親學習毒術,自創一種叫「花下醉」的媚藥,而通身上下全無武功底子的尹曼萍自是褚尚鏗的囊中物、甕中鱉。 然而兩人結褵數年,膝下始終無子。愛孫心切的阿翁立即強制壓褚尚鏗納寵,礙於現實無奈下,他只好奉父親之命與家道中落「鼓子巖山莊」的白家大小姐白菀珊完婚,不久誕下個兒郎。 大約一年後,五名身著黑袍,臉蒙黑巾的江湖劍客向他索取「五毒兒甜釀」,出身綠林的褚尚鏗深知來者心懷不軌,又敬懼敵手高強武藝,再加上豐厚報酬的誘惑,權衡輕重之下,終究昧著良心行事。直到莫約六、七個月後,江湖謠傳位在青海的「白嶽門」已在一夕間猝然匿跡銷聲,於江湖上除了威名。那頭官府又廣發通緝令,挨家挨戶訪拿兇手,雖不知兩件事是否有所關連,熟諳事情不單純的褚尚鏗,誠恐滅門家屬遺孤伺機復仇,褚家莊會無端殃及池魚,褚尚鏗不僅遣散褚家莊,還將長年謀取的不義之財撥發褚氏宗親,甚至不惜送走稚子,交由山野鄰里撫育。 為避免他人疑竇,褚尚鏗收養出生便是孤兒的褚薇香為女兒,以當作日後濫竽充數之用,也是交換獨子性命的替死鬼……孰料,人算不如天算,尹曼萍竟在當口懷有三個月身孕…… 這時尹曼萍顰眉道:「老爺,這廝賊人捎來根斷指究竟是誰的?又有何用意?」褚尚鏗一聲長嘆,提起右手將妻子拉到椅上,道:「想必是從那孩子手上砍下來的。嘿,咱們這些年來的所作所為都是白搭,這人不但全盤掌握了咱們一舉一動,甚至連咱們索盡枯腸、挖心搜膽捏造出來的李代桃僵之計都給通通看破。當中的用意嘛……只怕是先來個下馬威,令我們陣腳大亂,疏於防範吶。」尹曼萍瞧瞧桌上斷指,抓緊手中的絹帕,道:「為什麼這人會知道?這事只有你、我、白妹妹三個……」 褚尚鏗道:「恐怕中間生了變節。」尹曼萍顫聲道:「褚氏五口?咱們家裡若算了薇香可有六口啊……」褚尚鏗道:「信中挑明了誅戮褚氏房族,這人既知咱們把兒子交由鄉里照料,必是知道咱們薇香是抱養來的娃子……」尹曼萍一怔,乍然道:「老爺,你說銀鷹公子會不會是當年向你買藥的那五人之一?」褚尚鏗道:「自然有些可能。不知這些魔頭跟我有甚麼深仇大怨,竟連兩個孩子都不寬饒?尤其是菱香,她不過才八歲啊……若要殺人滅口,當年就能動手了,何必等到這麼多年?」尹曼萍道:「那麼……會是誰?」 褚尚鏗的為人某方面來說雖然有些奸惡,但是,打自娶了尹曼萍之後,篤愛妻子的大魔頭,不知不覺間心頭上竟也漸漸少了分夷戮,多了分仁慈。愛屋及烏的褚尚鏗,對自己女人與孩子,說來也是極好的,全視褚菱香為心頭肉,有求必應,可謂是倍加疼寵吶。至於褚薇香,褚尚鏗一直以來都有說不出的辛酸曲折。對她,褚尚鏗老是沒法兒真正疼入心坎,有禽犢之愛。或許,一方面她並不是褚尚鏗的親生骨肉;另一方面則是他小我的一己之私,深怕偏疼了褚薇香會對不住沒有雙親見憐的獨子。 乍聽自己不是褚家女兒的褚薇香,小小面龐早已愣怔著,緘口藏舌,再也無心留神父母的談話。未免給他們發現行藏,她靜靜的輕移步履,顧後瞻前,直到轉進了閨房,兀自吁了口長氣。她的珠淚方才一顆顆緩緩滑落,浸濕了粉亮的雙頰,細嫩的指尖撫過火燙燙的狀貌。接著,褚薇香快步飛奔至毛茸茸、軟綿綿的床鋪,將哭紅了的雙眼埋首於鏤金錯采的床褥中,讓爆發的嗚咽聲顯得格外靜謐。 她長長的睫毛,覆蓋著浮腫的目波,小嘴不斷囈語著:「爹爹、娘……」隨著那悲啼化成了淡淡哀思,有些哭累疲倦的褚薇香,這時倒是睡得十分沉穩,只剩下殘留的淚痕證明著這一切並不是場甜美的春夢,而是疾首痛心的噩夢……
果然不遠處,一個身穿黃色衫裙的婦人正翹首企足,眼光從未離開兩娃兒的所在處。褚菱香撅著小嘴,道:「好吧。」這才心不甘情不願地停下秋千,跟在褚薇香背面,朝家中閒步走去。驀地像遙想起些什麼,向褚薇香道:「菱香最喜歡薇香姐姐了,所以姐姐可別丟下我一個人喔,我們要永遠永遠一同鬧著玩兒,一同談笑。」她話聲才落,碎步上前,在褚薇香的臉蛋兒印下脣吻。 褚薇香一呆,道:「好……」正錯愕間,她的手已被褚菱香牽起,於是乎,兩個孩子手拉手,口中哼唱著簡易小曲,慢條斯理地回到廬舍。褚菱香當場放下姐姐的手,欣喜雀躍地奔到中年漢子面前,嬌聲叫道:「爹爹。」只見那褚尚鏗彎腰將愛女抱了起來,一對豆子般的眸子肆目細瞧著,神情甚為悲戚沉痛。褚菱香卻如小鳥依人般倚靠在褚尚鏗懷內,嗜好造亂的瑩澤小手兒,梳拉著父親下巴頦兒底下鬈曲的大鬍子。 褚尚鏗垂頭望著懷內掌上珠,他低啞的聲音道:「好了,去娘那邊吃飯去。薇香,妳也是。」兩女齊聲喊道:「是。」他一邊說著,一邊牽著褚薇香、褚菱香的小手,往飯廳走去。這頭尹曼萍早將平日豢養的土雞宰殺了,並揀選肥嫩雞腿輔以雞蛋、香菜、番茄及調料蒸、炸、燜慢火製作。尤其是烹製時,將雞腿用酒、鹽、糖和蔥薑略醃後,放進蒸籠至七成爛並取出晾涼,接著去掉大腿骨,裹上蛋糊、麵粉入油鍋炸至呈淺黃色時才將其撈出,放入蔥、鹽、辣油等調料,就成了道褚菱香十分貪饞的「油燜整雞腿」。 而邊旁的白菀珊雙手可也沒閒著,亦做了道浙江傳統名菜「帶扎魚筒」,乃因其取用帶皮魚肉,捲入三絲成筒狀,故有此雅名,而此菜色銀白,魚肉鮮嫩,湯汁清燉,香味濃郁。尹曼萍、白菀珊更著手烹調了清燉白菜、青紅蘿蔔豬骨湯和炒芥藍,兩人滿滿煮食一大桌。接著五人便將圓桌團團圍困,坐著吃飯。 席上褚菱香嘰哩呱啦的說不停,餘下四人則各有各的心事,鮮少發言,有時對褚菱香的問話更是虛應故事、敷衍搪塞。霎時之間,飯廳中只剩下褚菱香清耳悅心的一股聲音。 她嘟嘟囔囔好一會,忽覺無趣,止住聒噪的嘴兒,著手夾菜。那頭褚尚鏗似乎橫了心,長吁了口氣,道:「菱香、薇香,來,把這杯花蜜茶喝了──」隨即令尹曼萍端出事先參雜了毒藥的兩只杯子,而杯中的液體湧現一片金黃色澤。 褚薇香熟悉茶水恐有古怪,但覺能和妹妹一齊畢命,倒也樂觀其成。打自褚菱香出生,兩人便輔車相依,作伴優樂,情感甚篤。心想最好能一命抵過一命,代妹受罪,否則雙雙同歸九泉,也是件裨益的事。 而褚菱香好吃甜品,故不覺茶水有異。兩人正自聽話張口要飲,說時遲,那時快,兩枚帶有剛勁內力的碎石恰恰打中兩只水杯。頃刻間,那破裂滿地的白瓷杯,流出金黃瓊漿,散發陣陣香氣芬馥的蜜香。兩女娃兒驚得呆在當地,張大了口,發不出聲音。 褚尚鏗、尹曼萍、白菀珊三人同時大駭,不禁環顧廳堂一匝,始終未見來者身影。褚尚鏗提氣喝道:「打頭的是哪一個奸人?給本主兒滾下來!」他這番話以渾厚內力字字送出,明晰宏亮,奔馳如雷,仍舊沒有看到仇敵。連忙掉轉頭向白菀珊低聲吩咐說道:「菀珊,妳諳武,先帶薇香、菱香從邊門離開;我和曼萍替妳們斷後。」 白菀珊道:「是!」驟然醒覺,丈夫要自己帶孩子先走是假,實則是用兩條人命遷延對手,以讓她們有足夠充裕的時間擺脫追殺,然尹曼萍敢只是尋常村婦,這般行事,無異是羊落虎口,鑽頭就鎖。 此刻,白菀珊不禁悲從中來,親生兒子不但讓銀鷹公子治死,連丈夫臨死前選擇的伴侶仍舊不是她,枉駕自己為人作嫁多少年。回思了一回,白菀珊斂起自怨自艾的哀痛,排愁破涕,倏忽憶起丈夫交託的重任,自己責無旁貸。轉瞬之間,她便帶挾著兩個女娃兒悄悄離去。 見三人芳蹤如無形無影般消失,褚尚鏗、尹曼萍夫婦兩人這才氣定神閒,溫吞吞的坐下。莫約過了一盞茶工夫,尹曼萍才顫聲說道:「老爺,你道這敵人有何用意?我們既要毒死愛女,免得受人欺侮,但這廝小賊又搭救薇香、菱香……這、這可說不去啊……」褚尚鏗亦不明所以,當下只是安慰了尹曼萍幾句片言隻語,旋即才向屋內叱喝道:「咱們姓褚的是貪昧了巨富,害死人便害死人,何況老子一向是為非作歹的綠林頭子,有人送上錢來,不要就是呆子、蠢才。賊王八、兔羔子,快快當當給老子滾出來,來場背注一擲的生死戰,如此揜揜縮縮,威嚇婦孺,算甚麼英雄好漢?」 尹曼萍見褚尚鏗黑汗白流,便掏出手絹為他拂拭,柔聲道:「對……不……起……」這時就見尹曼萍背部不知何時中了金「箭」──一枚外似箭竹葉的金鏢,鏢身薄片頎長、輕巧鋒利。有倒勾,雕琢夸麗,金針尖上顯然淬入劇毒。 褚尚鏗心中悲慟,不斷喊道:「曼萍、曼萍。」但倒入懷中的嬌妻如今丹脣發黑,回天乏術,早已魄散九霄,繡幃香冷。褚尚鏗終歸落下了男兒淚,目眥盡裂,怒道:「出來──給老子滾出來──」他溫柔輕放著尹曼萍的屍身,便如瘋魔般在偌大的屋宇草率揮掌踢足,自亂了陣腳。 「出來──出來──」 褚尚鏗臉色發青,只道:「妳這小賤人當真該死行瘟,該死行瘟!速速還我娘子命來!看招──」褚尚鏗因愛妻慘遭毒殺,蓄恨難洩,當下使出蠙珠來入掌中的招式,著著向少女進逼。只見那少女不慌不忙,一味的向右側閃避,絲毫未有反攻的意思。 驀地,僅聽少女笑吟吟的問道:「欸,我說啊……這『箭竹金針』上的毒液比起『五毒兒甜釀』,究竟是誰能堪稱天下第一毒物?」便在這時,褚尚鏗左手呼向右方拍出,朝著那姑娘肩頭狠戾擊去,不料,她反身一轉,不偏不倚地正自躲過他劈來的掌風。就聽嘩啦聲響,打爛了幾盆室內植栽。褚尚鏗高聲喝罵:「姑娘小小年紀,心腸忒是歹毒。」當前又是左晃右繞,踏準步伐,順勢打向那少女左腹。豈料那少女蓮步輕移,一個觔斗,登時閃過,輕盈地蹤躍上了橫梁。 這下只見那少女嘴角彎起一抹鄙笑,輕蔑道:「怎麼不說你這『毒王』名號不稱頭?啊……是了,苟且偷安、飽暖生淫慾的日子過久了,連帶個把自兒醜事忘了……」少女一邊說,還一邊瞅著蔻丹,才接續道:「嘖嘖嘖……閣下厚顏無恥、死不認錯的功力,當真讓小女子大開眼界吶。小女子這廂可說是好生敬佩,忍不禁向前輩討教、討教幾招的意思。」這話,她說得劖言訕語,慢慢騰騰,待得語畢才慢條斯理地振揚手中長鞭,躍進場內。 褚尚鏗氣得勃然色變,喝道:「尊駕究竟是誰?」 那少女一雙冰冷冷的眸子向他直視,臉上毫無表情,啐了一口才道:「呸,我為什麼要告訴你?閣下根本不配知道!告訴了你,不正是羞辱了本姑娘那小小不言的薄名?」哪知褚尚鏗聽她言中有譏刺、嗤鄙之意,全然不以為意。左掌演幌,右掌直往那少女後心攻取,這一招「反掌折枝」卻是「蠙珠來入掌」中最為精妙複雜的架式,因原已出掌的手驟然更調其方位路子,致使敵人誤以向前擒拿,實際卻要劈擊仇敵未防之背腹。怎料,那少女身子若有似無地略微半偏,腳下一個踉蹌竟似躲過那致命一擊。被這麼一著,那少女稍加斂起玩心,以長篇連續擊向褚尚鏗項頸和肚皮,就在剎那之間,兩人已對拆了三十餘招。 褚尚鏗見她右手攻到,袖口鼓風而前,便如那依著風向的帆布等待張帆行船,威勢非同小可,突地大聲說道:「袖裡乾坤,果真了得!」他一語甫畢,一招「銜山吞海」,雙掌從橫裡向少女反劈過去,呼的一聲,已拍向她衣袖。但見那少女身形一矮,使出一招「借花獻佛」向他右腿打去,不料她這一鞭揮到中途,突然轉為「摘星換斗」,手腕一翻,直直打在褚尚鏗踝骨上。 又鬥數回,此刻兩人在每個瞬息便將攻擊和防守互換四、五式,褚尚鏗不禁臉色鄭重,暗忖曰:「臭丫頭當真邪得狠,截至目前為止,她仍未顯露出本門一招一式,不但功夫路數雜以河南殽山派的『搏手印』、安徽干道人的『疾風掃浪腿』、浙江鮮于家的『鮮于棒法』、少林的『小梅花棍法』、『八寶混元棍法』,還有福建沿海鄭家的『打魚棍法』與失傳已久的『拂紺紗十二路』、『十八路小綠玉杖』……如此舉止無疑是想隱蔽自己多年所學,即便再相鬥下去,也難免犬兔俱斃。」縱然隱逸多年,褚尚鏗對江湖掌故仍有一定的認識,還不至於淪為一隻坎井之蛙,因此能夠速即剖斷那少女使來的招式名堂。 忽地,只聽得「咻、咻」的聲響,褚尚鏗的左手腕上已然被刺破了一個極為細微的小孔,同時腹部正遭長鞭襲擊而來的力量震得倒退三、四步,一手撫胸,不禁連聲「啊」地慘叫,往地下吐了幾口鮮血,頓時已氣絕。 緊接著,女子掏來摺子,一個彎身,點燃了廬舍。 不過只是一霎時光景,便是烈焰騰空,含煙籠霧,褚氏屋瓦盡歸塵土。這時,那女子不住露齒大笑狂喜,久久不歇。過了半晌,才淡然地說道:「遊戲才剛開始而已……」 話音方落,已悄悄不見女子曼妙身影。
另一頭,白菀珊帶著褚薇香、褚菱香從小側門悄悄離開。一路行來,三人心裡始終惴惴不安,緊緊向前挨著,而這一二時辰奔馳,可謂馬不停蹄、快馬加鞭,奔得數里,才到一旁莽莽樹叢中歇腳。過了半晌,突聽得虛哩哩數聲,一枝響箭射上前路,三乘馬因受驚嚇而不辨方向,直直在林中亂竄。 就在這時,只見從前方彎道處捎來數聲暢笑,一道聲音低微沉重的男聲隨即傳來:「原來這兒還有三尾漏網之魚吶。」三人同時北望,乍聽這不疾不徐的朗朗高呼,兀自老大吃驚,久久不能言語。 白菀珊苦笑暗忖道:「莫非今日當真劫數難逃?注定命喪於此?」 當下天邊銀華灑滿在他身上,照亮了黑夜裡三道模糊的視線。只見那人身著綠色雲錦,腰配長劍,莫約只有二十八九歲。白菀珊怒喝道:「敢問閣下尊姓大名?」那年輕漢子謙和道:「不敢。山野鄙生,區區薄名,何足掛齒?」 就在此時,白菀珊瞥見遠處廬舍升起熊熊大火,深知丈夫褚尚鏗與大姊尹曼萍已命喪黃泉。於是道貌凜然的說道:「閣下既然要取褚氏五口之命,那是輕而易舉、唾手可得之事,不過在泱漭無疆的武林之中,孰是孰非各有公論。閣下總該言而有信,放了其中一個孩子。請!」自白菀珊得知親生愛子不但命斃於賊子冷箭,還連屍骨都不放過,簡直是痛澈心脾,夜夜以淚洗面,恨不得將仇敵大卸八塊、剝皮剔骨。 隨即一按劍鞘,鏘鏘一聲,抽出雙刃,切齒冷道:「出招吧!」她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只求手刃賊首,為丈夫、愛子雪恥報仇。而褚薇香、褚菱香兩女雖兀自感到害怕恐懼,仍舊一副傲骨嶙峋,倒也像極一條硬漢子,志氣凌雲,威武不能屈的樣子。 那年輕漢子心想:「久聞她『鼓子巖山莊』白家先祖所創的鼓子巖劍法輕盈靈活,身法之快,可謂日下無雙,難逢敵手。只是招式太過講究形勢,稍有華而不實、脆而不堅種種弊端。這頭可要好生留心用意……不過,她既已是我的囊中物,必是逃不遠。不如多留她一時半霎,鑽研一下武學套路也好……」 白菀珊又氣又急,當下更不客套,雙刃劍尖翻轉,登時連連使出鼓子巖劍法中的「哀江南賦」、「小園賦」、「蕪城賦」、「別賦」,節節進逼的劍法,一劍還有一劍,雙刃齊發,劍光爍亮,乍看正如六朝俳賦字句雕琢、行文駢儷的樣子,十分耀眼,然其中間卻有極大破綻。正當那年輕漢子與白菀珊來來往往拆了百來招,一旁褚薇香趁勢領著褚菱香向矮叢奔去而藏躲。 這時,那年輕漢子長劍翻轉,陡然拚刺,銀灰色劍花星星點點,不偏不倚朝向那套劍法七處漏洞擊出,只聽刷刷刷急攻劍刺,始終未下殺招。白菀珊舉劍擋禦,噹啷、噹啷數響,遏制那年輕漢子來勢洶洶的劍招,不料,她手腕一緊,硬生生捱了劈頭而來的利劍,頓時左臂酸軟,渾身無力,氣喘如牛。他搶將而上,已對準白菀珊羊脂白的頸項。 他長長吁了口氣,嘆道:「我既然答應妳放了一個孩子,便應守諾。」白菀珊扔掉雙刃,說道:「哼,成則為王,敗則為虜,事已至此,不如直接給我一個痛快!我不知老爺和你有什麼過節、深仇大恨,要滅門絕戶咱們姓褚的?……」只聽白菀珊話聲未落,一聲「啊」的慘叫,氣絕身死,伏維尚饗。 年輕漢子微皺眉頭,怫然不悅,冷怒道:「小丫頭,出來。」果然不遠處,一名女子緩緩從林中走出,盈盈笑著,十分標標致致,百覽不厭,而此人正是殘殺褚尚鏗的元凶。 只見少女雙手正提著褚薇香、褚菱香兩女頭首,宛如魔鬼現世,荼炭生靈。她眨著無辜雙眼,一副無所謂的笑道:「不過就是試試大哥新研發的『箭竹金針』玩玩嘛……怎知,又是一個禁不起『箭竹金針』的女人。無趣、無趣。」不時還見她倣效起文弱書生搖頭晃腦的模樣,自顧自說個不停。年輕漢子無力地搖了搖頭,過了良久,才道:「妳……」 少女斂起笑意,冷然道:「三哥,我知你近年閉關潛心修道,不太過問門中世事……」嘆了口氣,一揮手,又道:「但這當口可別忘了門主密令啊!即便你心腸軟,我佛慈悲,對人、對事且留三分情面,不忍痛下殺手,再這樣下去,難保不出岔兒。」年輕漢子冷口冷心說道:「屬下不敢忘門主之命,但妳也該知道褚薇香是無辜受累之人。若非褚尚鏗一己之私……」少女不等他說完,怒喝道:「不用你來教訓我。但你可別忘了山西千佛洞內所發生的大事……」喻少謙聽到「山西千佛洞內」這六個字,臉上忽然閃過一種難以言喻的神情,似乎是難過、是恐懼、是厭惡,又是立眉嗔目,最後才是一片大慈大悲與憐憫。 約莫一刻後,他才心平靜氣地嘆道:「丫頭,千佛洞內已是十二年前之事,何以舊事重提,多傷往事?」少女悲慟道:「只因此刻你起了惻隱之心……那一場惡戰,雖已過去十二年。可這些年來,我不知道曾幾百次於惡夢裡重歷其境。那時歹鬥的種種情景,無不歷歷在目印在我心中。固然當年的我僅有六歲,但仍依稀記得那賊子左手成爪,不知使來什麼陰功招式,便把爹娘的頭顱硬生生從頸項上分開,跟著一刺一劈,只稍片刻之間,現場十多個護衛盡皆成死屍。要不是大哥行如鬼魅,從馬背上飛縱而下,有時又躍回馬背的馬術功夫將我救起,如今又怎麼會有我?」 過了半晌,年輕漢子才伸出手來,摸了摸少女的頭髮,寬慰道:「抱歉,都是三哥的錯。我們走吧……」 少女嘟嚷道:「本來就是。」年輕漢子抬起頭來,但見一鉤新月高掛天際,彷彿剛才發生的一切不過是場幻夢。 (待續)
(本文圖片取用於網路資源,若有侵權請來信告知,即刻撤下。) |
|
| ( 創作|武俠奇幻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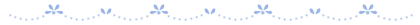

 參考書目
參考書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