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1/08/23 23:29:22瀏覽1229|回應0|推薦2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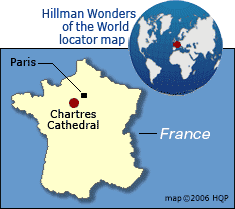 Illiers - Combray (上圖) 是個位處博斯Beauce 平原上的小鎮,向東北經夏特伊Chartre ( 上圖) 可到巴黎,西北則往諾曼第。我們到達巴黎的第二日,因天雨風涼,臨時提前行程,試圖朝南方追逐陽光。 從巴黎蒙帕那斯車站(Gare Montparnass) 搭乘法國國鐵 SNCF 可至世界遺產小鎮Chartres,再由此轉乘很特別的單節小型豪華列車( 見下圖左,它的廁所可是美麗的圓形搭配白色烤漆呦!) 。想到Illiers – Combray,你可以選擇直接接著搭時間接近的車班,或者,更應該停幾小時,順便一遊Chartres這個名勝。Paris 與 Chartres間車班很多,Illiers – Combray 回 Chartres 最後一班是6:47pm。車位很多,不需預定,只是蒙帕那斯車站既大且多層,最好查好班次後早點去買票。站內SNCF服務員可現場把你需要的各日往返各班次單獨印給你,服務極佳。 在Illiers – Combray,果然陽光早已懶洋洋地等待著我們。一出這迷你小國鐵車站 ( 位置見下圖Gare SNCF),與巴黎大相逕庭的樸拙鄉村趣味充滿空氣與微風之間。正對面壹張The Swann’s Way的專用地圖,許多地名都直接換成書中名字,真難為了這個小鎮。 Proust 的父親 Dr. Arian Proust 生於 Illiers (即書中的貢布雷Combray),是個有名的醫學教授,在Illiers,有一條為他命名的路「普魯斯特醫師路」 Rue du Dr. Proust,而鎮的東方,「普魯斯特大道」Avenue Marcel Proust則朝向巴黎。童年時, Marcel 6-9歲的夏天全家每年都會去 Illiers的聖靈街(Rue de Saint- Espirit)4號的姑丈Jules Amoit家渡復活節, Illiers可說是他童時的快樂天堂。 1971年,因為Proust之故,此地正式易名為 Illiers - Combray。  ■ 渡假時,普魯斯特家裡有兩個常用的散步方向: ★Guerrmantes即書中的蓋爾芒特Guerrmantes城堡方向,又稱蓋爾芒特之路 The Guerrmantes Way~~天氣好時,往Illiers西北的較遠的羅爾河Loir岸聖艾蒙Saint-Eman,神秘而高雅的柳樹、紫羅蘭、與水生植物,是象徵凡間榮華與高貴的世界,從未進入堡中的Marcel 賦予此家族無限美好的幻想,導致他日後與該家族的"聖盧 Saint-Loup" 交好、暗戀美麗的"蓋爾芒特親王夫人"、狂戀聰慧時髦的"蓋爾芒特公爵夫人",並與蓋爾芒特親王敏達自戀的弟弟"夏呂斯男爵Charlus" 糾纏不清。 ★Mereglise 即書中的梅塞格里斯Meseglise方向,又稱斯萬之路 The Swann’s Way~~往Illiers西南的梅黑格里斯Mereglise,書裡梅塞格里斯方向充滿粉紅山楂花,盡頭是具有藝文修養的猶太富商斯萬Swann的豪宅東崧維爾(Tansonvilli)之紫丁香花園,這個原型來自於姑丈的郊區美麗休憩花園「卡特隆綠地」Pre -Catelan,而這條路是書裡通往童年純真之愛與歡愉的象徵,山楂花叢邊與初戀菊貝(Gilberte)初識,一個菊貝的奇怪手勢觸發他少年的悸動;另一次偷窺到作曲家凡德伊Vinteuil女兒的同性戀及無情,更迫使他跨出童稚。 山楂花Hawthorns(Crataegusmonogyna),象徵"唯一的戀情"與"希望" 。  ( 山楂花大多在五月開放,但一定得等到霜氣消失,因此也稱五月花。最早出現此植物是在659 A.D. 《唐本草》提及山楂可助消化循環,在第一世紀希臘羅馬人用來治心臟病,也是生育的象徵,但到了中世紀有變成帶有死亡力量的花。這是因為花有香氣,但在枯萎時則放出與屍體腐敗相同的trimethylene故而傳統英國習俗是禁止把山楂花代入屋內的,除了May-Day celebrations作為裝飾之用。) ■ 我們的散步方向正好是由車站繞鎮西南一圈 1. 普魯斯特紀念館(蕾奧妮Leonie姑媽之家,Musee de Marcel Proust)  姑姑伊莉莎白Elisabeth的房子:伊莉莎白是蕾奧妮Leonie姑媽的原型,她長年豢臥病2F,躲在窗後窺探外界狀況。在Illiers白天很少人出門,除非辦事、購物等,許多人喜歡躲在門後論人長短,街上冷冷清清。她在1886把房子遺留給Proust,但他繼承後一直未再回到該屋,反而是幼時從伊莉莎白學來的偷窺本事,仍然勤用不懈。 此外,小Marcel與姑姑道早安時恩賜的椴花茶Linden flower tea 及馬德蓮小蛋糕 Madeliene,也是她送給Proust的神奇禮物。而現在這裡已是專賣普氏紀念品的博物館(右圖),時值週一,法國博物館一律休息,然則我們亦志不在此。姨媽過世後將此屋留給普魯斯特,但據說他始終沒再回來過。 書摘 : 我從萊奧妮姨媽那裡繼承了許多無法處置的物品和傢具,以及幾乎全部現金財產(她在死後表達了對我的愛,而在她生前我竟一無所知)。這筆錢將由父親代管,直到我成年,因此父親請教德‧諾布瓦先生該向何處投資。德‧諾布瓦先生建議購買他認為十分穩妥的低率證券,特別是英國統一公債及年息百分之四的俄國公債。他說:“ 這是第一流的證券,息金雖然不是太高,但本金至少不會貶值。”........至於某些老證券,父親已記不清它們的名稱了,往往將它們與類似的證券相混淆,因 此便拉開抽屜取出來給大使看。我一見之下大為著迷;它們帶著教堂尖頂及寓意圖像的裝 飾,很像我往日翻閱的某些富於幻想的古老書刊。凡屬於同一時期的東西都很相似。藝術家 既為某一時期的詩歌作畫,同時也受僱於當時的金融公司。河泊開發公司發行的記名證券, 是一張四角由河神托著的、飾有花紋的長形證券,它立即使我回憶起貢佈雷雜貨店櫥窗裡掛 著那些《巴黎聖母院》和熱拉爾‧德‧內瓦爾(1808—1855,法國著名作家)的書。 父親瞧不起我這種類型的智力,但這種蔑視往往被親子之愛所克制,因此,總的來說,他對我做的一切采取盲目的容忍態度。( II )
2. St. Hilaire街/橋,Pont St -Hilaire: 果真如蕾奧妮姑媽的教誨一般,整個小鎮在週一的午後時刻杳無人跡,若非某個古老的門內傳來陣陣搖滾音樂,真有說不出的詭譎 。 不過,下面那層陳列的,更是夢想已久,還研究過食譜的, 普式"朝聖客"才知的 ---- Cafe Eclair !!!櫃中另有 Chacolate Eclair,幸而老闆娘不知前者乃書中聖品之一,每個才1.02 歐元。 後來回到巴黎,在Fauchon又各買一些(下圖右二),舉凡甜點的滋味、大小、價格,都在Illiers – Combray。Illiers 的馬德蓮蛋糕真如普魯斯特書中所言 --- 「圓圓胖胖」,而位居馬德蓮廣場的名店Fauchon 則加入更多香料、奶油,形狀也是傳統的「海扇貝」。 我不由得想到,讓小Marcel 掛念不已的,卻是前者那些村民自製的簡單糕點,由此可 更為明瞭,普魯斯特絕非講究實質高級享受的人,他所追求的千百滋味,其實是需"求內心世界之精美"調製方成的"意念享受"! 3. 東崧維爾之路,Ru du Tansonvilli,就是Swann’s Way: 沿著似錦繁花的橋,向西南方向施施然而行,幾步之後,壹條優美的柳林大道於左側開展。尋了張路邊綠地上的舊長椅,我們快活地把適才的美味拿出野餐( 上圖右)。由此點回頭望,修剪得宜的林木成蔭 ( 下圖左一),2 : 45 pm,背景教堂鐘聲於草地後方、河道、水車、樹林間頂準時響起(下圖中),而往前望去,不可思議的層層疊疊綠意,綿延輾轉地勾勒出故事裡的東崧維爾之路(下圖右)。那一刻,你會忽然明白,普魯斯特為何選擇它作為故事的第一條徑路。
http://www.novelscape.net/wg/p/pulusite/zyssnh/006.htm
平時散步,我們總是早早就回家了,以便在晚飯前上樓去看看萊奧妮姨媽。初春時節天黑得早,我們回到圣靈街時家里的玻璃窗上已反射出落日的余暉,而在十字架那邊的樹林里,一抹紫霞映在遠處的池塘中,常常伴隨著料峭寒意,紅色的夕陽在我的心目中卻同烤爐上的紅色的火苗相關連,因為烤爐上的肥雞對于我來說是繼散步的詩情陶醉之后的另一种享受,使我得到解饞、溫暖和休息的快樂。到了夏天,相反,等我們散步回來,太陽還沒有下山。我們到萊奧妮姨媽的房里時,西斜的陽光正照到窗口,停留在大窗帘和帘繩之間,被分割成一束束、一條條,透過窗帘射進房來,給檸檬木的多屜柜鑲嵌上一片片碎金,又象照射林中的草木叢似的,以耀眼的斜光細致入微地照得滿屋生輝。但是,難得有那樣的日子:我們回來時柜子上的臨時嵌飾已經消失,我們到達圣靈街時,窗戶上已經沒有夕陽的反照,十字架樹林那邊的池塘也已經失去了夕陽的紅光,甚至變成銀白色;一道長長的月光,融入池塘的粼粼細波之中,并且舖滿整個水面。每逢那樣的日子,當我們走近家門時,就會看到門口有個人影;
媽媽對我說:
“天哪!弗朗索瓦絲在等候咱們呢。你的姨媽不放心了;
咱們回來得太晚了。”
我們顧不得脫掉外衣,赶緊上樓,好讓萊奧妮姨媽放心,并且以現身說法向她表明,同她想象的恰恰相反,我們一路上并沒有遇到不測,只是去“蓋爾芒特家那邊”散步了。天曉得,我的姨媽也明白,上那邊去散步什么時候回得來就說不准了。
“瞧,弗朗索瓦絲,”我的姨媽說,“我不是說著了嗎?他們果然去蓋爾芒特家那邊了!天哪!他們一定餓坏了!你炖爛的羊腿擱了那么半天一定發硬了。這么說,回來就得一個小時!怎么,你們居然去蓋爾芒特家那邊散步了!”
“我還以為您知道呢,萊奧妮,”媽媽說,“我記得,弗朗索瓦絲是看見我們從菜園的小門出去的。”
因為,在貢布雷附近,有兩個“那邊”供我們散步,它們的方向相反,我們去這個“那邊”或那個“那邊”,离家時實際上不走同一扇門:酒鄉梅塞格利絲那邊,我們又稱之為斯万家那邊,因為要經過斯万先生的宅院;另外就是蓋爾芒特家那邊。說實在的,我對酒鄉梅塞格利絲的全部認識不過“那邊”兩字,再就是星期天來貢布雷溜達的外鄉人,那些人,我們(甚至包括我的姨媽)全都“壓根儿不認識”,所以凡陌生人我們都認為“可能是從梅塞格利絲來的”。說到蓋爾芒特,后來我了解得更多一些,不過那是很久以后的事;當時,在我的整個少年時代,若說梅塞格利絲在我心目中象天邊一樣遠不可即,無論你走多遠,眼前總有一片已經同貢布雷不一樣的地盤擋著你的視線,那么蓋爾芒特對我說來,簡直是“那邊”的极限,与其說有實際意義,倒不如說是個概念性的東西,類似赤道、极圈、東方之類的地理概念。所以,說“取道蓋爾芒特”去梅塞格利絲,或者相反,說“取道梅塞格利絲”去蓋爾芒特,在我看來,等于說從東到西一樣只是一种語焉不詳的說法。由于我的父親把梅塞格利絲那邊形容成他生平所見最美的平原風光,把蓋爾芒特那邊說成典型的河畔景觀,所以我就把這兩個“那邊”想象成兩個實体,并賦予它們只有精神才能創造出來的那种凝聚力和統一性。它們的每一部分,哪怕小小的一角,我也覺得是可貴的,能顯示出它們各自特有的品格,而這兩處圣地周圍的道路,把它們作為平原風光的理想或河畔景觀的理想供奉在中央的那些純屬物質的道路,卻等于戲劇藝術愛好者眼中劇院附近的街巷,不值一顧。尤其是我想到這兩處的時候,我把我頭腦里的這兩部分的距离安置在它們之間,其實大大超過了它們之間的實際公里數;那是一种空想的距离,只能使它們相距更遠,相隔更甚,把它們各各置于另一個層面。由于我們從來不在同一天、同一次、同時去兩邊散步,而是這次去梅塞格利絲那邊,下次去蓋爾芒特那邊,這种習慣使它們之間的界線就變得更加絕對,可以說把它們圈定在相隔遙遠的地方,彼此無法相識,天各一方,在不同的下午,它們之間決無聯系。
每當我們想上梅塞格利絲那邊去(我們不會很早出門,即使遇上陰天也一樣,因為散步的時間不長,也不會耽擱太久),我們就象上別處去一樣,從姨媽那幢房子的大門出去,走上圣靈街。一路上,打火銃的鐵匠舖老板跟我們點頭招呼,我們把信扔進郵筒,順便為弗朗索瓦絲捎口信給戴奧多爾,說食油和咖啡已經用完,然后,我們經過斯万先生家花園白柵牆外的那條路出城。在到那里之前,我們就聞到他家的白丁香的芬芳扑鼻而來,一簇簇丁香由青翠欲滴的心形綠葉扶襯著,把點綴著鵝黃色或純白色羽毛的花冠,探出柵牆外。沐照丁香的陽光甚至把背陰處的花團都照得格外明麗。有几株丁香映掩在一幢被稱為“崗樓”的瓦屋前,那是守園人住的小屋,哥特式的山牆上面罩著玫瑰色的清真寺尖塔般的屋頂。丁香樹象一群年輕的伊斯蘭仙女,在這座法國式花園里維護著波斯式精致園林的純淨而明麗的格局,同她們相比,希腊神話里的山林仙女們都不免顯得俗气。我真想過去摟住她們柔軟的腰肢,把她們的綴滿星星般花朵的芳香的頭頂捧到我的唇邊。但是,我們沒有停下。自從斯万結婚之后,我的長輩們便不來當松維爾作客了,而且為了免得讓人誤以為我們偷看花園,我們索性不走花園外那條直接通往城外田野的道路,而走另一條路,雖然也通往田野,但偏斜出去一大段,要遠得多。那天,外祖父對我的父親說:
“你記得嗎?昨天斯万說他的妻子和女儿到蘭斯1去了,所以他要乘机去巴黎住兩天。既然兩位女士不在,我們不妨從花園那邊過去,路近多了。”
[1初版時,斯万妻女不是去蘭斯,而是去夏爾特爾。后來普魯斯特決定把1914年至1918年的大戰也寫進小說,故而把貢布雷改置于未來的戰區之內,即朗市与蘭斯之間(事實上,貢布雷鎮是以夏爾特爾附近的伊利埃斯為原型的)。]
我們在柵牆外停了一會儿。丁香花已盛极而衰。有几株依然托出精致的花團,象一盞盞鵝黃色的吊燈,但枝葉間許多部分的花朵,雖然一星期前還芳香如潮,如今卻已萎蔫、零落、枯黃、干癟,只象一團團香气已消的泡沫。我的外祖父指點著對我的父親說,自從他同斯万先生在斯万太太去世的那天在這里一起散步以來,這園內的景物哪些依舊如故,哪些已經改換模樣。他抓住机會又把那天散步的經過講了一遍。
我們的眼前是一條兩邊种植著旱金蓮的花徑,它在陽光的直射下向高處伸展,直達宅門。右面則相反,花園在一片平地上舖開。被周圍的大樹覆蓋的池塘雖是當年斯万老先生雇人開挖出來的,但這花園中最著斧鑿痕跡的部分也只是對自然的加工;有几處天然特色始終在它們的范圍內保持著獨特的權威,它們置身于花園就象置身于沒有經過加工的自然環境中一樣,公然挑出自己本來就有的特色。展示這些天然特色极需一個僻靜的環境,而在人工點綴之上它們自有一种孤幽的意韻:例如花徑下的人工池塘邊,兩行交相栽植的勿忘我和長春花組成一頂雅致的藍色花冠,箍住了水光瀲灩的池塘的前額,菖蒲象軒昂的王公揮落它們的寶劍,一任他們統治水域的權杖上紫色、黃色的零落的百合花徽,散落在澤蘭和水毛茛的頭上。
斯万小姐的遠行使我失去了有幸在花徑一見她的倩影的可怕的机緣。不能結識這樣一位享有殊榮、与貝戈特為友、能同貝戈特一起參觀各處教堂的少女,應算是有幸抑或不幸呢?因為若与她相遇,自慚形穢的我必受到她的輕視;可是,由于她不在,我雖生平第一次得到靜觀當松維爾園內景色的机會,卻只覺得了無情趣。對我的外祖父和我的父親來說,情況倒似乎相反,他們也許覺得女主人們不在反給整個庄園增添宜人的气氛,使它具有難得的美(猶如登山之日巧遇万里無云的好天气),因而今天到這邊來散步就格外适時。我真盼望他們的算計落空,突然出現奇跡,讓斯万小姐陪伴著她的父親雙雙來到我們的眼前,使我們不及躲避,只好同她結識。
4. 卡特隆綠地 ( 東崧維爾),Le Pre – Catelan: 略向上爬,一個小坡地下來,就到了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地了。這個以休假為主的花園,不但免費進場,拜週一之賜,杳無人蹤,清幽蔭涼,雖說是英式花園,卻有小橋流水、浮萍水草,坡地翻轉之間,每每又是驚喜的另番景致,難怪乎住在剛剛行過的無聊灰色的小鎮時,這兒會變成小Marcel的夢想花園。這些山林美景帶動的心靈滿足,又豈是人工雕琢的凡爾賽宮所能及?  花園後門有段摘錄自Swann’s Way內容的壓克力板: 'Je le trouvais tout bourdonnant de l'odeur des aubepines. La haie formait comme une suite de chapelles qui disparaissaient sous la jonchee de leurs fleurs amoncelees en reposoir; au-dessous d'elles, le soleil posait un quadrillage de clarte, comme s'il venait de traverser une verriere.'~~ Marcel Proust ('I found it all bourdonnant of the odor of the hawthorns. The hedge formed as a succession of vaults which disappeared under strewn with their flowers amoncelees in resting place; below them, the sun posed a squaring of clearness, as if it had just crossed glass..from google) 小門之外,一望無際的博斯平原靜默地沉思著,是在呼應這段文字嗎 ? 我竟看得癡了........ 5. 教堂,Eglise St –Jacques: 有著不對稱的教堂鐘樓,鐘響時聲音有如 “F – E – C”之音樂,難怪書中的外婆說「教堂會彈琴」。Proust 形容鐘樓像是「上帝的手指」,而且往往在鐘樓街頭行走時會感覺它忽左忽右、似近若遠地。教堂內部木雕斑駁,倒是彩繪玻璃相當新,式樣也較近代。隱約可見的金箔裝飾,讓我們足堪想像小Marcel 當時於此首度看到蓋爾芒特親王夫人、公爵夫人的閃亮場面。輕輕觸摸屬於他的質地,木雕斑駁,金箔隱約。
http://www.novelscape.net/wg/p/pulusite/zyssnh/006.htm 正當我姨媽同弗朗索瓦絲這么東一句西一句閒扯的時候,我同外祖父母和父母一起在教堂做彌撒。我多么喜歡那座教堂呀,如今想起來猶歷歷在目!我們進教堂時必經的古老門樓,黑石上布滿了坑坑點點,邊角線已經走樣,被磨得凹進去一大塊(門樓里面的圣水池也一樣),看來進教堂的農民身上披的粗呢斗篷,以及他們小心翼翼從圣水池里撩水的手指,一次次在石頭上輕輕擦過,年复一年地經過几個世紀,最終形成一股無堅不摧的力量,連頑石都經受不住,給蹭出了一道道深溝,好比天天挨車輪磕撞的界石樁子,上面總留有車輪的痕跡。教堂里掩埋著貢布雷歷代神父高貴尸骨的墓石,象是為祭殿舖下的地板,更增添了縈繞遐邇的靈气;可如今這片片墓石已失去死寂堅硬的質地,因為歲月已使它們變得酥軟,而且象蜂蜜那樣地溢出原先棱角分明的界限,這儿,冒出一股黃水,卷走了一個哥特式的花体大寫字母,淹沒了石板上慘淡的紫堇;而在別處,墓石又被紫堇覆蓋得不見天日,橢圓形的拉丁銘文更顯得縮成一團,使那几個縮寫字母平添一層乖張的意味,同一個字里有兩個字母挨得特別近,而其他的字母卻被大大地拓開了距离。教堂里的彩繪玻璃窗,只要外面稍有陽光,便能閃耀光彩,所以盡管外面天色陰沉,教堂里卻總是光輝燦爛;有一面彩繪玻璃窗,從上到下只被一個人物形象所占滿,那人的模樣跟紙牌上的大王相似;他就在上面頂天立地站著,教堂的拱頂成了他的華蓋。教堂里平常不做功德法事時,中午時分,他便籠罩在斜照的藍色的反光中(那樣的日子難得遇到,教堂里空空蕩蕩,空气清新,陽光照在瑰麗的陳設上,顯得更加堂皇,也更有人情味,再加上石雕和彩色玻璃,這里簡直變得象一家中世紀風格的旅館的接待廳,几乎具有供人歇宿的意味)。那時你能看到薩士拉夫人跪在那里咕噥几句禱文,她旁邊的祈禱桌上放著一包捆扎好的點心,那是她剛從對面的糕點舖買的,准備拿回家去當午飯。另一面彩繪玻璃窗上是一座粉紅色的雪山,山下是打仗的場面;它好象是雪山噴出的凌亂的雪珠直接打到玻璃上凝結而成的霜凍,又象玻璃窗上殘留的雪花,只是這片片雪花被一道霞光抹上了一層紅暈(無疑,就是這道霞光,把祭台的彩屏照得格外絢麗,好似這上面的五光十色,不是早就涂在石料上的顏色,倒象由外面射來的一道隨時准備放出异彩的光芒當場抹上去似的),每一面彩色大窗全都歷史悠久,處處顯得生意盎然,數百年的積塵銀光閃閃;這一面面由彩色玻璃交織而成的亮晶晶的大挂毯,已被歲月磨蝕得經緯畢露。其中有一面窗象長條的棋盤,由百十來塊長方形的小玻璃拼成,主調是藍色的,象當年供查理六世用來解悶的一副大紙牌;但是,也許因為有一道光芒倏然閃過,也許因為我的轉動的目光透過那面忽明忽暗的彩色長窗,看到了一團躍躍躥動、瑰麗無比的烈火,頃刻間那面彩色長窗忽然迸射出孔雀尾羽那樣變化多端的幽光,接著它顫顫悠悠地波動起來,形成一絲絲亮晶晶的奇幻的細雨,從岩洞般昏暗的拱頂,淅淅瀝瀝地沿著潮濕的岩壁滴下。我隨著手執經卷的長輩往前走,仿佛走進了五光十色的岩洞,四周是詭异的鐘乳石,多彩多姿;剎時間那一片片菱形的小玻璃顯得清澈透明,象鑲嵌在一枚碩大無朋的胸章上的藍寶石那樣堅硬,然而你又明明可以感到,在它們的后面,還有一件更令人欽慕的東西,那就是偶爾一露的陽光的微笑。在這片沐照著寶石般湛藍柔和的光波中,它是那樣清晰可辨,跟廣場石板上或集市草堆中的陽光一樣。在复活節前我們到達貢布雷的最初几個星期天,雖然大地仍是光禿禿的、黑黝黝的,但陽光的微笑卻給了我們安慰,它在這里,象歷史上圣路易的子孫們遇到過的那個載入史冊的春天一樣,使裝點著忘我草的那面金碧輝煌的大彩窗放射出燦爛的光芒。
6. 普魯斯特醫師路,Rue du Dr. Proust: 回火車站時,經過這條法國梧桐織出的小道,紀念普魯斯特的那了不得的神經學家醫師爸爸罷!?  車站外SNCF的地標,時鐘指著我們離去的時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