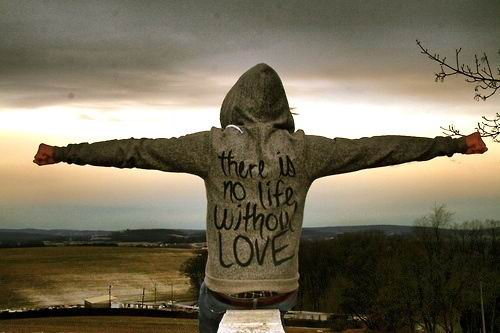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3/01/29 00:58:13瀏覽8878|回應101|推薦345 | |
這年頭就是喜歡男主角被虐得一支梨花春帶雨,兩眼猶含血淚痕
是劫是緣,都是命中注定,我們的故事並不算美麗,卻如此難以忘記。 是遺憾還是荒唐?錯的時間遇上對的你,對的時間遇上錯誤的你 周末夜,她一如往常地在公司加班,更晚一點之際,則到生命線義務幫忙,她已經不愿意再多想;自己不知從何時開始成了一位夜歸人,反正,身為一個貿易公司的主管,不難排滿在旁人想像中可以擁有的緊湊schedule,雖然其實很多時候,她只是不想早回家而已,尤其回去見到同住的女房客小施與她的男朋友大剌剌地曬恩愛,這房客因為是老客戶拜托,她不好回絕,不過就在前天,她已言簡意賅地跟小施表明,她不習慣在自家中留男人過夜,那怕是她自己的男人。小施倒沒說什麼,只是用種意味深長的眼光瞧了瞧她。 生命線中有位對婚姻價值困惑的女子對她述說;她是如何背叛了那個先背叛她的老公,之後,她一直徘徊在離與不離間。通常她的做法就是傾聽,因為這類的問題總沒一個標準答案。自認看透愛情關系中的脆弱本質,她對於自己的處境似乎更有種蒼涼的安心。 她愣了愣,不意想起了最後那次的分手,竟然就只由一通電話完成。 “我們――可以回到如普通朋友那般嗎?”對方聲音平平地:“因為――我們兩真的不適合啊――”。 三年多了,敗在個性實在不合,雖然她也承認,但在第一時間還是感到非常悲憤,然,比悲憤更強烈的是一種不甘――或許來自女人對歲月催人老的敏感,但壓下了那被貶抑的後知後覺,她只淡漠地回道:“我看連普通朋友都不必了,就這樣唄,再見。” 掛上電話後,過了好一陣子她才心驚肉跳起來。幾番她試著拿起話筒,懷疑線路不通。空氣出奇地安靜,在安靜中她仿佛聽到了內在一種摧枯拉朽般的坍塌。 “我沒義務告之您我的私生活。”她對女人索然地說。 外頭下著小雨,是那種不痛不快的雨,如同她的心情一樣。 停好車子,車門一開,冷空氣迎面而來,雨勢也在這一刻加大了,沒帶傘的她勢必得冒雨跑回家,一向是從容端莊的姿態,卻在這深夜僻靜的巷衢,難顧高跟鞋敲打在地面的紊亂倉皇,不期就撞上一絲惘惘的自惱。 也許一逕專注著什麼,開啟公寓大門時,她也沒多注意身後那名看來像是鄰居的男子,他跟她進了門,她住的是二樓,男子低著頭,默默地無聲地尾隨著。 用鑰匙開了門,方才踏入,俄頃間,一只濕黏的手蒙住了她的嘴巴,她本能地用盡力氣抵抗,摜倒了對方的腿,二人一起撲跌在陽臺上,掙扎中她的手臂一陣辣痛劃過,那男子卻似無意真的拿刀傷人,他急急揀起了掉落在地上的美工刀,往外一丟,慌張地扶起她;邊連聲道歉:“對不起,小姐,傷到妳了,要不要緊?――” 一個深夜帶刀的男子居然還好像忘了自己扮演的是什麼角色!她震驚之餘,也覺迷惑,但眼見男子把“證物”都丟了,不禁地尖聲呵斥:“你想幹啥?小心我大叫――” “不不,千萬別叫,不然我的一生就毀了,”男子用拳頭捶了下自己的腦門,氣急敗壞:“我真是瘋了,一定是瘋了――我可以不可以――立刻離開這里?——-” 她定睛瞧,男子穿著藏青色的大衣,灰色套頭毛衣,原來非常年輕,學生模樣,帶種令她意外的良好出生氣質,見他反而如此地無措,猶豫了幾秒,她口氣逐緩和了下來:“你――有什麼問題嗎?”, 於許久後的某一天,她就會知道,其實她早應該讓他走的,她根本沒任何理由去對眼前如此不利自己的情勢產生好奇,或許在她說完這句話之後就已經明白了,她卻有意無意將他拉進她的人生里,如果更深入一點分析,是她對這個社會大多數眼光的下意識反撲? 男孩也躊躇了一會兒,肯定她確實在釋放著善意,於是納納地說:“我――剛剛在大街上晃――然後――發現――小姐――妳的背影――很吸引我――但是我――沒有勇氣――跟妳搭訕,我想妳是根本不會――理會我的―――也許我――太衝動了――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知道你有帶刀子嗎?” “美工刀是我今天買的,但不是預謀――不,是預謀,”男孩點點頭:“我覺得不應該再在妳面前講假話,尤其妳對我――這麼寬容,我倒真希望――我可以跟妳多說一點――有些兒事情我根本找不到一個真正可以談心的對像――”他低下頭,蒼白的臉龐上飛上一朵暈紅:“如果妳愿意把我當個――朋友看待,我一定也會――改過自新――” “我――呃,在生命線工作過,所以――是可以跟你聊聊的,”她拉開落地窗門,賜恩般拋下一句:“進來坐坐吧,讓我聽聽你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困難。” 在往後的某一特定時刻,她總是不由己地將目光投注在那些洋溢著青春笑容的年輕情侶們身上,仿佛尋找男孩憂愁和苦惱的未知答案――但那只讓她倍感如同在咖啡的殘渣里;檢視虛幻的解構意義般徒勞。 從廚房倒了杯水給她的“病人”,她恢復氣定神閑地坐在他一旁,不失權威地說:“你是否心里有什麼事,覺得不方便跟父母或老師坦白?” 他喝掉大半杯開水,安了安神,認真地想了想,小心翼翼地回到:“不瞞妳說,我父母都是虔誠的摩門教徒,妳知道摩門教的十誡吧?他們告訴我一定得遵守――因那是尋求真善美人生必須行經的――呃――自我修煉過程,但對我來說,其實就是一切我想嘗試做的事――都必須先預付著罪惡感,”他抬眼看她,見她的眼神是帶著鼓勵的,於是繼續自剖:“而我不知怎麼搞得,就是偏偏對那可能會激起――犯罪意識的行為――感到興趣,”他深吸一口氣:“抱歉,我一定要說真話,不然就辜負妳了。” “你――沒有把這樣的感覺――對你父母說?” 他搖搖頭:“沒用的,反正只要我做了他們覺得不妥的事,比如我抽煙,比如我――逃課,或甚至是我――偷看A片,他們不去想我為何會有如此的行為,只要緊拉著我拼命地跟上天懺悔,記得一次我爬山迷了路,後來靠我自己學來的野外求生逃過一劫,他們喜極而泣,卻不斷地非說這是禱告下的神跡。我是家里的獨生子,自是不會對父母的愛質疑,但我好像――生就應該做一個人類的模范典型,為什麼?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嗎?不能不脫離他們的價值導向嗎?――我――” “對不起,我得打斷你一下,因為我覺得你的問題還是在於;你剛剛說你偏偏就是會對那些可能激起你――呃――犯罪意識的行為感興趣,這個部份已經不全然只歸於“自己的想法”了,那已經算――一種精神上的――失常或偏差,你帶著刀子;在夜晚跟蹤著單身異性――難道你沒――” 換了他連忙打岔為自己辯解:“對,我承認有不明的企圖,但刀子真的只是用來――嚇唬人的--我完全無意傷害任何人。” “那你的舉動是因為?——” 他絞扭著雙手,一時又說不下去了。 “或許為了達到某種目的,這樣的舉動已在你的潛意識里重復無數遍了,對嗎?” “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順了順氣,他再度開口:“什麼時候開始的?我已經――記不清楚了,總而言之,後來我根本讀不下書,我滿腦中充滿了――充滿了――呃--”他無助地望向她。 “我知道你的意思。” 那亦是教她敏感的字眼,她端肅面容:“你這種年齡,好奇心特別強,也因為缺乏觀念正確的教育,才會一天到晚胡思亂想――你都交些什麼樣的朋友?” “多半是教會里的朋友,其實他們都很善良,正直,不過都是乖乖牌,都有守貞的觀念,不管男女,我只是納悶,為何在婚前做那件事,就很可恥,我不理解——” “這麼說唄,在婚前守貞,也是愛在精神層面的最高提升表現,越是能抵抗誘惑,通過層層考驗,越是能彰顯生命之莊嚴和美麗啊。” “那妳也贊成,或者可以說,妳自己也實踐了嗎?” 他熠閃的眸子里,似乎有一些僭妄什麼的成份,讓她一時為之語塞。 “你不覺得你―-有點無禮嗎?” “啊,真對不起!”他的神色又懊惱了。 她其實也有感那番回答挺說教,逐調整了一下坐姿:“沒關系,你繼續吧,我還在聽。” 無疑地,自己始終被批判著,反正,他認為再壞不過就是說到底:“沒錯,要避開無所不在的誘惑很難,雖然我家人一貫周密地保護著我,但每當家人為了什麼拉著我一起祈禱時,我居然不專心地老會想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比如和女人――親熱的情景,這樣的畫面總是一再地出現在同時做禱告的時候,使得我又因為褻瀆了神明而更加深了罪惡感――我是否挺邪惡的?” “沒事,他們早睡了,不知道我溜出來。再聊一會兒我就走,可以嗎?” 連她自己都聽出;沒在趕走他的意念上,多用心促成一分。為了掩飾,她站起身,但一時又忘了起身的理由,半嚮拿起他的空杯子道:“我去廚房再倒杯水。”
廚房里一如往日地亁凈,冷清,一塵不染的流理臺,全套高檔的廚具,鍋碗瓢盆,幾乎原封不動,順手將東西歸位的好習慣,在她的家里竟顯得多餘且不近人情。 等水煮開時,她把茶葉分別放在兩個茶杯里,蜇至窗前往外眺,一片黑壓壓,風大,內衣褲來不及收進來,模糊的影子在風中絕望地翻撲著。 她沒察覺他不知何時已經悄然倚著門;靜靜地凝視著她的背影。 不管她的氣勢如何駕臨在他之上,她的背影就是透著某種弱質,那穉秀的肩膀,盈盈的腰身,白皙渾圓的小腿肚,要不,那一點眼梢的浮動,甚至是淡淡的疲倦神情,或有些寂寞的線條,在在吸引著他。 而最教他暗自想窺視的,就是她的“失神間”的霎那,總好像在下一秒鐘,會來個什麼樣全盤皆翻。果真,她出現了一個像是拭淚的動,但沒等他回避成功,她閃電般叫住了他。 “站住!別溜啊,你在偷看我,是不?” 他一動也不敢動。 “告訴我,你――究竟想從我身上得到什麼?感覺上,不只是性吧?如果純粹只為了性,你只要花一點錢,難道你會不知道?我不相信。” 他緘默著,朦朧地預感她的不肯偃旗息鼓,暗藏著他其實不太敢想像的目的。 她移至他面前,鼻子似乎嗅聞到一股費洛蒙般的麝香,屬於處子的味道。非常奇特的,她突然異常舍不得他的第一次;就可能從她的開導而真的忠於到那個好女孩身上。仿佛;她覺得他不需要好女孩,那只會將他的人生帶進一場死寂中。 或許在幾十年後她的晚年,還有人對她的愛情感興趣時,她會推翻曾經對法官的說辭,在法庭上,她厭惡自己為自己似是而非的辯護。她應該有個更堅定的人生的。 “說啊!怎麼?有啥不能說的?” 他的嗓音沙啞了:“真的――沒別的意思,我只是――想找個能――懂得我的人,不會因為我的坦白而看輕我,或――還愿意――愿意接納我――”他微微緊張了起來,幾乎詞不達意地。 她別過頭去,一時也有點訝異自己的口吻,一股無由來的焦慮壞了原先組織好的脈絡,她快要看不分明整件事,但依稀覺得隨著夜的深沉以及這場大雨的對外隔絕,已然推向最後的;只關系兩人結局的一刻。 “我--是不是應該--走了蛤?--妳也可以早點休息--” 他的謙讓竟然在某一點上贏得了她的好感,終於,她決定成全那個無名的時機。 “抱我一下唄,”她用種大方無垢的態度對他伸出手臂:“這代表我沒排斥你,來,讓我們來個友誼的擁抱――之後,你就可以走了。放心,沒人看輕你--” 他上當了,或者他受教了,她這個假友誼之名的動作其實只為了避開明顯的邀約。 黑黯中倒順利地摸上那張可供二人躺下的長沙發。正當他已確知自己可以發展到什麼地步之際,卻從她急促的喘息里迸出不像方才喃喃呻吟的清晰字句:“記得,你我就只有這一次!唯一的一次!以後你永遠不能來找我,否則我絕不繞你!聽見沒有?” “不!我要跟妳在一起――我希望妳也會愛上我--” “不可能,也絕對不行——” “為什麼--一定要如此———” 她的耳朵為了仔細分辨他的語音,卻破天荒聽到了大門響起的咔嚓聲,她大吃一驚,比貓兒還靈敏地猛拉起他,一溜煙進了她的房間。 也是確定了小施每個周末下了班就直接回自己東部的老家,她才無所顧忌,不料在這麼晚的時刻,小施還會回來。 今天是情人節,小施沒事先告訴她將不會回老家,男友陪她回來,原本準備走的,但小施卻發現新大陸般地對他低嚷:“看,這里有雙男人的鞋子!陌生男人的鞋子耶!哈――” “真“假仙”的女人!”小施男友小聲道,樂了:“那我也不走啦―――” 房間里的她,在昏黯中緊攫住那頭躁動的小獸,一直試著回想似乎那里出現的不對勁,思緒慢慢地回溯,終於,倒片般轉到了陽臺的一幕。 “啊,完了,你的鞋子?放在門口的鞋子!”她驚呼。 “你不走了?” “當然,何況妳也不忍心我就這樣離妳而去唄?” 她想試著推開他,他卻更篤定地從身後用力環抱住她。 “不要--” 他已經聽過她的口是心非,如今根本不再理會她。 如果說這是男女性事的第一課,那麼有可能連最後一課也學到了,因為沒有比經過荒唐的情節還能逆轉協達成相悅的情況更教他費解跟識得了。 她發現自己的“不要”已有幾分真實,但他卻折回“帶刀”的初衷。
吻,如聲聲凄切的軟刀子般落在她的頸脖,臉上,以及帶點蠻力扳過的她的嘴唇上。一點也不難地將她放倒,而她的抗議混在窗外的暴雨聲中只顯得單薄微弱,甚至反抗成了背德刺激的同義詞,形成更深的誘陷。 他的心子如同神奇的杰克的豆子;瞬間快速地抽長而猛然越變越大株,準備沿著天梯直達高頂,似乎目的已是唯一,那樣的一個偉岸的樹影(男人)好像跑了出來了,卻失去了以原先的柔情及憐惜灌溉而擁有著向陽茂密綠葉,只成了株光被黑黯沼澤養份使勁催熟的巨大蔓藤,四面八方企圖包抄和吞沒她。
她感到男子驟然生出攻擊的狼牙;仿佛那是隨時就藏在皮毛層底下的武器,也就是說;刀子根本就無形地被鎖在他的意志里,一切其實都以他的意志為主,她不能不說自己最怕的還是相互消長的意志力,明顯地,她將它放在“我們就只有這麼一次”上,且不見得堅定,但必然抵觸了他的一些什麼東西,讓他下意識更加要使勁“把握這可能的最後一次”,也或許黯朦中不免放大了想像,她覺得那樣被他狼吻到幾近遍體鱗傷的獠牙;就如無所不攀狠狠纏繞她的蔓藤,幾乎在對她進行一場駭人的身心致死方休的纏綿悱惻。 “拜托,我們先停止一下——” “不,是妳要求的---我不能讓妳失望--” 他完全朝著被撩起的炙熱欲望一路馳騁,她無論如何抵擋,都控制不住那已然奪回主導地位的他的氣焰--
又,抵擋無非更像添置的柴薪,投在欲火上不時竄高起威嚇的熊熊烈焰,終至一發不可收拾,在完全赤紅的幽閉中,映出她眼中的迷惘,迷離跟迷失。
“妳喜歡我對妳這樣,是不?--”至今還不知名字的小男人對她耳語,他不再提到“愛”這個無關緊要的字。
她發現她的一汪清水,原來早流向了一個奇異的黑洞,再也有去無回。
其實她早就可以預料,事實上一開始她就知道可能的結果,她只是需要更崇高一點的借口,來說服自己這麼多時日來的堅持為何。
夜,不替她背書,雨,成了幫兇,但最大的兇手,還是她自己。
一個夜歸的女人,正被自己一手喂食的念頭洶涌地強暴著---- |
|
| ( 創作|另類創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