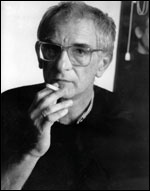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06/07/29 19:49:59瀏覽2633|回應2|推薦17 | |
悲憫的人類詩篇奇士勞斯基的戲對我而言,倘若電影果真具有任何意義,那便是讓人們身入其境。 我無意於此(編按:史上第一位奪得三大影展最佳影片的導演),但我寧願看到這樣的記載:史上第一位成功地製造出直角的導演(編按:喻能將事情掌握得恰如其分),目前我尚未能達到。 我拍的每一部電影---除了〈工人'71〉(Robotnicy '71)之外---都在講人,而非政治的故事。 我拍過的電影,從第一部到最近的一部,每一部都在講一群找不到自己方向、不曉得該如何生活、不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的人----一些迫切在尋找的人們,他們企圖尋找一些最基本的答案,像是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麼?早晨為什麼要起床?晚上為什麼要睡覺?又何苦再起床?從這次醒來到下一次醒來之間,該如何打發時間?你該怎麼過日子,才能讓自己在早晨的時候能夠心平氣和地刮鬍子或化妝? 電影學校教我如何去看這個世界。 並不是每件事都可以被描述的,這正是紀錄片最大的問題。拍紀錄片好像掉進自己設下的陷阱一般;你愈想接近某人,那個人就會躲得愈遠。那是非常自然的反應,誰也沒辦法。 如果我想拍一部有關愛的電影,我總不能在人家躲在房間裏作愛時,跑進他們的房間裏去拍吧!如果我想拍一部關於死亡的電影,我也不可能去拍某人真正死掉的過程,因為那是一個非常私密的經驗,誰都不應該在那個時刻受到打擾。我注意到當我在拍紀錄片時,我愈想接近吸引我注意力的人物,他們就愈不願意把自我表現出來。 我害怕那些真實的眼淚,因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權利去拍攝它們。碰到那種時刻,我總覺自己像是一個跨入禁區的人,這就是使我逃避紀錄片的主要原因。 我想要表達的是,在每天的生活當中,我們都面臨抉擇,並應對其負責。同時我們並沒有察覺到這些抉擇會將我們導入某些方向。對此我們可說是一無所知,只有在日後回顧一生,我們才能明瞭當時做下的某些抉擇,所具有的決定性。 當我拍記錄片的時候,所擁抱的是生命,接近的是真實的人物、真實的生命掙扎;這驅使我更了解人的行為--人如何在生命中克盡其責地扮演自己。 基本上,這些人物的表現和其他電影裏的人物沒什麼差別。不過在《十誡》中,我把重心放在他們內心中,而非周遭的世界。以前我所處理的題材經常都是外在的環境,陳述周遭發生的事件,以及這些事件如何影響人群,然後人群又如何影響這些事件。現在,在我的作品中,我經常把這個外在的世界拋開;愈來愈常出現的題材,是那些回到家裏,把門關起來面對自我的人們。 我們在構思《十誡》的時期,常常想到這些問題: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什麼是謊言?什麼是真相?何謂誠實?何謂不誠實?它們的本質為何?我們又該以什麼樣的態度來對它們? 我不拍隱喻,隱喻是給人讀的;它是個好東西。我總是想攪動人們的心情,讓他們想去做某件事,無論是把他們拉進故事中,或是給予他們分析這個故事的靈感。重要的是,我能夠迫使他們去做某件事,或是以特別的方式感動他們,這就是我一切作為的目的:讓人們去經驗某些事物,無論是用理智或感情去經驗,都無所謂。 我拍電影是為了給人們一些東西,將他們帶往另一個地方,無論那個世界是屬於直覺亦或知性的世界,都是好的。 我最喜歡的觀眾是那些說電影在講他們自己,或對他們產生特殊意義,以及改變了他們的人。 藍、白、紅:自由、平等、博愛。皮西歐提議把十誡拍成電影,那我們為何不嘗試把自由、平等、博愛也拍成電影呢?為什麼不試著對《十誡》中訓誡作更廣義的了解?為什麼不試著解析十誡的現代功能?我們對它的態度為何?而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個名詞的現代功能又是什麼?讓我們針對人性化、隱私及個人的層面,而非哲學、更非政治或社會的層面來討論。西方世界已將這三種觀念在政治及社會層面上付諸實行,但它們對個人層面來說,卻又是完全不同的論題;因此我們想到拍這三部電影。 這三部電影(編按:藍白紅三色電影)都在講具有直覺、感性的性情中人,對白中不見得都直接表達出來。在我的電影裏,很少有話直說。最重要的事經常都發生在幕後,是你看不見的;要不它存在於演員的舉手投足之間,否則它就不存在;要不你可感覺得到,否則你就感覺不到! 紀錄片的推展主要須借助作者的想法;戲劇的推展則須借助動作。我想我的電影一直有一個傾向:推展它們的動力總是想法多於動作,或許這正是它們最大的缺點。無論你做任何事,都應該有一貫性;而我卻從來不擅於描述動作。 這一條思路最後即發展出《盲打誤撞》。它描述的對象不再是外在世界,而是內心世界。它所敘述的是那些會干預我們命運,把我們往這個方向或那個方向推的力量。我想該片最根本的瑕疵出在劇本上;直到今天,我還是很喜歡這個有三種可能結局的點子,我覺得它豐富且極有趣味,只是劇本沒能好好地發揮。每天我們都會遇上一個可以結束我們整個生命的選擇,而我們卻渾然不知。我們從來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是什麼,也不知道未來有什麼樣的機遇在等著我們。 我所謂的命運指的是一個地方、一個社交團體、一份專業生涯,或是我們從事的工作。在情感的範疇裏,我們可以享受較大的自由;但在社會生活的範圍裏,我們卻大大地受到機遇的主宰。有很多事我們非做不可,或者我們必須變成某種人;當然,那和我們的基因有關,在拍攝《盲打誤撞》時,這些念頭不斷縈繞在我心頭。
奇士勞斯基的信仰我並不上教堂;但我相信有類似上帝的東西存在著,我與祂的關係是個人化的,不須依靠別的憑藉。 想想「十誡」總是有用的。它們已存在六千多年,未曾受到挑戰;但是,數千年來卻天天被重新觸犯。問題不在於當代人行為特別懷,或甚至我們不懂如何應對進退;而是我們藉以判斷事物的標準不斷在降低,好壞不再明確,我們的生活方式亦然。我們開始不斷問這些問題,但是我對於從別人處聽來的答案,信心日減,每個人都試著依個人所需,建立起一套價值,我們甚至不再確定,每個人所擁有的是否還是同樣的十誡? 我認為能夠提供絕對仲裁的標準是存在的;不過當我說我想到的是上帝時,我指的是舊約,而非新約裏的上帝。舊約裏的上帝是一位要求很多、很殘酷的神。祂毫不寬貸,殘忍地要求子民服從祂定下的一切規矩;而新約裏的上帝卻是一位蓄著白髯,寬容而善良的老頭子,任何事都能得到祂的原諒。舊約的上帝賦予我們極大的自由與責任,祂觀察我們的反應,然後加以賞罰,想求得祂寬恕是不可能的事。祂是永恆、明確、絕對(而非相對)的仲裁。一個仲裁的標準理當如此,尤其是對像我這樣不斷在尋覓、懵懂無知的人而言,更應如此。 罪惡觀念和我們常稱之為上帝的這種抽象、絕對的權威密不可分。不過,對我而言,還有一種自覺的罪惡感和前者意義相同。通常,它源於我們的懦弱。我們不能抵抗誘惑:貪求更多的錢、享樂、想擁有某個女人或某個男人,或想掌握更大權勢的誘惑。 另一個問題是:我們是否應該活在罪惡的恐懼之中?這又是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它源於天主教及基督教傳統,這個傳統又和猶太教的傳統不盡相同。這也是為什麼提出舊約及新約上帝的原因。我認為這樣的權威的確存在。有人說過:如果上帝不存在,人類也會創造一個上帝。但我不認為這個世上有絕對的正義這回事,我們永遠不可能得到它。唯一的正義存在我們心中的那把秤上,而我們的秤非常微小;我們既渺小、又不完美。
奇士勞斯基的人生我們都是在偶然的情況下被可能的選擇所審核。選擇,是一種決定命運的方式;它或許會適時呈現,卻不是我在期待中而獲得的。 我有一個不太流行的觀念,我認為人本善;人天生想做好人。問題來了,如果人性本善,那麼邪惡從何而來?我並沒有一個十分合乎邏輯、又有道理的答案。我的理論是:一般來說,邪惡之所以會滋生,是因為人們總會在某個階段發現到自己沒有能力行善;邪惡的原因是挫折感。無論人的改變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我們也不可能對人為什麼會無力行善作出結論;因為理由太多了,有成千上百種不同的理由! 我很怕那些企圖教我一些事或想指導我找到目標的人物,對我或對任何人都一樣。因為我不相信別人能讓你找到目標,除非你自己找到它,我對那一類的人具有近乎偏執的恐懼感。 對於這些事我非常地落伍。我知道現在大家很流行到處去找心理治療師,參加各種團體或個人的心理治療活動,尋求心理醫師的援助。我認識很多人都在這麼做,我覺得這很可怕。我對那些治療師近乎偏執的恐懼,就跟我對政客、傳教士和老師的恐懼一模一樣。 我害怕這些指你走上正途、這些「知情」的人士。因為老實講--我對此真的深信不疑--沒有任何人真正知道任何事,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非常不幸,這些人物的行動通常都以悲劇收場--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或是史達林主義之流。我深信史達林與希特勒都十分清楚他們在做些什麼,他們清楚得很,那就是實情!那就是狂熱主義!那就是覺得自己知情的結果!下一刻,軍靴就出現了。那些事件的結局永遠都一樣! 我的態度是:即是有不公正的事件發生,有人表現得很惡劣;以我的觀點來看,我必須試著去了解那個人。無論他們是好是壞,你必須試著了解他們為什麼會這樣。我認為這個方法和對抗一樣有用。 如果我看到某人的動機是為了他們內心所信仰的某種意識形態--比方說,政治上的意識形態--而不是為了追求生活上的舒適,那麼即使他們站在相對的立場上,也會得到我某種程度的尊敬,不過這種尊敬當然有限度。我不可能去尊敬一個認為應該把別人眼睛通通剜掉、把敵人的喉嚨全割斷的人。 在戒嚴法實施期間,我領悟到政治其實並不是這麼重要。當然,從某個角度來看,政治決定我們的角色,准許我們做某些事,或不准我們做某些事。但是政治並不能解決最重要的人性問題。它沒有資格干預或解答任何一項攸關我們最基本的人性或人道問題。其實,無論你住在共產國家或是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一旦碰到像是「生命意義為何?」「為什麼我們早晨要起床?」這類的問題,政治都不能提供任何答案。 長久以來,我只知道在物質世界,那個你可以觸摸,可以在店裏買到的世界之外,生命裏還有別的東西存在。 我想,無論你住在哪裏,一般來說,每個人都很孤單。我經常目睹這種情況,因為我在國外工作,和許多國家的年輕人都有接觸:德國、瑞士、芬蘭和其他許多國家。我看到人們最大的困擾,以及使他們自欺最主要的原因——因為他們都不願意承認—— 就是孤寂。 事實是,他們沒有可以談論重要話題的對象。事實是,因為現代生活愈來愈舒適,反而抹殺了許多過去對我們十分重要的事:交談、寫信,與另外一個人作真正的接觸。每件事都變得太過虛浮。我們不再寫信,改用電話代替。我們不再旅行,以前這本來是非常浪漫、極富冒險性的活動,現在卻淪落成到機場去買一張機票,飛到另一個看起來大同小異的機場去罷了。 我還有一個愈來愈強烈的印象:雖然人們都寂寞,其弔詭卻是大部分的人都想發財,以便享受遠離他人、獨自一人的奢侈生活。他們想住在一個遠離人群的大房子裏,去那些大得沒有人會坐在他們旁邊、聽得到他們談話內容的餐廳用餐。同時,人們又極端怕孤寂。當我問:「你真正怕的是什麼?」我最常得到的答案是:「我怕一個人!」當然,也有人會回答他們怕死,可以大部分的人現在都會說:「我怕寂寞!我怕一個人!」可是每個人又都渴望獨立。
|
|
| ( 知識學習|檔案分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