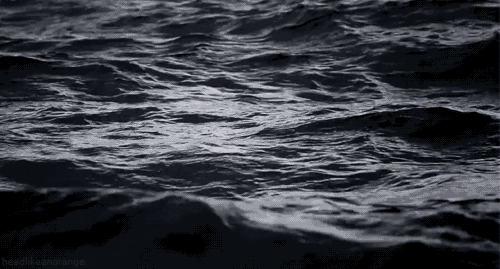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7/04/06 00:07:22瀏覽1222|回應0|推薦16 | |
#1 父親劫
「媽媽,這花為什麼不香?」 酒店大廳,身著紅色洋裝的小女孩,她踮起腳尖,好不容易才用圓滾滾的小手,碰觸到大廳中央那張黑檀木桌子上擺放的花。 洋蘭,本應幽香,但小女孩卻連一點味道都沒聞到。這和她想像的落差太大,就像自己不應該費盡這麼大的力氣去做這件事。 小女孩左右張望,發現媽媽不在身旁。 視線飄向遠方,穿過簇成一小群一小群的人們。 小女孩的母親正在和兩位男士寒暄,她沒聽見女兒呼喊的眼神。 夏志傑是這場酒會的策劃人,從瑞士學的酒店管理,回國後做了幾年酒店工作,抓住國內企業轉型,越來越注重大型公關活動的機會。他開始和一些小型的EAP(員工援助、管理)機構、企業培訓等公司合作。 做了兩年,夏志傑感覺酒店裡頭的發展沒有外頭做活動來得大,於是辭了酒店工作,成了一位專業的活動規劃師。 至少對外,夏志傑如此介紹自己的經歷和頭銜。在這些社會化的身份之外,夏志傑擁有一項不為人知的能力。 一如往常,夏志傑注意到了小女孩。 「小朋友,妳怎麼一個人,媽媽呢?」 小女孩指著母親的方向,卻發現剛剛還在跟兩位大叔說話的媽媽,現在不知道又流連到哪簇花叢。 「別著急,我帶妳去找媽媽。」 小女孩對夏志傑的提議,有些猶豫,她記得媽媽要她一個人待著,別跟陌生人走。這點,學校老師也交待過。可是眼前這個男人看起來很可信,他和會場其他人一樣,西裝筆挺,是媽媽平時會答理的對象。 小女孩鬆懈了心房,夏志傑拉住她的小手,兩人逐漸朝會場外圍走去。
會場外有座小花園,種了無數洋蘭。 幾位在洋蘭面前拍照,他們對自己拍出來的照片十分不滿意。 廉價的相機,往往無法拍出洋蘭的美,因為一般數碼相機使用的感光元件,只能捕捉到紅、綠、藍三色,對於紫色,那是靠相機的軟件演算出來的結果,簡單來說,就是用「猜」的。 便宜的相機,猜色能力差,一拍紫色就露餡,會呈現出奇異的藍色,或者桃紅色。比較高檔的相機,猜色能力強,拍出來的紫色如肉眼所見。 在各種高檔相機中,還能再分高下,強光底下大家猜色能力都差不多。可在弱光下,還能把紫色拍得恰如其色,那說明相機的演算能力優異,在色彩方面可以給予攝影師更高的信賴感。 「好了,別動,我再拍一張。」邵峰是一位攝影愛好者,對於感光元件和顏色的道理一清二楚,可是他依然選擇一台非常普通,經常猜色錯誤的相機。因為他沒錢,頂多在網路論壇裝裝樣子,說得一口好相機,但真正頂級的相機,機身、鏡頭超過一萬塊的,他壓根沒用過,因為他怕老婆球球,所以把存摺交在老婆手裡。 花沒拍好,要老婆、孩子跟著再拍一張。本來孩子邵大大還興高采烈的,接連被指定表情,笑得都僵了。要不是球球哄著,說等會兒買奶茶給他喝,他連待在鏡頭前五秒鐘的意願都沒有。 孩子到了一個年紀,挨著母親豐滿的乳房,反倒不好意思起來,但內心卻又充滿對乳房的渴望。尷尬與害羞的衝擊,邵大大像個不識趣的雕像,硬愣著被球球揣在懷裡。 照片拍好了,邵峰端詳手機屏幕,屏幕除了一臉不快的孩子,中年發福的老婆,背景的花圃硬生生帶到了夏志傑的身影。 畫面中,夏志傑蹲在花圃旁,對著旁邊空蕩蕩的空氣好像在說些什麼。他腳跟旁的角落,畫面有點捲曲,就像那裡有片看不到的透鏡,折射了空氣。 邵峰抬頭,看夏志傑對空氣自言自語,趕緊拉著老婆、孩子上了遊覽車。 球球對他扯著自己衣服的樣子,十分不高興,說:「幹什麼呀!離開車的時間還有半個多小時呢!」 邵峰朝花圃方面使個眼色:「那裡有個怪人,對著空氣說話。」 「哎唷!還真的,怪可惜的,小哥長得挺俊。」 「可惜個屁,萬一是個神經病,等會兒拿刀出來砍人,那怎麼辦?我們身邊帶著孩子呢!」 「瞧你這個窮酸的樣子,把你砍死了,我找個更有錢的去。」 「去去去!去他媽的,妳這婆娘愛找誰找誰,反正我沒錢。不!我有錢,只是我的錢都給妳把持住了。」 酒店保安正在一旁抽煙,在北京工作十幾年,抽的還是老家湖北的黃鶴樓。煙價越來越高,他得省著抽。本來一天幹掉一包,現在克制為三天兩包,朝兩天一包邁進。 「哇操!」保安半根煙叼在嘴裡,靠在駕駛座旁的車身上,還在享受那股神仙勁兒,就聽見背對他的車門側有男女爭吵的聲音,他轉身一看,兩個旅行團的客人正在打架,也不顧孩子在旁邊看得不知所措,有點疼惜的把手上的煙往地上一扔,趕緊跑過去勸架。 保安在那裡勸,邵峰和球球互相掐著對方脖子,誰也不肯讓誰。 「別使勁兒,有話好好說。」也不知道這對夫妻平常吃了什麼,或者對彼此真是苦大仇深,保安用盡吃奶的力氣也分不開他們。一個反作用力,整個人跌坐在地。 球球鬆開手,邵峰把她推倒在地。 他的嘴角露出笑容,憋了十幾年的氣,在這一刻獲得了勝利。腦中響起讚歌,是拉丁天王瑞奇.馬丁在1998年法國世足賽的成名曲〈La Copa De La Vida〉: Go, Go, Go!Ale, Ale, Ale!Go, Go, Go!Ale, Ale, Ale!Go, Go, Go!Ale, Ale, Ale!Go, Go, Go!Ale, Ale, Ale!Go, Go, Go!Ale, Ale, Ale!……
讚歌中間還穿插黃健翔在2006年德國世足賽,義大利對澳大利亞賽中的激情點評:
球进啦!比赛结束了!邵峰获得了胜利,淘汰了球球。他没有再一次倒在老婆面前,伟大的男人!伟大的男人中的男人!邵大大他爹今天生日快乐!全中國的老公万岁!……
小女孩摘著花圃的花,突然像是感應到了什麼,回頭對夏志傑說:「不好,要出人命。」 本來兀自興奮的邵峰,雙手抱住胸口,他感覺自己的胸口像是被塞上千斤巨石,跪倒在地,向球球伸手:「救我。」 球球緩緩伸手,想要回應邵峰的手,但她的手伸到一半又縮了回去。 「對不起,老公。」 「快……叫救、護……車……」 「手機打不通,好像壞了。」 「去……借……」 倒臥在地上的邵峰,把求救的眼神扔向坐在路邊的保安。 保安倉皇說:「糟糕,我的手機沒電了。」 邵峰口吐白沫,在沒有一滴水的柏油路面,被自己不爭氣的心臟殺死。 死亡的過程,就像在一條看得到盡頭的隧道中轉換,你覺得自己像是喝醉了一般,迷迷糊糊的從一個充滿光的洞,穿越黑暗的道路,然後走到另外一個充滿光的洞口。 「怎麼搞的……」邵峰發現自己不知何時,處於一個站立的姿態。他看見夏志傑身邊的小女孩,也看見另一個自己,面部猙獰,嘴角冒著白泡泡,倒臥在地上。 邵峰瞬間明白了許多事,他猜到自己死了。他靜靜的走到小女孩和夏志傑身邊,想稍早还用看怪物一般的眼神,看著夏志傑。 這一回,邵峰的眼神先是一陣空洞,然後變得像是叢林中被狩獵的小兔子,驚恐而迷茫的望著他們。 「我記得電影裡頭這樣演,通常表是一個人死了。我死了?」邵峰對於自己說出來的話,感到有點荒唐,可他還是不由自主的說了。 小女孩點點頭。 「操他大爺的,我怎麼就死了呢!」 「看情況,估計是心肌梗塞。」夏志傑起身,拍了拍褲管上沾染到的泥土,回應道。 「我該怎麼辦?」 「等待。」 「等什麼?」 「等他們來接你。」夏志傑右手食指指著天空方向。 「他們什麼時候會來?」 「你準備好的時候,他們就會出現。」 「什麼叫準備好?」 「看看你的腳下,如果妳對活著還有太多的眷戀,你的腳就沒辦法離地,來自天上的人就不會來,就算來也帶不走你。」 夏志傑補充說:「你有什麼捨不得的嗎?」 邵峰:「慢,我的老婆、孩子都看不到我,為什麼你看得見?」 「總有些人看得見別人看不見的,這是人世間的真理。」 「那我现在該何去何從?」 「放下你内心的執著。」 「你。」邵峰瞥見夏志傑胸口的名牌,改口說:「志傑兄,但我不知道自己執著什麼。」 「每個人都有放不下的,每個鬼也有放不下的。」 夏志傑從胸口掏出一包煙,遞給邵峰。 邵峰遲疑了一下,他想自己到底能不能抽這煙,他已經不是人了,是鬼。鬼能抽人的煙?這也許是個測試,也許鬼真的能抽煙。或者這煙有古怪,是給鬼抽的,不是給人抽的。 邵峰的手觸碰到煙盒,有一種穿越的感覺,好像自己其實還是人,地上的是一尊以自己外型為藍本打造的蠟像。 救護車來了,他們把躺在地上那尊「蠟像」裝上車,就像清道夫裝走地上的狗屎。 「跟我走。」夏志傑對邵峰招招手。 「我們要去哪裡?」 「去一個可以解開你心結的地方。」 「有這樣一個地方?」 「有的。」 「你做過心理諮詢嗎?」 夏志傑幫邵峰點煙,邵峰注意到夏志傑用的打火機,打出來的火帶有妖豔的紫色。
#2 大叔 陋巷。 一座城市隨處可見被遺忘的地方,那裡是你從高德地圖或百度地圖,都能找著,但可能一輩子都不會去的角落。 這些角落住著活生生的人,但他們跟其他都市中的菁英份子沒多大關係,菁英份子不會來這樣的地方,除非有特殊理由,譬如來救濟他們,好顯得自己高尚,或是看錯導航,才會來到這片夾在市中心、高架行經,與郊外高級住宅區的過渡地帶。 有人稱這裡是七期都市開發區的保留區,有人稱為深有潛力,只是拆遷失敗的都市重劃區。 這裡的居民可不喜歡這樣文謅謅的字眼,他們稱這片臨江的社區為「江城」。 江城有座小碼頭,二十年前,當江兩岸沒有那麼多橋樑,每天熙來攘往的車輛和行人好不熱鬧。 碼頭邊賣杏仁茶、油條和酥餅的小販,能忙活一整天。 現在的江城,除了房子是老的,幾塊石頭和紅磚夾雜的道路是老的,就連空氣味道也都變得過份乾淨,再也沒有渡輪煙囪飄散出來的燒煤味。 江城多是一排排六層樓的老公房,在老公房的後頭,還有更老的一片房子,有點石庫門的味道,但小巷弄的感覺又不夠整齊,故又有點像是北京胡同的擁擠。
二五六弄,十號。 一棟外觀看起來比兩層樓矮一點,平房高一點的磚房。差不多是兩臂長等的窗內,有張松木書桌。桌上擺了許多書,一本硬皮的德文版《夢的解析》,壓在一堆打印出來的論文上。論文頁面的空白處,寫了許多注記,扭捏的字體,說明作者並不期盼別人看得懂。 「朝偉!」一位大媽拍著磚房的大門,在外嘶喊:「高朝偉!」 一位臉上有點鬍渣,穿著優衣庫經典燙印T恤,卡其色七分褲,腳踩雷根鞋,雙手提著五花肉和幾樣蔬菜的男子,遠遠看見大媽拍門,三步併成兩步走過來。 「牛嬸,著急什麼呢?」高朝偉對大媽微笑說,掏出鑰匙打開大門。門縫有點不規則,說不准是門老舊的關係,還是大媽拍打這一陣造成的後遺症。 「出事啦!」 「不管什麼事,我先把東西放了。」 牛嬸抓住朝偉的手,直愣著要把他帶走。 朝偉不得已,只能把肉和菜扔在入門旁的茶几上,跟著牛嬸一路往她家的方向走去。 牛嬸的屋子前面有個小院,院裡養了兩頭牛,一頭黃牛,一頭奶牛。 「朝偉,你說我家萌萌是怎麼了,從昨天開始,連一根草都不吃。哎唷!看到牠這個樣子,我心都揪起來了。」 「牛嬸,萌萌是黃的,還是這個黑白相間的啊?」 「黑白相間的。」 「等會兒,我又不是獸醫。」 「好歹你是心理諮詢師,自從我把萌萌的孩子送走,牠的食慾就一落千丈,你倒是勸勸牠,要牠想開一點。」 「牛嬸您自己已經有想法了,還要我來幹麻呢?」 「好好好,都怪我多嘴,那你用你的方法試試。」 「那我得把萌萌牽到一個只有我們兩個人能說話的地方。」 「為什麼?」 「諮詢是極為隱私的一種對話方式,我們說什麼,要是您都聽得著,這樣會洩漏來談者的隱私。」 「你說怎麼好就怎麼好,只要萌萌願意好好吃飯,我都沒意見。」 「對了,那費用……」 「你把萌萌治好,未來一個月我每天擠萌萌的奶給你當早餐。」 「一言為定。」
朝偉把萌萌牽到樹下,扣著鼻環的繩子繫在樹下如章魚腳一般,盤根錯節的間隙。 朝偉靠坐在大樹下,萌萌望著牠。 「你等一會兒,現在還不到時候。」 朝偉在等人,等一個能夠和牛溝通的人。他從口袋拿出手機,滑了滑,點擊微信中的一位聯絡人「小白」,發出語音信息:「牛嬸要我跟她的牛做諮詢,需要妳翻譯。」 畫面傳來文字訊息:「我在上課,不方便聽語音,你打字吧!」 朝偉把剛剛說的話,打成文字訊息發出去。 小白很快回覆:「這就來。」 三月天,清晨只有六度,到中午氣溫飆升到二十度。樹陰下,二十度的氣溫經徐徐微風吹拂,讓人臉上肌膚溫暖的同時,身體卻被喚起某種極度適合睡眠的狀態。 「天氣真好,就是少了一頂草帽。」朝偉嘴裡的字,到句子後頭已不大容易聽清,他睡著了。 鼻頭的刺激,朝偉搔了幾下,不得要領,止不住那股癢勁兒。 一睜眼,小白拿著一根野草,朝他鼻孔撓。 「來了怎麼不說一聲?」 「我正在說呢。」 「別淘氣,先把正事幹了。」 「對你來說是正事,對我來說不是。這次牛嬸又給了你什麼好處,讓我們的高老師願意對牛談心。」 「舉手之勞,幫幫街坊。」 「那我有什麼好處?我可是為了你放棄睡午覺的時間,等一下還得回學校上下午的課。」 「請你吃碗餛飩麵。」 「成交。」 小白把書包放下,立花中學四個大字,原本是黑色的,被小白用原子筆塗成天空藍的顏色。書包側邊掛了一個布做的四葉草吊飾,布的表面起了毛球,還有點變色,看來比書包跟在主人身邊的時間還長。 淺藍色的制服上衣,荷葉領口的邊緣能見到小白深邃的鎖骨。一張圓臉,和清瘦的上半身有點不搭。 小白摸著萌萌的頭,人和牛的臉頰耳鬢廝磨,十分親熱。 萌萌低聲嗚了幾下,小白邊聽,邊點頭:「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朝偉在旁邊看著兩人的互動,從褲子口袋掏出自製的小筆記本,以及一枝套著不鏽鋼筆桿的鋼筆。筆記本用黃色方格紙的替蕊切割,作為巴掌大小,由於是自己切割,頁面的邊緣有些粗糙。 「萌萌說牠願意跟你說話。」小白對朝偉說。 「好的,那牠同意讓妳擔任翻譯,於諮詢時在場嗎?」 「大叔,你以為你還有選擇啊!我肯定要在場。快點快點,我為了你翹了中午睡午覺的時間,等一下還要趕回學校上下午的課。」 「好。」朝偉翻開筆記本,對萌萌宣讀《諮詢同意書》的內容。 「萌萌你有什麼問題嗎?」朝偉讀完同意書的內容,並確認小白也翻譯完成後,問道。 萌萌嘶鳴一聲,小白說:「萌萌說沒問題。」 「行,蓋個蹄印後,我們就開始。」
#3 城 夏志傑、小女孩和邵峰,行至江邊。 指著遠方一片房子,夏志傑說:「那裡就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邵峰看見那排房子的天空,有一片黑壓壓的烏雲,仔細一瞧,那不是烏雲,而是盤旋在天空的烏鴉。 「這條該不會就是黃泉?」邵峰說。 「只是一條江。」 「過江有什麼呢?」 「有人,還有一位諮詢師。」 「幫鬼做諮詢的諮詢師?」 「只要你有想法,能表達,他就能做。」 水岸邊有一艘木舟,夏志傑和邵峰先後上船。 小女孩站在岸邊,沒有要上船的意思。 「她不跟我們走嗎?」 「她怕水,走不了。」 「我們就這樣把她丟在這裡嗎?」邵峰想到自己的孩子,動了父愛,不忍和小女孩分開。 「他不會走遠,相信我。」 「你是什麼人,為什麼在酒店工作,又和死人打交道?」 「酒店大廳裡頭總是徘徊許多找不到出路的靈魂,他們和許多活人一樣,有家歸不得。」 「這樣說來,你幹兩份活,其實是一份活。」 「哈哈,正是。」 夏志傑和邵峰,兩人划槳,費了將近半個小時,到了江的對岸。 碼頭上只有幾艘木舟,以及一艘外觀斑駁的帆船。 上岸後,他們朝店舖方向走,這些店舖都空著,不過都有人整理。 只有兩間店舖在做生意,一間是小雜貨鋪,一間是賣特產的商店。兩間店隔著一道牆,由一對兄弟經營。 兄弟看見夏志傑,招呼道:「大哥,一個人划船?好興致。划船累了吧,來我這裡買瓶紅牛。」 「不了,我要找人。」 「需要我給哥指點條路嗎?」 「不用,我知道在哪裡。」 「你請便。」 邵峰跟在夏志傑身後,對於身邊的景物,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他家是村裡第一戶用磚蓋房子的,多少同村的孩子羨慕他,冬天房子不怕風,夏天房子不怕雨。 小區裡綠樹成蔭,老人家在樹底下乘涼,看見夏志傑這個外人,難免指指點點,但也沒人用侵略性的眼神注視他。 「二五六弄,是這裡了。」夏志傑依著路牌,轉進一個小巷。 「這個小區挺靜。」 「年輕人這時間都出外工作了,留在這裡的多半是老人和小孩。」 走到十號門口,夏志傑敲了敲門,沒見回應。 「裡邊沒人?」邵峰問。 「嗯。」 「要不我穿牆進去看看。」邵峰有點興奮,想到自己莫名其妙死了,但當鬼有當鬼的好處。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死人也有死人的規矩,不要觸碰規矩,以免攬禍上身。」 「我都死了,還能攬什麼禍?」 「生者做死事會折壽,死者犯生事恐禍及家人。」 夏志傑字字鏗鏘,邵峰聽到「禍及家人」四字,嚇得打了一個寒顫。雖然他和老婆感情不睦,但夫妻一場,總歸是愛過的。即使最後情份更像是親人,缺少情愛,但愛情的結晶卻積累了兩個人曾經有過的真情。傷害孩子的事,邵峰做不出來。 「我們去探探情報。」 回到巷子外,小區的幹道上,夏志傑跟剛才打過照面的老人家問:「老大爺,有人知道住在二六八弄裡的高老師上哪裡去了嗎?」 「高老師,你是說高朝偉啊?」 「高朝偉?這什麼鳥名字。」邵峰死後,還是第一次樂得笑了。 老人們互相探問信息,聲音老響,好像深怕周圍百公尺內會有人聽不見他們討論的內容。 邵峰有點不高興,對夏志傑說:「這些老人也真是,說話那麼大聲跟吵架似的。」 夏志傑不動聲色,牛嬸從另一條巷子穿出來,她聽見有人提到高朝偉,從家裡出來看熱鬧。 「朝偉他幫我治牛去了。」牛嬸鉅細靡遺的把萌萌不吃草,請朝偉做諮詢的事情說了一遍。 「是在江邊嗎?」 「對對對。」 牛嬸很熱心,帶著夏志傑和邵峰往江邊去。邵峰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剛剛還怪老人們說話大聲,沒想到就是這種不禮貌的熱情,讓鄰里之間的消息得以暢通。這是高度依賴手機和電話的現代人,所不熟悉的一種情感交流方式。 一頭乳牛,在江邊靜靜吃草,看樣子,牛解開了心結。 「朝偉。」夏志傑打招呼道。 「志傑,怎麼有空來?」 「帶個朋友來。」 「朋友,在哪裡?」 「在我身邊。」 夏志傑拉兩人彼此認識,「這位是高朝偉,高老師。這位是邵峰,邵先生。」 「『看不見』的朋友,很高興認識你。走吧!我們去諮詢室。」 朝偉牽著繩子,準備拉牛往小區走。 邵峰對夏志傑說:「也不用做什麼諮詢,我其實沒什麼煩惱。」 「若是如此,你應該早早升天才是。」 「也許有其他原因。」 「譬如?」 「我也不知道,我第一天當死人。」 邵峰的腳訪彷彿有千斤重,他決定不再走了。 他自己也很難說明現在是什麼樣的情緒,眼前這個牽牛的人,還有這個西裝筆挺的青年,他們能夠幫助自己在這個迷茫的時刻,提供一個方向。 很多時候,迷茫的時刻只要隨便有個方向,就能讓一個人堅持走下去。即使對於未來充滿未知,甚至是充滿恐懼,都好過讓自己拄在當地,看著自己手足無措來得好。 「我不想走了。不知道為什麼,我只想靜靜看著這條江。」 夏志傑喫了兩口煙,朝四周一陣吞雲吐霧。 「江讓你想起什麼了嗎?」夏志傑問。 邵峰看著江水,江水從西面往東面流動。他的腦中記憶,宛如逆流而上的鮭魚,從東面往西面游動,想尋找過往回憶中的關鍵點。 本不該在西下時間,還高掛當空的豔陽,再次發力。順上游方向看,一片沿著江岸生長的洋蘭,在陽光及水面波光的相互輝映下,散發出紫色的光彩,這種紫色的光彩,稍早邵峰也曾見過,好似夏志傑為他點煙時的火焰。 「我記得洋蘭,」 「酒店前面的洋蘭嗎?」 「不是,是記憶裡的。」 「記憶裡的什麼地方?」 「以前我住的小區,樓裡出來的院子,有人中了洋蘭。紫色的,我經常去拍那些洋蘭。」 「為什麼呢?」 「可能我喜歡紫色的緣故,而且剛好拍洋蘭能用來測試我的相機。」 「你都一個人去嗎?」 「有時候一個人,有時候帶著我的孩子。」 「你喜歡洋蘭嗎」 「我不怎麼喜歡,現在這些洋蘭沒香味,我不喜歡沒有香味的花。」 「到了其他地方,看到洋蘭你都會去拍嗎?」 「好像是如此,就像之前在酒店前面看到洋蘭,我拍了那些洋蘭……」
邵峰陷入了回憶,幾年前的某個夏日午後,碰上寫字樓進行消毒作業,他提早兩個小時下班。 他去黃昏市場買了西紅柿和雞蛋,要給大大做他最喜歡的西紅柿炒蛋。 當然還有老婆球球最愛的馬鈴薯燉牛腩,牛腩前一天就買好了,可家裡生抽不夠,剛好在市場一起買。 除了老婆、孩子愛吃的,邵峰還買了一條鯽魚,打算配老豆腐、薑絲和黃酒燒湯。 豐盛的一餐,為了迎接老婆和孩子從娘家回來。 傍晚六點多,差不多老婆和孩子該到家了。邵峰遲遲沒有接到電話,忍住聯繫他們的念頭,為的就是給他們一個驚喜。 七點,門口有了那麼一點聲響,都會讓邵峰以為是老婆和孩子的聲音。他想起這一次老婆離家前,兩人起了一點口角。 球球希望邵峰陪她回家一趟,邵峰原本一口答應,之後又反悔。這不是第一次,邵峰反悔,他不喜歡面對丈人,當年娶球球,丈人極力反對,認為他大學畢業幹個小銷售,沒辦法照顧自己的女兒。 邵峰胸無大志,但他不甘心被人瞧不起。拼搏了好些年,孩子也上小學,勉強買了一間市區兩室的房子,談不上體面,但至少餵飽一家老小沒問題。 和丈人之間的心結,球球作為橋樑,極力想要幫兩個男人和解。 邵峰嘴巴領情,心還是不願意放下身段,他內心有對丈人的憎恨。 這份憎恨轉移到了妻子身上,在經濟、社會地位等方面,邵峰無法報復丈人,那就報復在他的女兒身上。 邵峰和妻子的感情一天天不合睦,很大一部份就出在邵峰出於自卑感的復仇心,把他和妻子的距離越推越遠。 儘管他的內心,仍有對妻子的感情,所以他會為即將歸來的妻子和孩子準備晚飯。但他仍免不了內心對妻子,以及丈人的詛咒。 「Go, Go, Go!Ale, Ale, Ale!」邵峰的手機鈴聲響起,接起電話,是警察打來的。 妻子和孩子坐的遊覽車出了交通意外。 趕到醫院,邵峰和老丈人終於見到面,也確實因為球球搭起的橋,用的是她和大大的屍體。 從那之後,邵峰就有了遊覽車恐懼症。出行絕對不搭類似遊覽的大型巴士,連搭公車都會讓他感到不舒服,特別容易暈車。
「沒事吧?」夏志傑把手搭在單膝跪地的邵峰肩上,安慰道。 「我想起來了一些事,唉……你說人怎麼就這麼想不開,為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 「來根煙?」 「謝謝。」 邵峰的顫抖的手,特別費力的將煙送進嘴裡。夏志傑為他點煙,這次邵峰看煙的火焰顏色,不再是詭異妖豔的紫色,而是再正常不過的橘紅色。 尼古丁有點鎮靜的作用,邵峰用力吸了一口煙,覺得剛剛頭暈目眩的緊張感,一下子得到改善。 「我好多了。」邵峰吐了一口煙,說:「真没用,都死了還那麼膽小。」 「有些事情不會因為死亡而消失。」朝偉說。 「你不是看不見我?」邵峰訝異說。 「通過菸草的煙霧,便能看見。」 邵峰這才明白,剛剛夏志傑朝是故意朝四周吐了幾口煙。 「我的記憶有點混淆,我記得我的妻兒死於交通意外,那麼我白天爭吵的對象又是誰呢?」 「有的時候記憶會在我們的腦中重放,那些記憶儲存在大腦裡,同時儲存在靈魂裡。你的大腦死了,靈魂還在,所以記憶還在。」 「什麼意思?」 「人的煩惱,有時是自己欺騙自己。更詳細的說,是大腦欺騙我們自己,讓我們做出違背自己心意的事。現在你少了頭腦的束縛,讓自己完全沉浸在更深處的記憶裡,放下要用頭腦去控制自己,包括控制回憶的念頭。」 邵峰放下對頭腦的控制,他看著自己的形體,儘管如肉身一般,但他知道已經不是原來那句沈重、會散發各種氣味的有機物。 「把自己沉浸在對於過去的畫面裡,專注去看,就像自己坐在一個電影院裡頭,看著螢幕上的畫面。你是旁觀者,不再是裡頭的演員。不要想改變過去,因為過去已經發生。」朝偉緩慢吐出一個又一個堅實的字句,每字每句都像刻在卲峰的心口。 卲峰閉起雙眼,扮演對於回憶的旁觀者,放下對回憶的控制,包括改變過去的念頭。 回想白天他看見自己屍體的場面,他記得屍體旁有妻子和孩子,他們目睹一切,還有惶恐的保安。 可是現在再次回想,確實有對母子,但更加仔細的回想,那對母子不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是不認識的陌生人。 保安那時候的姿態,其實不是在勸架,而是在阻止他衝向大馬路。 自己倒下的位置,也不是在人行道上,而是在馬路中央。 「我不是被掐死的,我是被車撞死的。」邵峰恍然大悟,他弄明白過去,才弄明白現在。 夏志傑和朝偉交換了眼色,他們知道邵峰終於跟上了自己刻意遺忘的記憶。
早上,夏志傑酒店當班,他看見紅衣小女孩的靈魂。通常有紅衣小女孩出現的地方,預示可能出現的死亡。 小女孩總是在找媽媽,眷戀著生前對母愛的飢餓,所以她們永遠在人間排徘徊,久而久之,她們成為引起靈魂聚集的誘惑者,也成為容易出現死亡場面的指標。 邵峰在酒店對面的馬路,喃喃自語,看來有幻視和幻聽的症狀。 夏志傑看見紅衣小女孩,又看見邵峰,猜到了可能發生的情況。他想阻止悲劇發生,可惜為時已晚。 當邵峰瘋了似的衝向遊覽車,夏志傑能做的,只剩下帶他到江城,見見「送行者」。 送行者是人間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引路人之一,他們幫助迷茫的靈魂找到方向,讓執著於塵世的靈魂學會放下,和過去的自己好好道別,重獲新生。 夏志傑扶起邵峰,跟著牽水牛的朝偉。 「慢慢来,别著急,我們明天談。」朝偉對邵峰說。 溫度驟降,江水表面漸漸漫起白霧。 「啊!」夏志傑清呼一聲。 「怎麼了?」朝偉問。 「沒什麼。」夏志傑想起對岸的小女孩,不知道小女孩現在又去何方,那個地方是否又會有新的死者,又一個迷茫的靈魂。 江的彼岸,小女孩拾起洋蘭的花瓣,在地上排出一張女人的面孔。 小女孩是按照眼前那位站在木舟的女子,她的面容排的。 球球望著對岸,她在找老公。
|
|
| ( 創作|小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