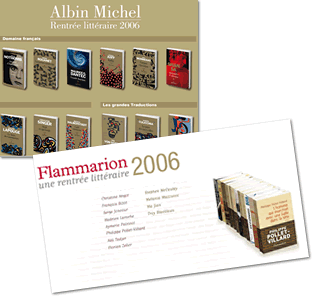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0/08/24 03:09:01瀏覽455|回應0|推薦5 | |
2010.7.18思鬱
優秀出版人士怎樣煉成 用暢銷書養小眾書 1919年12月,龔古爾學院根據傳統在特盧昂飯店吃了中飯,然後宣佈了龔古爾獎的評選結果,普魯斯特的《在少女們身旁》險勝多熱萊斯的《木十字架》:六票對四票。之前已經有人放風出來說多熱萊斯肯定能獲獎,他的出版商阿爾班.米歇爾(Albin Michel)也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印好了一萬冊的新書就等獲獎後上市。但是最後獲勝的是伽利瑪出版社(Éditions Gallimard),據說這次的評選的結果是因為五年以來,每屆的龔古爾獎都頒給了有關戰爭的小說,現在戰爭已經結束了,也許應該獎勵一部與戰爭沒有太大關係的純文學作品。總之,現在爭論結果已經沒有了多大的意義,關鍵的問題是如何把手頭庫存的書賣出去。龔古爾獎評選之後的十幾天,普魯斯特的書已經賣空了,他的出版商加斯東.伽利瑪在新書上包上了腰封,上面注明了「龔古爾獎」,而阿爾班·米歇爾精明地在多熱萊斯的書上包上了腰封,上面也印了幾個大字「龔古爾獎」,下面有幾個幾乎看不清的小字「十票得了四票」。這種明顯的銷售策略讓加斯東.伽利瑪(Gaston Gallimard)氣瘋了,他把阿爾班告上了法庭,要求對方撤掉腰封上的文字,並賠償損失。阿爾班甚至沒有辯解就乖乖照辦了,最終賠償了兩千法郎的損失。但這些損失根本不算什麼,對一本書來說,任何新聞都會有利於圖書的銷量。 之所以提及這段法國文學史上的八卦,源於近期關注了《阿爾班.米歇爾:一個出版人的傳奇》一書。阿爾班.米歇爾創辦的出版社在法國並不算最具有實力和最為搶眼的出版社,尤其對比伽利瑪出版社的純正和高端的文學品味,但阿爾班的出版社本來就不以文學圖書取勝市場,它顯得更為大眾化和通俗化。這種獨特的圖書品味來源於阿爾班早年在書店當學徒的經歷。阿爾班本是鄉村醫生的兒子,十多歲時孤身一人來巴黎闖天下,在一家劇院後面的露天書店裡當學徒。他不但是個吃苦耐勞的好夥計,而且長久以來鍛煉了一副好眼光,能夠揣測讀者的閱讀心理,估摸出圖書市場的暢銷走向。這種獨特的經歷在他成為一個出版商後成為了他獨特的看家本領,對一本書有著靈敏的嗅覺和直覺。阿爾班當學徒時就已經發現了圖書市場有兩類書比較好賣,一種是那些有著廣泛聲譽的名垂千古的純文學作品,另外一種是那種「很輕巧的故事,很快能讀完但也很快就會被忘記的東西」。後者正是阿爾班初涉出版業時候的主打圖書,他需要依靠這種圖書積聚實力和資金才可能盡可能多涉獵到其他種類的圖書。這種出版和行銷策略至今也是很多出版社和圖書公司的做法,用暢銷書養小眾書,平衡讀者的各種品味。阿爾班用這種暢銷書策略很快就在出版界站穩了腳跟,組建了阿爾班.米歇爾出版社。他後來在接受採訪時經常提到這種獨特的經歷:「出版業是一個充滿激情的行業……這個行業需要對公眾十分了解,所有的出版人都應該在零售書店進行實習,以了解讀者的口味。我之所以成功,就是因為在零售書店做了十年。」
阿爾班的經歷總讓我拿他與加斯東.伽利瑪的出版社相互比較。當然,龔古爾獎的爭奪上只是他們之間眾多較量中的一個小例子,伽利瑪的出版社雖然創建較晚,但是比較這兩個出版社,你會發現伽利瑪的出版社似乎具有一種貴族品味,創建伊始,背後有雄厚的資金支持,《法蘭西文學》獨特純正的文學品味,聚集以安德列.紀德為首一大批法國大作家的支撐,而且出版的大部分圖書都是純文學作品,甚至「介入」到法國一系列的政治和文化爭論。我們提及法國文學的時候,第一個想到的是伽利瑪出版社,總覺得它代表了純正的法蘭西文學,在這點上,阿爾班.米歇爾出版社似乎有點黯然失色。但是對阿爾班而言,他把握住的更為大眾和通俗化的圖書市場,他把出版的觸角伸及到各種領域,科學、歷史、兒童、文學甚至美食領域,他的目標本來就是要把出版社創建成為一個具有各種知識領域的綜合性質的出版社。我們回到開篇提到的1919年龔古爾獎頒發後,阿爾班麾下的多熱萊斯《木十字架》雖然 敗給了加斯東出版社的普魯斯特,但在阿爾班精明的銷售策略之下,這本小說仍然輕易過了五萬冊的銷量。但如果對比阿爾班出版的其他圖書,這本書的銷量很是一般,阿爾班麾下的其他作者的圖書不少都有五、六十萬的銷量。但對一個出版人而言,一本圖書除了商業上的成功,還必須有其他的因素,比如圖書的口碑,作者的合作,對讀者的影響力等等。
加斯東.伽利瑪談到作者時有句名言,作者就是婊子,誰有錢就跟誰。也難怪伽利瑪如此咬牙切齒 地痛恨某些「忘恩負義」的作者,一旦出名就轉投其他出版社。任何一個出版人都會面臨這種境況,對阿爾班來說,在選擇作者的時候也會無比的謹慎,他所著眼的還是作者的作品:「在選擇作者的時候,我不關心他屬於哪個流派,也不關心他是哪個組織的。我所希望的是書要寫得好,結構要棒,能讓廣大讀者感興趣。對我來說,出版主要的目的就是:打動讀者。」對阿爾班來說,他不想成為一個只出文學作品的出版人,因為出版本身就是一個包含所有知識和娛樂領域的大概念,而不是單單撕裂開來成為了某種人的獨特的文學品味。在大眾和菁英之間,在輕文學與純文學之間,甚至在文學與非文學之間不應該看作某種對立,而應該成為相輔相成的領域。阿爾班有句名言說,文學是一種奢侈。言下之意是說,我們更應該把文學變成一種人人都能消費的生活品,而不是曲高和寡的奢侈品。 從現今出版業的境況看,阿爾班的目標似乎已經達到了,大眾文化和通俗文學統領了出版領域,但是文學仍然是一種「奢侈」,一種幾乎沒人在意惹人嘲笑的「奢侈品」。
在這個行業從事了四十年之後,我只能告訴你一件事情,就是我們永遠也無法預知一本書的命運…… ──加斯東.伽利瑪 加斯東.伽利瑪的出版帝國 加斯東.伽利瑪,這是一個既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名字。熟悉,那是因為如果你關注法國文學,如果你讀過普魯斯特、紀德、沙特、卡繆,如果你稍微了解二十世紀法國歷史上那些著名的思想論爭,你總會在一掃而過的字裡行間看到這個人的名字;陌生,也許在你閱讀那些法國名著的時候,你在對圖書封面上那個大名鼎鼎的作家的名字頂禮膜拜的時候,從沒有注意過在封面的下方,很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也會有一個人的名字會出現。加斯東.伽利瑪,他通常不是我們讀過的那些法國文學名著的主角,但假使沒有他的存在,也許我們永遠看不到這些書的出版。加斯東.伽利瑪,以一種缺席的方式存在著,在那些出版的圖書中間。論及二十世紀法國文學史,加斯東.伽利瑪是個繞不開的名字,某種程度上,他是法國文學的同義詞,他的身影無處不在,他的一生無愧於他一手鑄就的出版帝國。 1908年代時,像法國這樣總是孕育文學和浪漫的國度,盛產了許多才華橫溢的文藝青年,他們作風前衛,愛好文學,而且總覺得與前輩作家們格格不入,所以有時候只有操辦自己的雜誌,才能發表自我的主張。那一年年底,就有這樣「六個尋找刊物的人」,尋找到一些評論家的支援,開始創辦自己的刊物,他們給未來的雜誌起了名字叫《新法蘭西雜誌》。別小看這個不起眼的文學雜誌,他們的組織中的靈魂人物老大哥可是安德列.紀德。也許我們該慶幸,當年法國有那麼多的文學小團體,各種小雜誌,大都是辦過幾期之後無疾而終,再無下文,《新法蘭西雜誌》雖然也是歷經波折,但總算在紀德的精神感召下,得到了許多名人的支持,堅持了下來。1910年的時候,雜誌雖沒盈利,但已經贏得了很高的聲望,刊物品質和厚度也都有所提高,雜誌的幾位創辦人,又開始動起了心思。他們打算創辦一家出版社延續雜誌的成功,他們需要一個合適的管理者。按照當時的想法,這個人「他必須……足夠有錢,能給雜誌的財務添磚加瓦;足夠無私,能不計較短期利益;足夠謹慎,能把此事辦好;足夠愛好文學,能品質第一回報第二;足夠能幹,能樹立自己的威信;足夠聽話,能執行創始人其實是紀德的指示」。就這樣,年紀輕輕的花花公子加斯東.伽利瑪進入了他們的視野,「儘管他才二十五歲,也沒有文化方面的專長,但他有一種嗅覺,能正確地判斷作品的品質,直奔最好的東西,不是理性方面的原因,而是由於喜歡」,就這樣,加斯東成了他們的出版商。 怎麼才算一個合格而優秀的出版商?或者乾脆這樣問,加斯東.伽利瑪是怎樣煉成的?從一個整日無所事事的花花公子,成為一個優秀的出版商,這其中的轉變豈是如此簡單?別忘了,最初的時候,創始人對他的要求是「聽話」「執行」指示就可以了。伽利瑪不是傀儡,他把出版當成了自己的事業,毅然放棄了安逸的生活,向前輩們學習,主動去跟作者們溝通和交流,他身體力行,尤其是在出版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的事件上,他變得日漸成熟。也許我們現在已經很難想到了,普魯斯特的這本書的出版也是一波三折,幾經退稿。當時在伽利瑪出版社遭到了紀德的草率拒絕後,他自費與另一個出版商貝納爾.格拉塞合作出版了這本書的第一部。結果已無懸念可言,出版後的小說受到的好評讓紀德和伽利瑪後悔不跌。伽利瑪想要彌補紀德犯下的錯誤,把普魯斯特和《追憶似水年華》爭取過來。正如皮埃爾.阿蘇里所言:「普魯斯特事件是加斯東.伽利瑪從同行那兒挖作者方面的第一次真正的嘗試,換句話說,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潛在的競爭。他在一個十分棘手的領域初試身手。」也許,不僅僅如此,這次事件給伽利瑪更多的啟示,讓他意識到他要擁有出版社的權力,要有獨立發言權,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能把個人的意志任意淩駕於出版社和作者的利益至上。
1919年,紀德和伽利瑪的權力之爭終於得到了裁決,伽利瑪開始真正領導出版社,紀德更多隱居了幕後,成為了《新法蘭西雜誌》和伽利瑪出版社的精神代言人。也正是在這之後,伽利瑪出版社開始有了一個很獨特的部門:審讀委員會。這是個掌握著圖書出版生殺大權的神秘部門。別忘了當初是紀德一人就斃了普魯斯特的稿子,這樣一個人的決定太過於主觀和草率了。正是這次事件讓伽利瑪意識到審讀書稿的嚴重性,他挑選的審讀員無一例外都懂得閱讀、研究、分析、解釋、批評一部稿子。只有經過審讀委員會的一致意見後,他才會考慮是否要出版這本書。這樣謹慎而負責的做 法無疑保證了圖書的品質和眼光,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這種審讀會佔用很多時間,有時候會缺乏靈活性,從而錯失很多作者和作品:普魯斯特、塞利納、莫利亞克、讓.科克多、馬爾羅、蒙泰郎,當然,還有當年名不見經傳的沙特,也是經過兩次退稿之後才被接納。與這些偉大的作家擦身而過,注定是伽利瑪的遺憾,但是這種遺憾卻是以另外一種方式獲得了彌補:自伽利瑪出版社創辦至伽利瑪1975年去世,他麾下的圖書作者有六次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二十七次龔古爾獎、十八次法蘭西學院小說大獎、十二次聯合獎、七次美第奇獎、十次雷諾多獎、十七次費米娜獎…… 二十世紀上半葉,本來就是多災多難的多事之秋,且不論那些數不清的小打小鬧,單是兩次世界大戰已經讓人民苦不堪言。伽利瑪生平對戰爭深惡痛絕,他總覺得英雄主義是最虛偽的東西,他寧願當一個活著的懦夫。為了逃避兵役,他什麼都試過,裝瘋賣傻,裝死,自貶為懦夫。他只承認自己是一個出版商,是一個愛好文學的商人,所以兩次世界大戰的經歷無論對他的事業還是他本身都影響甚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二戰期間,法國淪陷時期,如何出正常版就成為了一個大問題。如果出版商不迎合德國人的主張,他們就會受到強迫。而德國人在審查圖書方面顯得十分靈活,他們從不自己動手審查圖書,而是讓法國出版商根據「歐洲新國家社會主義的原則」自己來審查,而自我審查的好處就是可以獲得配額發放的紙張。這方面,伽利瑪的老對手,格拉塞表現比較直接,他選取了直接向德國人示好的方式:「呆在自由區的法國人應該明白,佔領者尊重所有值得尊重的東西。在巴黎做個完全的法國人,體面地從事自己的職業是得到允許的。」伽利瑪明白,如果想得到紙張,必須去找德國人,聽從他們的要求,服從他們的願望,甚至於他們合作,但是合作也有不同的方式,他採取的是陰奉陽違的那一種。他甚至向紀德解釋必須把出版看作「是一種抵抗行為,而不是合作的表現」。他在戰爭期間出版了一些從德國翻譯過來的符合佔領者意願的作品,比如歌德的作品。他還是經常使用模糊的語言:為了避免書刊審查,他需要經常出入佔領者的地方,參加聚會和宴會,與許多德國人示好;另一方面,他也允許出版社提供場地給地下抵抗組織開非法會議:「加斯東這個幻想主義者在辦公室裡牽著無數看得見或看不見的線,一邊讓對抗的雙方能以文學的名義和平共處。」這種模糊的態度在戰後終於產生了作用,在戰後清算運動中,許多作家都曾為他辯護,尤其是在戰後威望很高的沙特和卡繆。其中沙特的證詞中有這樣的句子:「我以個人的名義擔保,我對加斯東.伽利瑪充滿了敬意,他對我來說是一個朋友……所以我認為,責備伽利瑪出版社,也就是責備阿拉貢、保朗、卡繆、瓦萊 里和我本人,總之,是責備所有參加抵抗的知識分子和所有由他出書的人。」譴責加斯東.伽利瑪就是譴責抵抗主義的菁英作家,聽了這樣的忠告,誰還會去清算這家出版社?但是他的老對手格拉塞就沒有這麼幸運,幾經審判和訴訟,元氣大傷,幾乎一蹶不振。
|
|
| ( 休閒生活|網路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