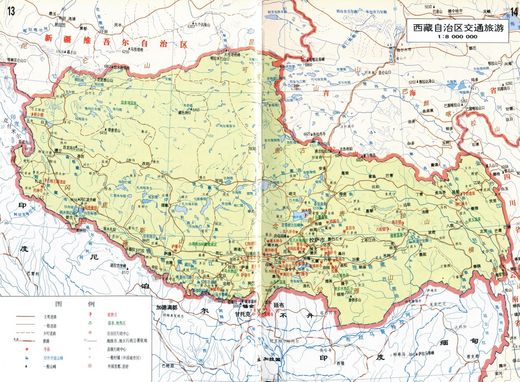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08/08/29 08:18:00瀏覽1497|回應1|推薦0 | |
關於西藏的過去和未來 -魏京生先生「給鄧小平的信」讀後
魏京生先生的道德勇氣世所共知,無論今後的政治演變如何,筆者對他個人歷史的尊敬永存。在這封公開信裡,魏先生的直言無忌和理想主義一如往昔,更以他的自身經歷給歷來充滿政治宣傳和辯論的西藏問題不少清新之意。 魏先生說他對西藏歷史的研究「不過淺嚐輒止,只鱗片爪」,但文中比比皆是的廣泛和終結性論點與上述的謹慎頗有衝突,而且這些政治含義相當重要的觀點又沒有具體論證支持——事實上有許多與「第三者」的研究結論完全不符。無庸諱言,西藏是一個極其複雜和敏感的問題。正惟如此,嚴肅的討論最好能盡量避免感情用事和宣傳色彩。另外,人性在歷史上大致是個常數,近期內也沒有「基因突變」的前景,所以不能因政治現狀的醜惡便對過去有種「人心不古」的牧歌式憧憬;至於未來,即使再有「人權」「自決」等高尚口號,國際政治也不見得會比過去真正「理想主義」多少。 從「對著幹」的原則講,魏的公開信(以下簡稱魏文)的確是相當尖銳和發人深省的好文章;但從有關的西藏歷史講,它的「宣傳色調」太過明顯;至於對西藏問題的將來,儘管文中已經認識到一點南亞的傳統地緣政治,濃厚的理想主義依然處處可見。這種強烈的政治內涵使得魏文在很大程度上成為與所「批判」的中共《白皮書》一樣的「政治文章」,而非嚴肅的歷史討論。 本文所用參考資料:為了避免可能的偏見,中文資料盡可能用原始記錄(《大清歷朝實錄》、《東華錄》等)。滿清時期西藏和南亞藏語區有關歷史主要依據西方和其他「第三者」的研究,例如意大利藏學家Luciano Petech的著作和在荷蘭Leiden出版的傳統亞洲歷史學術期刊《通報》及其專題系列,近代西藏史的主要文獻是當今美國西藏現代史權威Melvyn C. Goldstein的巨著。 關於西藏歷史 似乎有人說過,歷史很難是客觀的,因為每個人都從自己的角度和切身利益「解釋」歷史。在西藏問題上,這自然使得從滿清、民國到中共的任何中央政府官方文件以及大部分漢人寫的歷史被人認為帶有強烈偏中國政府的傾向。基於同樣原因,西藏地方政權及其代言人的文章和看法也就有對等的偏頗。好在從上世紀起許多西方學者出於各種政治動機和文化需要對這一地區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態度嚴謹和取材廣泛(事涉漢、藏、梵、蒙、「回」、俄、英等文字)的嚴肅學術成果。只要對作者的政治背景有所了解(例如來自英管納粹戰俘營的逃亡犯Heinrich Harrer和印度英國殖民當局在拉薩的官方代表,在親中央政府的熱振活佛被親英派扣押殺害以及與此有關的色拉寺院大批喇嘛被圍殺事件中有極深捲入嫌疑的黎吉生Hugh Richardson),閱讀這些「第三者」的研究可以讓我們對西藏問題的歷史和未來獲得冷靜和有益的知識。 西藏近代史離不開黃教,或喇嘛教的黃教教派(而非魏文中籠統的喇嘛教)。一個基本問題便是黃教如何獲得它今天在西藏的地位?黃教和中共在此事上似乎有相當程度的諱莫如深的默契。眾所周知,黃教的光大並不發生在西藏本土,甚至連達賴一詞都不是藏語。然而在西方的一項常識卻極少為漢、藏文獻公開承認:黃教在西藏的地位起源於「外族」的直接軍事征服。簡言之,五世達賴依靠青海厄魯特和碩特部顧實汗(固始汗)對藏區的軍事佔領和對非黃教的其他喇嘛教派、原始本教殘餘勢力以及傳統世俗藏王的迫害誅殺獲得黃教在西藏的「一統天下」——用通俗的話可以說是一個引進並建立在外族軍力上的「兒喇嘛」。達賴喇嘛的「世俗權力」源於1642年顧實汗的「供奉」為藏文史料自己承認[1]。五世達賴這一「開國歷史」被西方學者不客氣地指出帶極大政治風險[2],其早期結果便是西藏的實際政治權力長期掌握在受滿清封為「遵行文義敏慧顧實汗」及其繼承人手裡[3]。 上述事實對了解西藏歷史和未來至關重要。第一,它說明黃教在西藏的權力從一開始便和「外族」的捲入形影不離。以後自拉藏汗、準噶爾策旺阿拉布坦派兵侵藏、滿清對西藏建立直接控制起,一直到印英殖民勢力的進入、十四世達賴入印和今天在國際上的奔走等等,無一不是這個「傳統」的延續。第二,與魏文中達賴和滿清皇帝地位「平等」的宣傳相反,這段「開國歷史」充分錶明達賴喇嘛「神權」的來源及其有限性。毛澤東一生諸多虛偽,但「槍桿子裡出政權」一句確實將一大堆表面漂亮的「政治禮儀」後的實際把戲赤裸裸地捅了出來,至今尚為西方作者津津樂道。即使今天我們還是可以從「銀河號事件」中看到它的影子。離開外族的「槍桿子」,達賴的「神權」從何談起? 魏文中「國教的最高領袖」、「各自成為對方的主要存在條件」、「雙方的法律地位」「平等」等等抬高黃教實際政治地位的論點和達賴喇嘛及黃教的一廂情願的傳統自我宣傳大致相通,但在基本歷史現實甚至一般常識上難以自圓——一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經濟體系、廣土眾民,以「儒教」立國的皇帝如何會和一個自身存在都依賴外族軍隊的「宗教領袖」平起平坐? 比如美國出於國內近三分之一的天主教徒人口和冷戰時期政治關係等必須與教廷及其在美「組織」維持良好關係,但這關係決不「平等」。傳統由加爾文、長老會諸新教教派支配的美國主流政治對墮胎權利的堅持,便是一例。最近被菲律賓天主教會公開指責為「美帝國主義」的彼邦美援計劃生育計劃,又是一例。遠的不說,羅馬教廷和1789以後的歷屆法國政府就從來不平起平坐,誰佔上風不言而喻。教皇被法國長期禁閉(1809-1814),十數名紅衣(樞機)主教因為冒犯法國政府,紅衣被改為黑衣之類[4]的戲劇性史實(文革時的「黑幫」源遠流長)充分說明政權和神權不可能處於平等地位。意大利比法國更有忠於教皇之名,但是我們眼見的是1870年意大利完成統一,奧軍被逐,教廷領地遂入意國囊中,教皇也只好自稱被「劫」,身不由已,在梵蒂岡成階下囚。這樣的「劫持」竟維持到墨索里尼法西斯黨當政,才以簽訂「同心協定」作為台階收場[5]。一二論客喜歡以西藏比羅馬教廷,以大清比意大利,以證明兩者互不隸屬,平起平坐。但是證諸西洋史實,結論適得其反。緣故正如斯大林所問[6]:「教皇有多少個師?」語極無禮,但不失實事求是。拿破崙就更乾脆,政由己出,毫不客套,搶了皇冠自行加冕,教皇唯唯,觀禮而已。後來兩者徹底鬧翻,教皇下詔只能「驅逐皇帝出教」,阿Q一番;皇帝一下詔便把教皇給逮了[7]——不失神權政權「平等」的生動表現。 但是說明黃教領袖「神權」力量的最好實例是滿清和準噶爾帝國的殊死鬥爭。與清廷自我宣傳不太一樣,這場鬥爭鹿死誰手開始並不明顯。例如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農曆八月一日烏蘭布通之戰的勝利被某些現代漢族學者認為當然[8],事先卻大有明代「土木之變」的迴響(噶爾丹正是當年瓦刺領袖也先的第十二世後代):入夏,噶爾丹沿克魯倫河和喀爾喀河推進,勢如破竹,諸蒙古部「不能禦」;農曆六月壬申清聖祖下諭動員八旗軍隊,丁亥,檄諸軍「量馬力疾行」;北京直接受脅不說,與大清祖基滿洲的聯繫都有被噶爾丹包抄截斷的危險;六月二十一日,滿蒙聯軍和準軍會戰於烏爾會河,準軍銳利火器之下「我師大北」;聖祖既定的「親征」突因「聖躬違和」取消;皇兄(裕親王福全)、皇弟(恭親王常寧)和皇長子(允〔礻是〕)等大批皇家要員受命出征,聖祖最信任的「舅舅」內大臣佟國綱、佟國維亦「參贊軍務」,等等。戰事的激烈和清廷的危殆從佟國綱的陣亡和聖祖後來自己承認「噶爾丹乘勢直抵烏蘭布通,距京師未及七百里」略見一斑[9]。 最重要的一點:當時黃教的最高「神權」——隱瞞五世達賴死訊(1682),繼續以達賴名義發號施令的第巴(桑結嘉錯)從始至終支持噶爾丹[10]。就這樣在毫無「神權」幫助的情況下,滿清從康熙二十六年(1687)噶爾丹開始騷擾外蒙的困難情況起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昭莫多大捷短短十年便全面擊敗了曾橫行中亞薩馬爾罕、布哈爾、哈薩克、布魯特、賽拉木等地的噶爾丹,注定了雍正和乾隆兩朝徹底摧毀準噶爾勢力,滿清邊界直跨帕米爾的結局。更要緊的是在這期間滿清獲得了虔信黃教(!)的喀爾喀外蒙古的全面效忠(與僧格林沁成為僅有的兩位配享太廟的蒙族、第一世超勇親王策楞及其世子成袞扎布是最好的例子[11]),清廷在外蒙古的直接主權由此確立,滿蒙全面聯盟成為中國重演漢唐在西域及中亞的歷史角色的關鍵——這一切都是在和黃教最高「神權」「對著幹」的情況下實現的。斯大林問「教皇有多少個師」的道理在此一展無遺。 這樣魏文中所謂黃教對清廷的「神權」作用的實際幅度便大成問題。事實上在黃教已徹底被清廷支配後清高宗(乾隆)仍立意翦除從伊犁河谷到北疆一帶的黃教厄魯特勢力[12],任其由信伊斯蘭的維吾爾等族取而代之[13]——何有靠達賴「維持版圖」之考慮? 魏文中有大量類似上面專為與中共《白皮書》「立異」的經不起史實考辯的論點,無法一一細評,僅舉主要幾項簡略討論一下。 駐藏大臣。魏文在此事上的大部分論點都與基本史實不符。首先駐藏大臣的確起源於準噶爾入侵事件的平定(康熙五十九年1720),當時的藏語文獻便開始對滿清入藏官員有滿文amban(大臣)的對譯記錄[14]。駐藏大臣的正式確立是雍正六年(1728),首任者為僧格和馬喇(或後者的繼任邁祿,即藏語文獻中所謂的僧大人和邁大人)[15],遠早於魏文所稱的「平定西藏的屬國尼泊爾的叛亂」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廓爾喀戰爭。第二,魏文對駐藏大臣權力的描述(「聯絡使臣」,「權限遠低於英國駐文萊大使」等等)亦與第三者的研究結論不符。例如Petech對此的總結是:駐藏大臣自1751年起擁有〔對西藏政府〕「控制和監督」(control and supervision)大權,自廓爾喀戰爭結束頒行「藏內善後章程」後更有「直接參與(direct participation)西藏政務」的權力,這一情形一直維持到1912年[16]。 達賴喇嘛在西藏的地位以及與中國皇帝的關係。如前所述,魏文的論點無視「槍桿子裡出政權也出神權」這一遺憾但無法迴避的「現實政治」。有清一代,達賴喇嘛在西藏的實際權力和地位數經滄桑。例如從1706到1720年,與滿清結盟的和碩特拉藏汗絕對控制西藏,其傀儡達賴不為黃教大部分「組織」承認,達賴位置實際數年出缺[17]。後來七世達賴為滿清?720年一手「捧立」,成為「中國人的政治創造」[18]。在1727-28的西藏「內亂」後清廷更將所有世俗權力給予忠心耿耿的軍閥頗羅鼐,達賴喇嘛沒有絲毫權力(slightest power)的事實連當時駐拉薩的天主教傳教團都有記錄[19]。 另舉數小例:1728年正式首任駐藏大臣捲入的第一件大事便是不顧許多藏官求情,將在雍正五年到六年西藏「內亂」的十五名「禍首」如數正法,其雷厲風行在五年後編寫的藏語文獻中仍有深刻反應[20];另一件事是當時清廷覺得達賴之父對局勢不利,為了「以杜釁端」,假惺惺的一紙請上北京的邀請,乾脆請達賴暫時走路,連班禪來講情都不管用。烏蘭布通戰役中陣亡的色思特(滿州鑲白旗)之子,當時率軍入藏的左都御史(從一品)[21]查郎阿(字松莊[22])一句話就毫不客氣地把魏文認為和皇帝「法律地位」「平等」的黃教最高精神領袖的隨員限定在八十人以下,還是靠頗羅鼐說話才把人數增加到兩百(至少有三份藏語史料記錄了這一事件[23])。到1735年清廷最終允許達賴回駐拉薩時又對達賴父子的權限甚至住地百般限制[24]。以此看,魏文的「內部自己治理完全自主」的說法從何談起? Petech的研究結論便是:近代西藏達賴喇嘛主持的政治結構代表滿清經反复政治「實驗」後發現的控制西藏的「最後解」[25]。假惺惺的「平等」和不管細務的表面文章之外,誰是拉薩真正的政治boss由此不言而喻。但魏文暗示的「兩相情願」並非全無道理,因為據西方人研究,自從元朝以來中國皇帝在西藏始終享有傳統的moral supremacy[26]而西藏的僧侶階層則always pro-Chinese[27]. 西藏「可以毫不費力地從中國分裂出去,像外蒙古那樣」。這反映對近代史的認識問題。沙俄/蘇聯在外蒙古的作用盡人皆知,如果沒有這層關係,我想不大會有人認為「外蒙古獨立」會這樣「毫不費力」(其中一項有趣插曲是外蒙和中國政府攜手企圖阻止烏梁海從外蒙的「獨立」[28])。所以西藏的「毫不費力」的獨立大約也得靠「列強」的「慫恿」——其實也就是英國。我們再來看一下此事的可能:第一,傳統Great Game對手俄國/蘇聯(包括其在相鄰的新疆「既得利益」)對英國這種咄咄逼人攻勢的必然反應(可參看邱吉爾自己對1944年十月九日晚上在克里姆林宮裡與斯大林兩人紙上瓜分巴爾幹繪聲繪色的精彩描述[29])。第二,中國似乎並非那樣「虛弱」——抗戰初期中國政府下令在玉樹修建可供轟炸機起落的軍事機場[30]和中國國民黨對印度國大黨獨立運動的大力支持(包括蔣介石夫婦1943年不顧英方阻擋親訪甘地)。事實上,英國在1943年正式警告拉薩,在中國為二次大戰大作努力時,如果噶廈政府某些成員繼續其小動作而引起重慶中央政府的軍事反應,則印英將愛莫能助[31]。 西藏近代社會歷史。這裡魏文出於對中共傳統政治宣傳的逆反,不免接受了黃教及其代言人同樣自我宣傳的「香格里拉」牧歌。但不管來自中共還是黃教,宣傳總歸是宣傳,中共固然有高唱「階級鬥爭」的習慣,西藏當時的具體社會狀況也絕非十四世達賴等自我吹噓的那樣「美好」。這方面美國現代藏史權威Goldstein的詳盡研究大可開人耳目。 比如不免被中共誇張的黃教傳統殘傷肢體的酷刑懲罰,略微讀一點Goldstein就知道並非子虛。以龍夏被活生生取眼致瞎(原定死刑再加龍夏兩個兒子截肢刑的「從寬處理」)的過程[32]為例,任何有基本天良的人讀了都不可能無動於衷。砍腿截耳之類則更普通[33]。還想替舊西藏制度粉飾的人不妨去看一下美國著名《生活》(Life)畫報1950年11月的彩色圖片報導。至於藏區下層人民生活的艱難不幸,連十四世達賴自己都不得不閃爍其詞地吐露一點[34]。 Goldstein書中許多舊拉薩童謠這樣的第一手資料更證實了「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民困」的道理,絕非黎吉生等有個人榮辱牽扯在內的「歷史學者」能夠否定。 魏文對黃教當局「改革」計劃的讚歌也是一面之詞。當時西藏具體社會結構是各寺院、地方領主實際各自割據為政(包括獨立的武裝力量)[35],出了拉薩,噶廈政府的社會影響力非常有限[36]。傳統「階級鬥爭」理論固然誇張,但是參照最富「民主參政」習慣的美國的「槍枝管制」問題的例子就知道讓一個掌握絕對政權和「神權」的「既得利益」集團主動放棄其傳統利益的艱難,廉價的lip service除外。 「改革者」龍夏的悲慘結局是最好的見證,藏軍中某些激進親英分子居然會策劃剝奪十三世達賴的所有世俗權力的陰謀[37]更說明以達賴為首的「神權」對「改革」會有多少真心。 魏文提到「英國」式「改革」更無視冷酷的國際「現實政治」,即大部分「改革」必須通過印英殖民當局的「襄助」。事實上藏軍軍官到1950年還在用英文發號施令而軍樂隊則在演奏「天佑我王」之類的英國老調[38]。黃教對所有喇嘛教地區「念念不忘」眾所周知,在喜馬拉雅山南麓攫取了從拉達克、哲孟雄(錫金)、大吉嶺(原屬哲孟雄)到不丹等大片原喇嘛教藏語區的殖民老手如何會養虎自噬? [39] 關於國際政治 對西藏歷史,特別是黃教的「神權」的理想化理解以外,魏文的另一主要問題便是許多對國際政治近乎天真的看法。篇幅所限,我們又只能對主要幾點略加評論。 南斯拉夫。正如王若望先生剛到海外時一篇指責中共與南共勾結支持塞爾維亞的文章一樣,魏文的敘述完全不符合實際事實。南斯拉夫的問題不是所謂「絕不承認其他民族的自決主權」,而是在各方面紛紛插手的情況下對「自決權」的濫用。負責調停衝突的美國前國務卿萬斯從1991到1992年力主推遲對前南國各共和國獨立的承認和歐洲由法國人權活動家、前司法部長Robert Badinter主持的調查委員會僅認可斯洛文尼亞和馬其頓兩共和國基本人權狀況符合承認條件都是眾所周知的例子。凡搞國際關係和巴爾干問題的人都知道事態的急轉直下與德國借統一之勢,挾獨步歐洲的經濟實力迫歐共體,特別是極不情願的英法兩國,作出承認克羅地亞等國獨立的決定有關。事情與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在內的歷史恩怨和羅馬教廷的作用也不無關連(天主教的克羅地亞現國旗上還有二次大戰時屠殺了數十萬塞爾維亞人的納粹傀儡政權的標誌,能不令克國境內的大量正教塞族人心寒並也「自決」起來? )。 南斯拉夫的例子其實表明在「醜惡的現實政治」中,「民族自決」已經成為某種政治武器:什麼自決結果予以承認(例如「北愛爾蘭六郡」),什麼則否認(例如愛爾蘭全島),乃是變少數為多數,多數為少數的手段。因此興起的「對策」——「民族清洗」更將現代政治和戰爭的醜惡和殘酷都提高到「嶄新階段」(指程度而言——民族清洗的成功先例有以色列在美國政府和納稅人大力支持下幾十年的慘淡經營和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島的我行我素)。 蘇聯/俄國。魏文的有關看法顯然沒有顧及俄國最近國會選舉顯示的令人擔心的趨向——前蘇聯/俄國的這齣戲遠遠沒有唱完。據《紐約時報》報導,即使在所謂「民主鬥士」葉利欣的克里姆林宮裡也已有一個二十四小時工作的「中樞」在遙控和影響前蘇聯各地的矛盾和衝突,格魯吉亞和阿塞拜疆的「自決中的自決」把戲便是例子。而美國出於伊朗伊斯蘭勢力等地緣政治考慮,對俄國的這種動作也「視而不見」。這場「人人自決」的火一旦燒大,加上前蘇聯境內到處皆是的核武器,不知道會給人類帶來什麼結果。 印度。魏文最後雖然略有提到,但遠遠未及事情的真相。對比「受盡摧殘」的「西藏自治區」今天的藏族絕對多數,喜馬拉雅山南麓歷史上蓬勃的藏語文化現在只有不丹在危機四伏中碩果僅存(魏文一字未及曾經非常興旺的拉達克文化[40])——印度在此區域的地緣政治目的早就超過了「司馬昭之心」,但西方媒介對此幾乎一片沉默。 對西藏問題演變極有關係的是查謨——克什米爾,不是指時下每月橫死在印度軍隊手下的無辜穆斯林人數遠惡於「西藏問題」但大多數西方政治家絕口不提的「人權情況」,而是祖孫數代執印度政治牛耳的尼赫魯/甘地「王朝」與希特勒的某種對比:出身奧地利無賴的第三帝國元首必須讓奧國加入德國和源起克什米爾婆羅門大族的印度尼赫魯世家[41]始終不讓克什米爾「自決」乃是心有靈犀——這和假定李光耀家族成員有朝一日成了中國總統,那麼新加坡作為獨立國家的日子將屈指可數是一樣的政治必要。 (另一趣事是達賴流亡政府的「行在」歷史上屬於克什米爾王國——克什米爾的現狀如有變動將會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 ) 黃教創始人(青海湟中人宗喀巴)和光大過程(大明順義王、土默特蒙古俺答汗於萬曆六年在青海仰華寺首將達賴稱號贈予「藏僧鎖南堅錯」,是為達賴三世——前二世後來追封)之外,西藏近代大量宗教領袖包括過世不久的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和當今十四世達賴喇嘛都來自青海。入藏「勤教」的和碩特顧實汗和當今達賴的漢族親嫂子均為青海民族雜居傳統的明證,且不說雍正以後當地行政權力實際來自何方。但是從黃教包括達賴本人關於所謂西藏Amdo省(即青海)的大量「預行宣傳」,我們不難猜到西藏一旦「獨立」後的下一個政治熱點。 (讀者可參考「民族清洗」老手以色列對猶太教聖地耶路撒冷死活不放和塞爾維亞在其「發源地」Kosovo的鐵腕。) 未來展望 本文主要討論西藏問題的歷史和現狀。對於將來,水晶球並不存在。儘管個人對魏文提出的增加漢藏兩族彼此了解尊重和互助互惠的經濟往來兩點甚為贊同,但在看到許多善良願望導致的悲慘結局後,筆者甚至並無勇氣加入賣膏藥的行列。漢藏(羌)兩族幾千年來的歷史恩怨無法迴避,很大程度上這與兩者文化語言和居住地的密切關係有關。如果我們接受羌姜兩字同源的通行理論,則華夏文化一開始就含藏羌成分。現代漢藏學研究顯示藏語可能是漢語最近的親戚(漢藏語專家Nicholas C. Bodman近來更提出傳統漢藏語系另分漢和藏緬語支的做法可改為漢——喜馬拉雅語系,而漢藏則構成其中最密切組合這樣的新觀念[42])。當然語言學和政治是兩碼事,但這的確也促使我們去尊重和了解藏族及藏文化。 尊重和了解是雙向的事。在指責中共大量政策失誤和損害藏人感情的同時,我們也不應忽視另一方的動作。除了出於現代政治需要對自己並不光彩的歷史大作不負責任的美化,黃教一些領袖包括達賴本人的許多言行並不有助於雙方的尊重和諒解,稱當年從印度一路燒殺擄掠到拉薩的英國榮赫鵬上校為老朋友,拜榮赫鵬「遠征」之賜(達賴原文),才有拉薩英國代表團和榮赫鵬迫拉薩所籤條約,因此證明西藏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這樣的驚人之語[43]還不在其次。 西藏問題並不是民族自決一句話就完事:與魏文不符事實的藏人「幾千年來的慣例」恰恰相反,我們已經顯示西藏的宗教政治從來離不開青海新疆四川雲南等民族雜處地區的藏族和外族(!)的直接捲入。黃教某些領袖的言行充分指明西藏「本土」問題一旦「解決」後的下一個「動向」。我們從前南斯拉夫和前蘇聯的例子上難道還沒看夠在民族、宗教錯綜複雜地區玩「自決」的後果? 除了傳統的達賴——班禪矛盾(滿清和歷屆中央政府自然均曾利用,近年來拉薩的街頭騷亂中已出現這種矛盾激化的跡象),在顧實汗的「鐵血政策」下漏網的其他喇嘛教教派尤其是紅教(rNinmapa)的殘餘勢力對從此獨大的黃教而言一直如芒刺在背。紅教掌權的不丹王國歷史上頻遭黃教軍事進犯便是例子[44]。據《紐約時報》和《新大英百科全書》等記載報導,在達賴指示下堅持不入不丹國籍的西藏「難民」於1974年居然策動起一項謀殺不丹國王進而「奪權」的政變陰謀,達賴喇嘛親兄嘉樂頓珠直接捲入[45](為了掩飾,達賴在自傳裡專門強調當時二十二名著名難民被不丹政府逮捕,包括達賴駐該國代表在內,而對胞兄嘉樂頓珠間關潛踪之事隻字不提[46])。這類對達賴喇嘛流亡政府「和平,慈悲」形像大有損害的真人真事,西方媒介自然不會張揚(最好的例子是1961年11月肯尼迪政府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辦公室以「美國國家安全」為理由「說服」《紐約時報》不刊登一則關於中央情報局在科羅拉多州秘密訓練西藏「自由戰士」的報導——十二年後揭露此事的書名就叫《撒謊的政治》[47])。但黃教人士寄人籬下時便敢如此「反客為主」,對今後的事態發展不啻是極好的提示。 另外黃教在西方維持良好的「好生惡殺」、「非暴力」形像也經不起仔細推敲。Goldstein的巨著充分說明黃教執政的舊西藏決不是這樣一個和平幸福的「香格里拉」,1959年西藏「起義」前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從軍事訓練到空投武器人員等的巨大作用連達賴本人都不諱言[48]。此後「堅持武裝鬥爭」的組織如「四水六崗」(ChuShi GangDruk)全靠外國軍事經濟支援更是包不住的事實[49]。達賴筆下「英勇頑強」的「自由戰士」最終淪落到只敢在境外騷擾當地無辜土人的地步[50],一旦山姆大叔於1970年代初起改變對中國的地緣政治戰略,自由鬥士們便不免兔死狗烹——以前一直敢怒不敢言的尼泊爾當局在美國默許後於1974年將這批綠林好漢如數全殲[51]。 如此種種內部矛盾和外界干預都說明西藏問題可能不是一廂情願的「尊重了解」就能了結的。 結語 西藏是個錯綜複雜的問題,所有善良的人們都希望看到一個和平、長久和有效的解決方法。但是高尚動聽的「原則」和「主義」無法掩蓋和消除幾千年曆史顯示的基本人性(悲觀者所謂的人類劣根性)。法國大革命期間Madame Manon Philipon Roland(1754-1793)在斷頭台前留下這樣一句發人深省的話[52]: O Liberte! O Liberte! que de crimes on commet en ton nom! (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惡假汝名以行!) 把「自由」一詞換成「平等」,共產主義的歷史提供了羅蘭夫人箴言的近代解釋。只要再將「自由」換成「民族自決」,今天的北愛爾蘭、巴爾幹半島以及前蘇聯外高加索和中亞細亞等地便正在上演這句話的現代版。 另外在「人權」「自決」的時髦口號幕後,幾千年國際政治遊戲照舊。巴爾幹今天的慘劇和前蘇聯日益嚴重的民族衝突和主要大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人人可見。對東非、西非(例如美國以前的「寵兒」利比里亞)以及克什米爾、海地、東帝汶等地駭人聽聞的人權問題,歐美各國不是坐唱高調而作壁上觀,便是出於地緣政治考慮而默不作聲。如此種種,不一而足。最近披露的冷戰時美國利用弱智兒童等從事自己承認與納粹「醫學實驗」類似的輻射實驗更揭示了專制和「民主」之間的實際距離。 中亞、南亞已經是個宗教政治衝突的火藥桶:印巴世仇(雙方都有核武器),前述克什米爾「自決」問題,印度國內日益嚴重的教間、族間衝突,前蘇聯解體後的爛攤子(包括中亞遺留的大量核武器),俄國對其舊日榮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再加上寄人籬下時就想以武力解決幾百年「芒刺」紅教問題而成為不丹「主要安全問題」(《新大英百科全書》語)的黃教「和平,慈悲」喇嘛集團及其從青海,內外蒙古直到西伯利亞的舊日徒眾,……。任何人在討論西藏問題時都必須慎而又慎,歷史的教訓和現實的例子比比皆是,善良的願望和美麗的口號與實際效果和具體解決絕不是一回事。一旦捅出亂子,向北是青海新疆乃至中亞——古老的絲路和未來中國、朝鮮、日本以及俄國遠東與中亞和歐洲經濟聯繫的重要環節,向東則是中國(人口)第一大省和長江中下游——下世紀經濟發展的重要中心(光緒三十年《東方雜誌》第九期就有西藏英夷之禍「必進航巴蜀,順流而下荊門,自此而南方諸省」的見解)。我們的共同願望是看到各種族、宗教的和平共處和安居樂業,而不是巴爾幹、外高加索和中亞今天的玉石俱焚。望各位三思。 (作者保留版權) (作者保留版權) 註解: 註解: [1] Tucci, Giuseppi, Tibetan Painted Scrolls, Libreria dello Stato, Rome, 1949, pp.66-67. 参见Grousset, Rene, L'empire des steppes, Attila. Gengis-Khan. Tamerlan, 4 ed. Payot, Paris, 1939(以下簡稱Grousset), pp.602-3. [2] 例如Halkovic, Stephen A. Jr. The Mongols of the West, Indiana University, 1985, pp.7-8. [3] Petech, Luciano,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XVIIIth Century: 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Tibet, 2nd Ed. T'oung Pao Monographie I, E.J.Brill, Leiden 1972, (以下簡稱Petech). p.8.顧實汗封號見《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七十四順治十年四月。 [4] Atlas zur Weltgeschicht, Taschenbuch Verlag, 1968. [5] Christelijke Encyclopedie, the Netherlands, 1960, Vol. V, p.462. [6] Churchill, Winston S. The Gathering Storm, Houghton Mifflin Co. Boston, 1948, p.135. 五世達賴親赴北京朝覲後清世祖命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達賴的政治作用,馬上招來“我朝荷天之佑,征服各處,以成大業,當年並無〔達賴〕喇嘛也”之論,與斯大林所問相映成趣。皇帝呢? “奏入,上曰:‘不必〔向達賴喇嘛〕詢問事情’”(《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七十一順治十年正月)。 “國教”之為政治花瓶,一目了然。 [7] 拿破崙自行加冕一事,見De Rosa, Peter, Vicars of Christ: the dark side of the papacy, Crown Publishers, New York 1988, p.128.教皇被法國扣押一事,出處同[4]。 [8] 例如袁森坡《烏蘭布通之戰考察》,《歷史研究》1983年第四期。 [9] 此處所引,除“我師大北”和“未及七百里”句出蔣良驥《東華錄》卷十七,餘均據《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亦參考《平定朔漠方略》。 [10] 除《清實錄》外,可參見前引Halkovic書頁18, Grousset p.612,以及Petech, Luciano, Notes on Tibetan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 T'oung Pao, LII(1965/66). p.284. 此事與噶爾丹從小被其父巴圖爾琿台吉(和多和親)送去拉薩在五世達賴下“修行”不無關聯。還俗喇嘛噶爾丹後來的所作所為(東征西討之外再加殺兄、殺侄、殺岳父等)是黃教傳統自我宣傳的“慈悲、惡殺”的極佳註解。 [11] 參見《清史稿》。 [12] 參見《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平定準噶爾方略》及《清史稿》等。 [13] Grousset p.618. [14] Petech p.86. 亦可参见Grousset p.613. [15] Petech pp.113,145,156,255. 另参见Rockhill, The Dalai-Lamas of Lhasa, T'oung Pao, 1910, pp.38-43和Haenisch, E. Bruchstuke aus Geschichte Chinas, I, T'oung Pao, 1911, p.197. [16] Petech p.260. [17] Petech p.237. [18] Petech pp.237-8. [19] Petech p.238. [20] Petech p.149. [21] 黃本驥《歷代職官表》卷二。 [22] 見《清史稿》。 [23] Petech p.152. [24] Petech, Luciano, Aristocracy and Government in Tibet:1728-1959,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Roma, 1973, pp.33-34. [25] Petech p.260. [26] Petech p.14. [27] Petech p.76. 參見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9(以下简称Goldstein), p.144. [28] Underdown, Michael, Tuva, 见Krueger, John R. Tuvan Manual, Indiana University 1977. pp.6-7. [29] Churchill, Winston S. Triumph and Tragedy, Houghton Mifflin Co. Boston, 1953, p.227. [3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白崇禧先生訪問記錄》,台北,1988,页569-71和851。 [31] Goldstein pp.385-90. [32] Goldstein p.208. [33] Goldstein p.123. 亦可参见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M.E. Sharpe, 1987(以下简称Grunfeld), p.p.22-23. [34] Tenzin Gyatso the 14th 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HarperCollins, 1990(以下简称Freedom),p.54. [35] Goldstein pp.25-26. [36] Goldstein pp.15-16. [37] Goldstein pp.124-35. [38] Grunfeld p.38. [39] 參見Grunfeld p.39. [40] 例如Petech, Luciano, The Kingdom of Ladakh: c.950-1842 A.D.,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Roma, 1977. [41] Tariq, Ali, An Indian Dynasty, New York, 1985, p.4. 参见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42] Bodman, Nicholas C. 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Data toward establishing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in: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 s,F. van Coetsem and L.R. Waugh ed. Leiden, E.J.Brill 1980, p.39. [43] Freedom p.61. [44] Rose, Leo E. The Politics of Bhuta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以下简称Rose) pp.59,63. [45] 关于此事,除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989 printing)外,可参见《纽约时报》1974年六月二日报导,Rose pp.121-22, Grunfeld pp.201- 02, Foster, Laila M.,Ph.D., Bhutan, Children's Press, Chicago, 1989, p.46以及U.S. Dept. of Army, Nepal and Bhutan: Country Studies (formerly Area H andbook for Nepal, Bhutan, and Sikkim), 1993. 最後一份美國國會圖書館主持的最新官方出版物隻字不提有關細節及達賴胞兄之名充分說明新舊地緣政治和David Wise所謂的“撒謊的政治”繼續在大行其道(參見註[47])。 [46] Freedom p.191. [47] Wise, David, The Politics of Lying: Government Deception, Secrecy, Power,Random House 1973(以下简称Wise), pp.163-78. [48] Freedom p.191; Grunfeld pp.149-53; Wise pp.162-78. [49] Freedom p192, Wise p.177 notes. [50] Freedom pp.127,192. [51] Freedom p.193. 另见Goodman, Michael H. The Last Dalai Lama, Shambhala, Boston, 1986. [52] Lamartine, Alphonse de, Histoire des Girondins, Tome second, Librairie Plon, Paris, 1984, p.635.
|
|
| ( 時事評論|政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