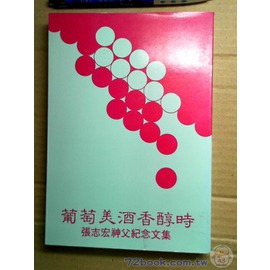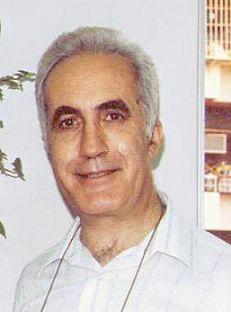摘錄自見證月刊奉獻生活年座談 (見證月刊2015年1月號)
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
應芝苓修女
嗯 !我就說故事吧!一個不喜樂的人成為喜樂的人。
我曾是台北市立國樂團專任團員,這樂團是國內第一個專業國樂團。樂團的工作就是演奏,專業樂團的要求是必須看到任何譜就能馬上正確演奏出來,速度的快慢、音量的強弱依照指揮的詮釋。當然每個人在團練之外的時間把自己的樂器練到純熟,演出為我其實是一個壓力,膽戰心驚的,出岔了沒得修正,無法真正投入音樂中,一個朋友對我說:「奇怪!妳跟妳的琴不是合一的,首席就是人與琴很合一。」但同時,我常常覺得在台上演奏很空虛,就是為了掌聲。看到台下一大片黑鴉鴉的人群,可是跟這些人沒有互動。樂團成員彼此之間的關係也很奇怪,是一種競爭的關係,而我的態度是生硬的,不會跟大家打成一片。有不少的批判和不滿, 一個同事說:「真不知道妳在想什麼,每年妳都說要離開樂團,卻只會在這裡抱怨、不滿。」她說得沒錯,讓我正視這問題:為什麼我不離開呢?
坦白說,是我離不開,樂團的環境與一般職場相比還是很單純,我怕自己無法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怕人吃人…..,我的想像力把我自己關在一個安全的圈圈裡。
而耕莘青年寫作會是我可以伸展的一個天地,那裡是一個讓我可以跟人們有交集、能放鬆開懷的地方,每個人都很珍惜這個有愛、自由參與、不怕做錯、受陸達誠神父及幹事們包容與鼓勵的環境。學習寫作之外,深深體會到一種愛的氛圍。在接任總幹事時,唯恐無法使這種愛傳遞下去,特別花時間閱讀「葡萄美酒香醇時」張志宏神父紀念文集,以能深入了解創會神父的精神。之後,有會員問我是否基督徒?那是有生以來頭一次被這樣問,那位會員說感到我身上發出一種愛。無知的我很不以為然地卻回答 : 愛不是基督徒的專利,不是基督徒也可以懂得愛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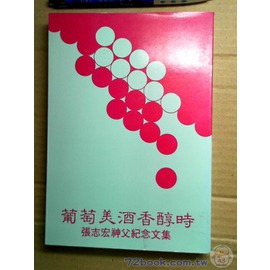


說也奇怪,自此,過去曾因利害衝突時發生的自私行徑的記憶,或生活上的小事似乎在嘲笑著我的愛的能力。尤其意識到在樂團的我和寫作會的我很分裂,直到三十歲領洗前的慕道過程,差距慢慢縮小。尤其跟樂團到美國迴演出的那四十五天的經驗。行前,請梁德佳神父給我一堂要理,好讓這四十五天可以消化,他給了一堂很具體的要理課:1.一切以愛德為優先,若有衝突,就讓,不要爭。2.若有人身體不舒服,需要照顧,留下來陪伴。3.欣賞天主透過這國家所展現的文化。最後是祈禱。 當時同寢室的同事懷孕三個月,而且是頭一胎,我竟然不必她開口,主動做一切為她不便的事,選擇靠冷氣的床。有一次,在旅行巴士中為了捍衛這位同事跟一位男同事衝突,還用羞辱的字眼回敬。掙扎了半天,祈禱後,我開口先向對方承認我的錯,對方也承認自己的疏失….等等。那四十五天都在努力“做功課”,而得到的就是一種“做到了”的喜樂,那是一個內在的改變。旅程結束,回到台北,同事跟我說:「謝謝妳和妳的天主。」 她篤信藏傳佛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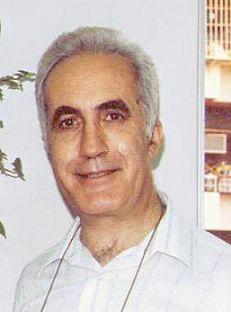
梁德佳神父
領洗的喜樂,陪著我經驗到最輕鬆的一次年度技術評鑑,用心準備,卻不擔心成果。而在一次基督生活團的避靜中,我正視自己想離開卻離不開樂團的問題。終於 ,毫無戀棧地遞出辭呈,結束七年半的演奏生涯!一位比我勝任有餘學生輩的兼任團員因而有機會考上專任團員。到底,避靜中我得到什麼光照呢?
「人受造的目的,是為讚美、欽崇、事奉我們的主天主,由此妥救自己的靈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為人而造的,為助他達到他受造的目的。
由此可見,取用世物,常該看自己受造的目的;它們能幫助多少,便取用多少;能妨礙多少,便放棄多少。 …」
這樣的喜樂,在基督生活團日給景耀山神父一個特殊的印象,他多方打聽找我,邀請我去新竹社會服務中心跟青年分享「喜樂的生命」。 也是因為我給他的喜樂印象深刻,於是在我初學第二年時,跟我談他的計劃,景神父是仁愛啟智中心的董事長,他希望中心工作人員中有個喜樂的人 ,但是我可以做什麼呢?音樂老師!特殊教育的音樂老師,他為我開啟了一個新路!當時國內並沒有音樂治療系所,就憑著一通長途電話跟台灣音樂治療先驅張初穗老師請教,之後,開始從做中學習的音樂治療的服務,直到現在,近幾年由弱智者或多重障礙小孩的年齡層轉換到高齡者。

初學第二年去仁愛啟智中心體驗
一路走來,我領悟到音樂是方法,而人是主體,按個別差異,找方法使每個人得以發展。他們對自己有信心,也就願意再學習別的技能、能生活自理,減少依賴。而八九十歲失智的老人們自覺在他們喜歡的事情上還能有所為,對週遭事務感興趣。建立一個信任的關係是很重要的,用心在每個人身上,看到他們的改變真是非常美的事。音樂的路很寬廣!
自己奉獻生活中特別難忘的經驗?
在初期培育過程中,在團體裡,我是個異類,我是感覺型的人,講感受。另一個一起初學的同伴,我忘了使她發火的原因,平常她是沒什麼脾氣的人,氣著說:「感覺感覺,沒人像妳這樣,妳太不一樣了。沒有人可以接受妳這樣的人。」這讓我很震驚,自問真的是這樣嗎?不敢確定自己在團體的存在有何意義。然而,有一次在泰山團體時,週四守聖時團體公拜聖體,排禮儀的姐妹選擇用泰澤短誦貫穿,團體姐妹唱同一個旋律、一位姐妹彈吉他、一位姐妹吹直笛、我拉大提琴,四個旋律線,卻是和諧的,很美!當下,我仿佛得到一種肯定:自己的獨特對團體是一個貢獻。若都一樣就很單調了 !當然要學習去了解別人,接納自己、接納別人,而這是一輩子的事,不是一次就結束了。絕對化的殺傷力很可怕,我承認自己將感覺與感受看得過分重要,而引起那位姐妹的強烈反應。
友愛團體生活是最大的見證,不是沒有衝突、表面和諧,而是事後可以和好、可以為了團體、為了更大的目標合作。這是一個不斷死於自我的過程,為了天國的拓展,我們的關係要建立在耶穌基督身上,不然,來自不同家庭、不同的背景怎能生活在一起,一起分享、分擔?團體生活不是夢幻。我們在太原致命的七位姐妹是最具體的活見證,她們活出友愛團體的極致:交出自己的生命,是福傳使命的成果。有為者亦若是!




 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