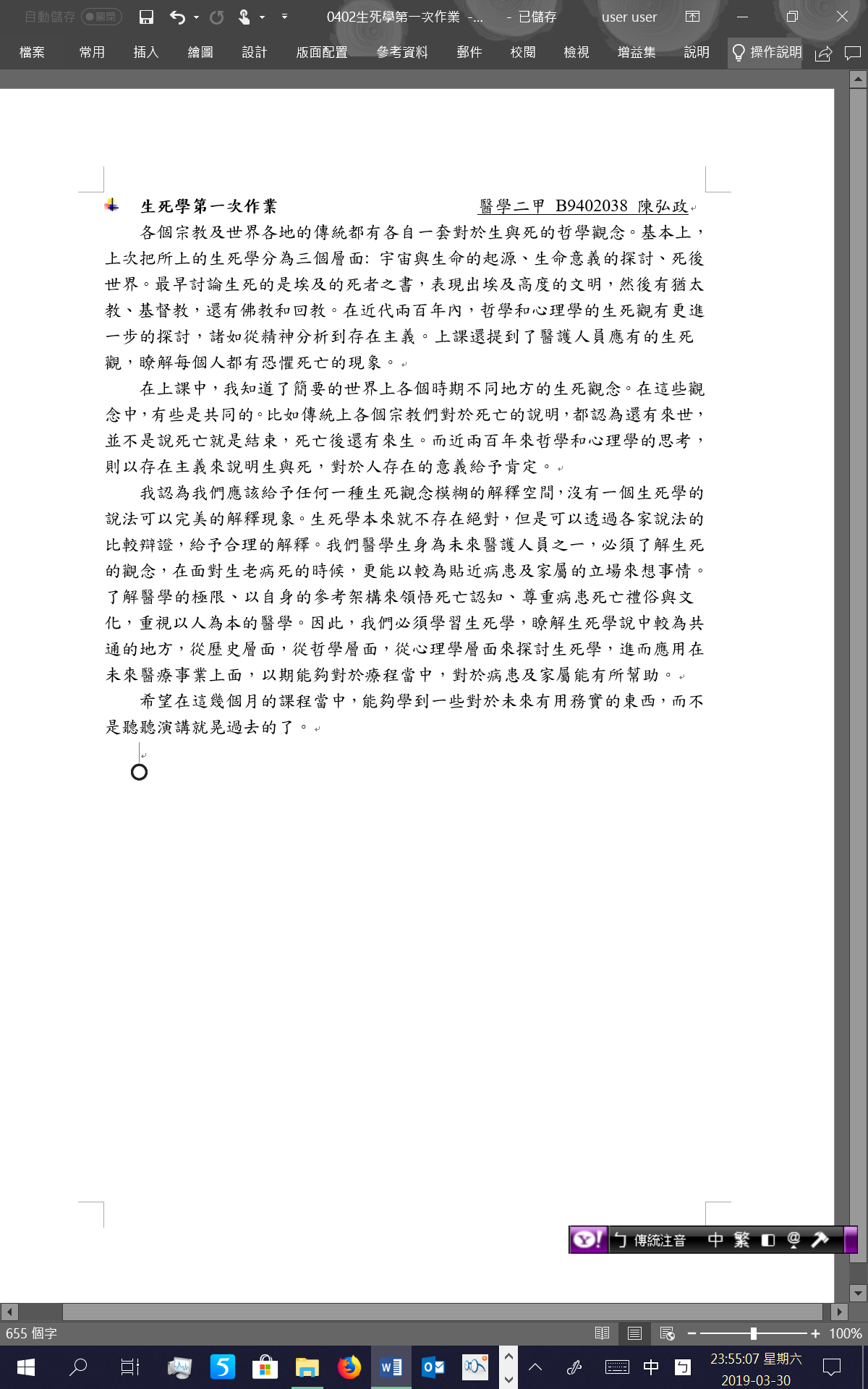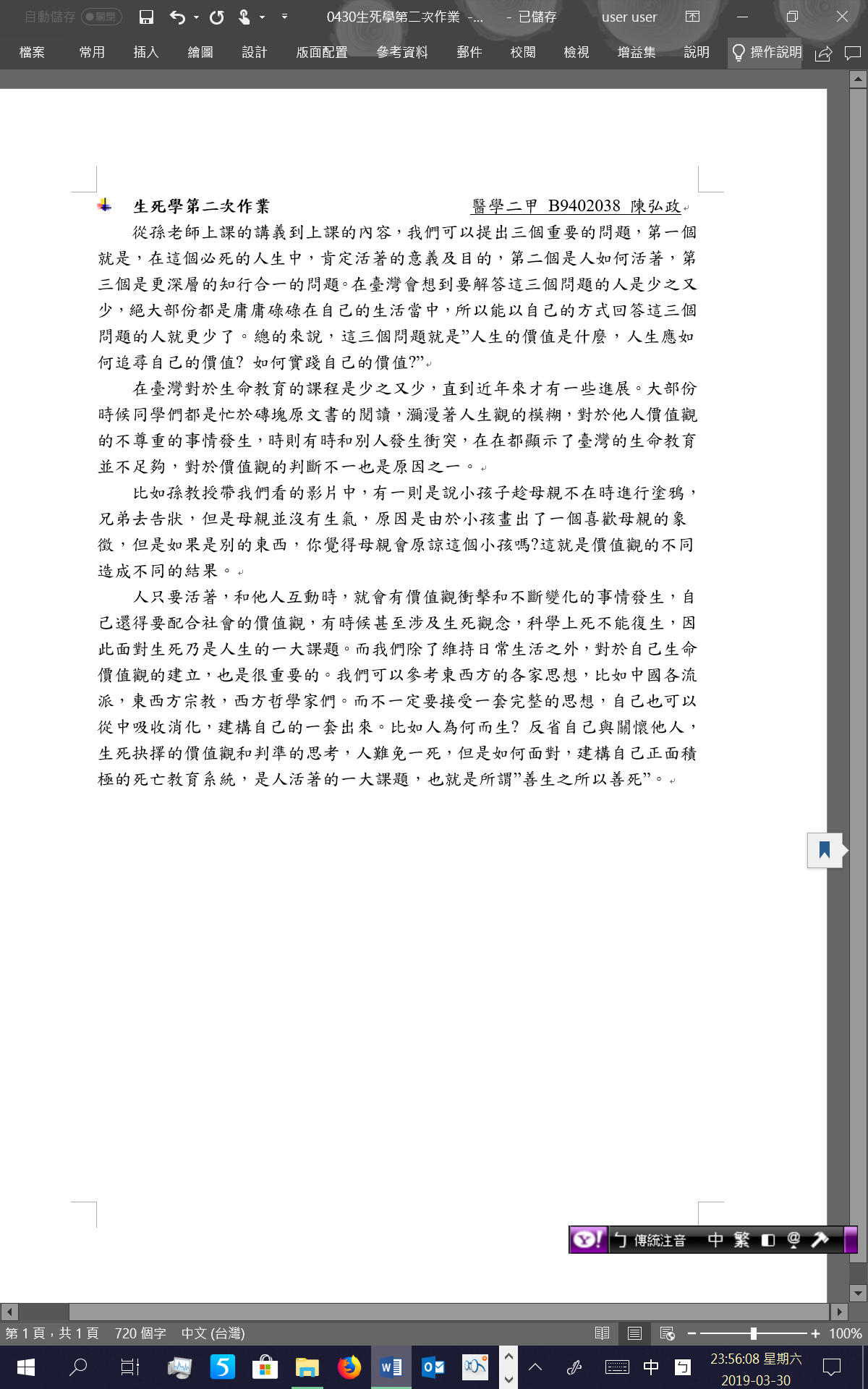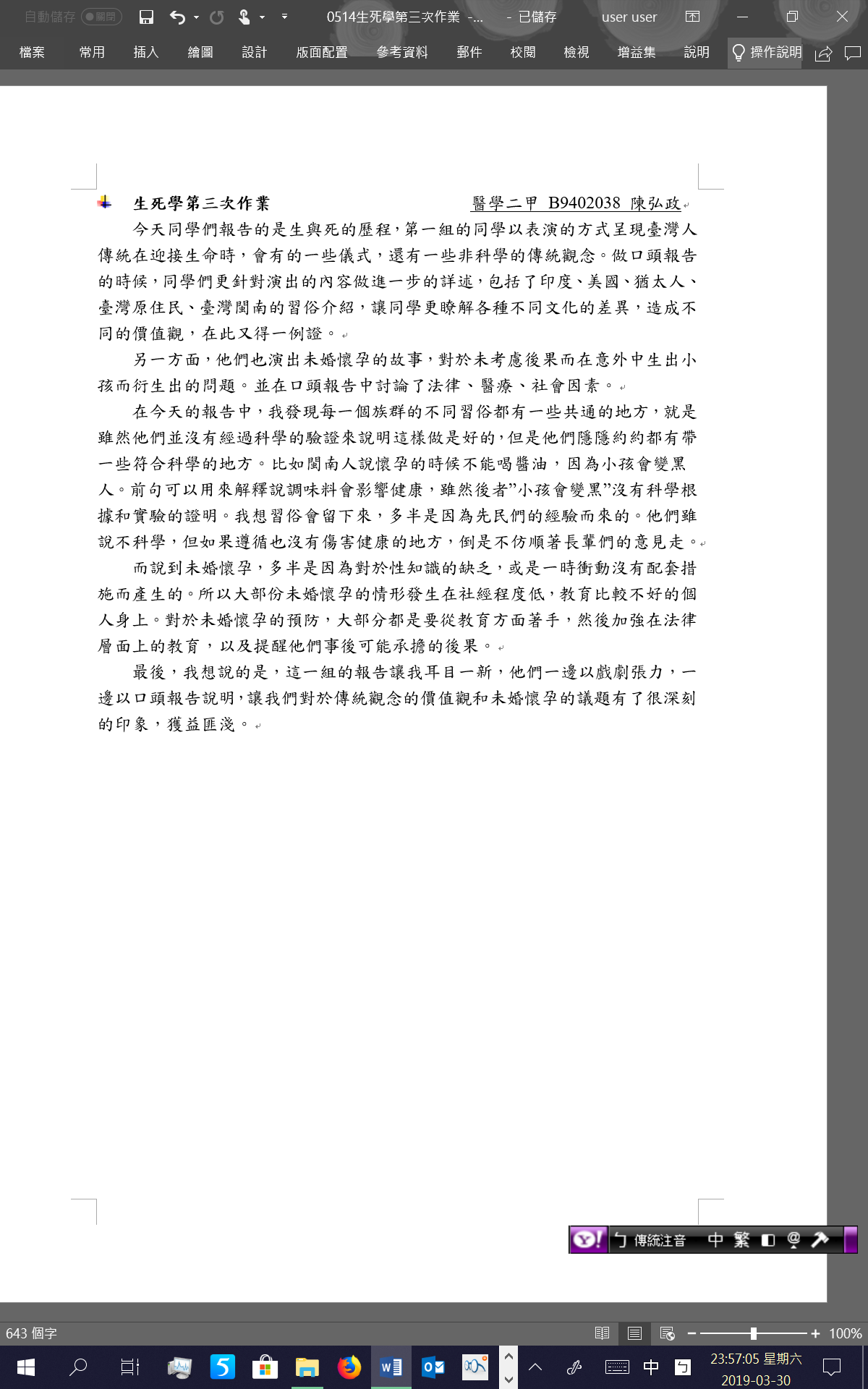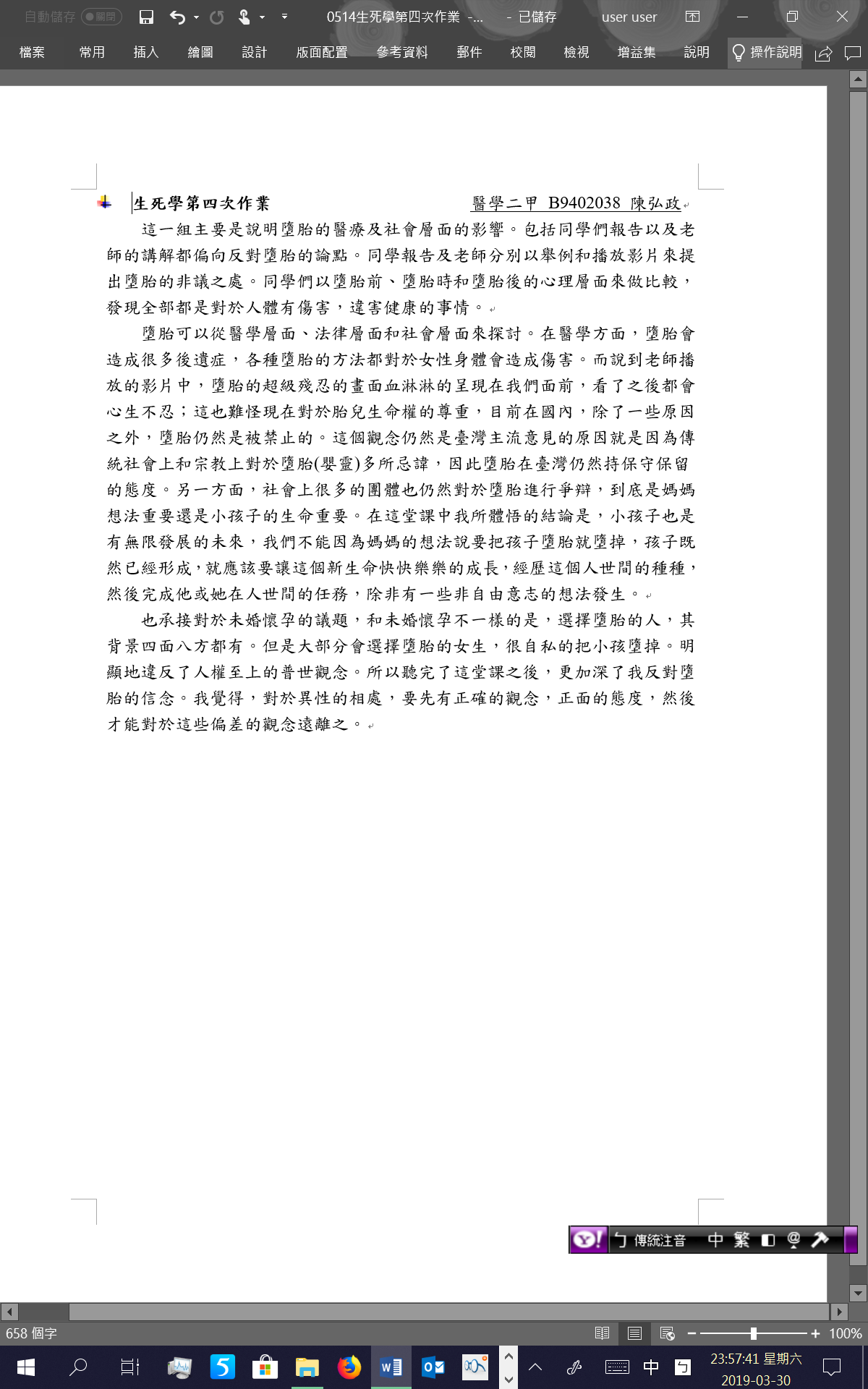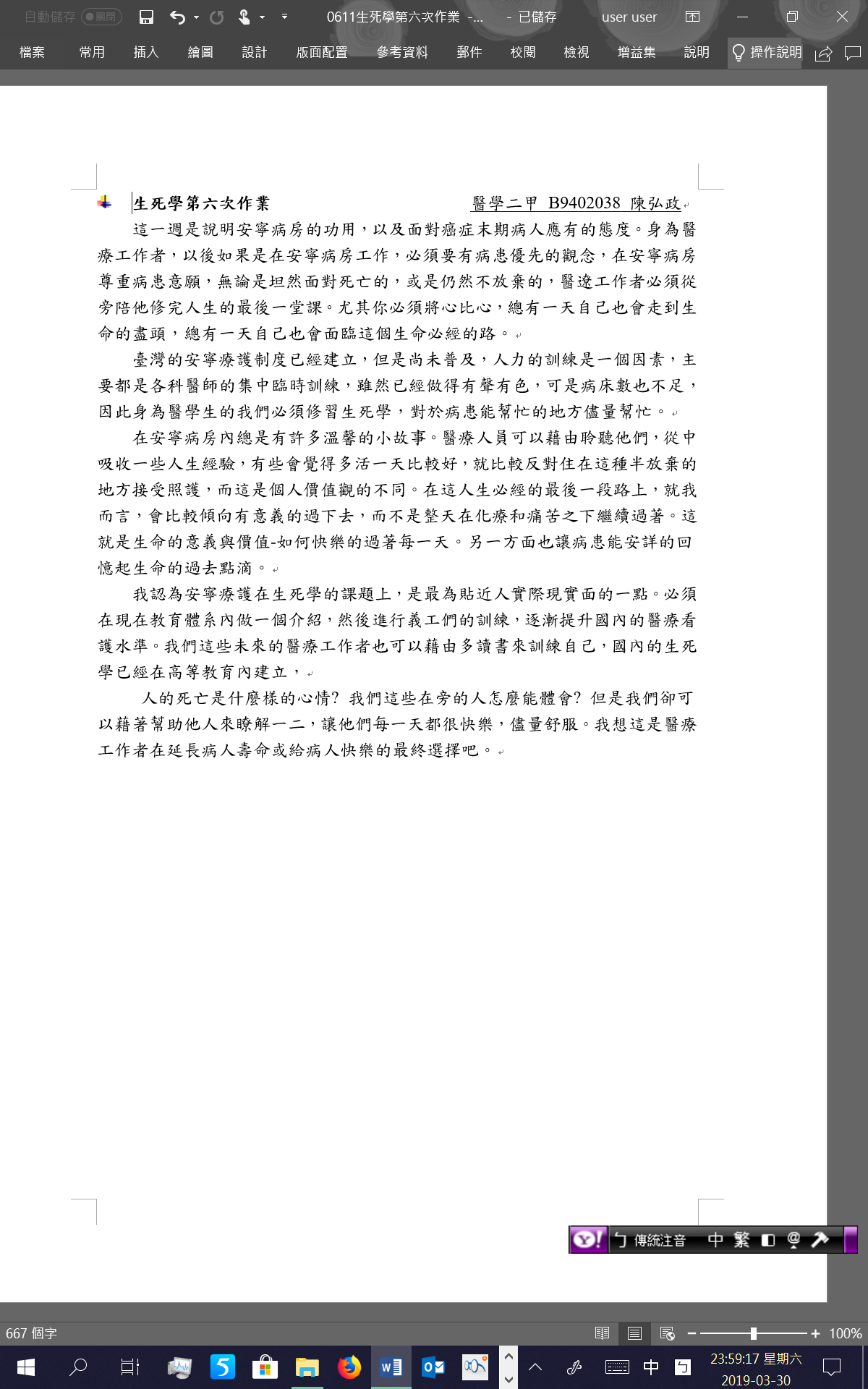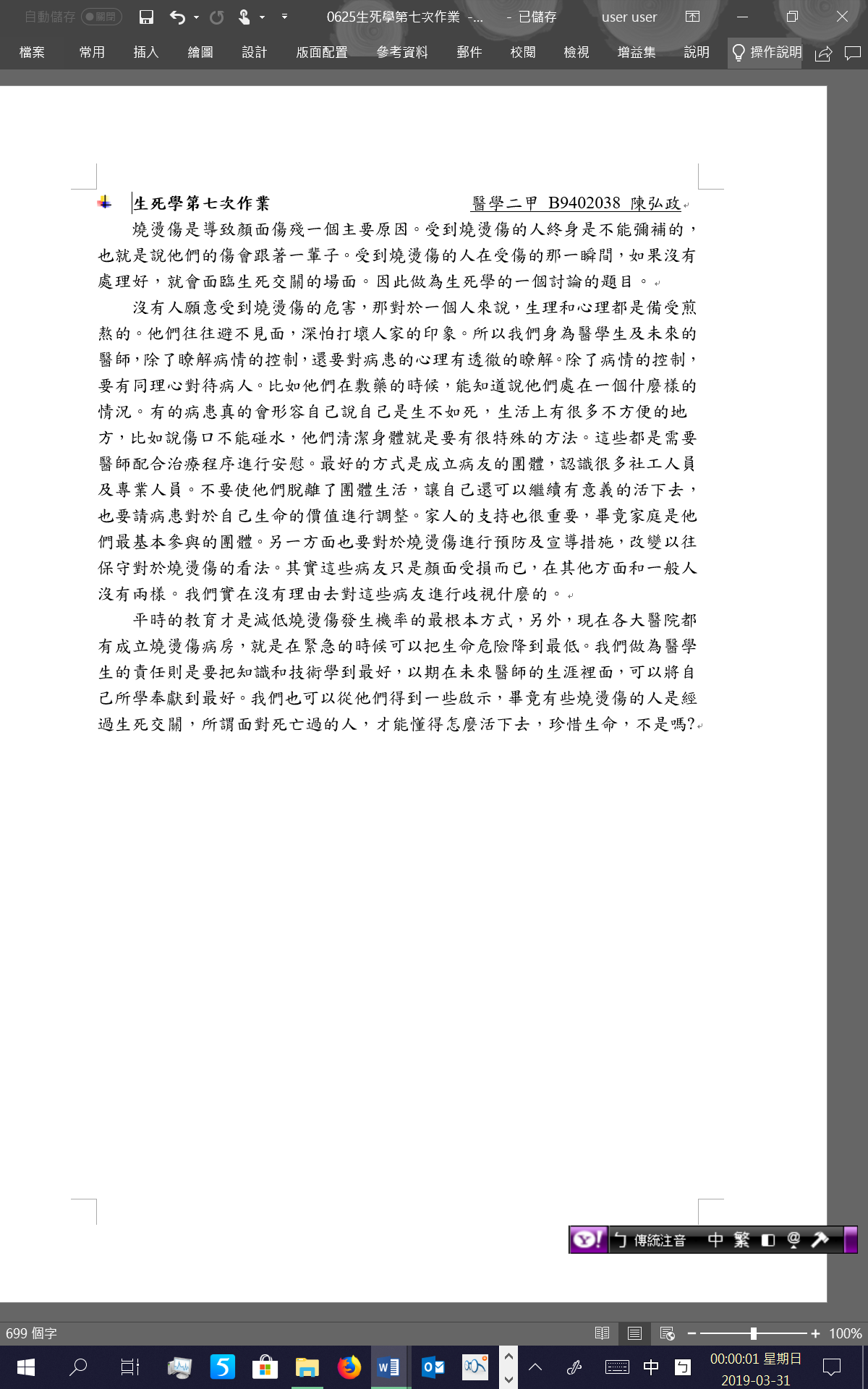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9/03/31 01:00:36瀏覽537|回應0|推薦0 | ||||||||||||||||||||||||||||||||||||||||
生死學是一個很奇怪,但是很新奇的一門課程。根據精神醫學的研究,及醫師的心理建設而言,需要多方面了解探討案例。一開始筆者很幸運,爭取到五位好書分享討論的名額,回憶起在新北市新莊國中的文藝社,曾經陪現在於台灣中小學界很有名的許信中老師討論一本「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這個一年的社團是許老師當實習老師時開的,他大學工讀時的搭檔就是很有名的東森氣象主播王淑麗,是透過筆者同社團的同學,所認識的筆者小時候補習班凱琳美語的溫淑梅老師牽過去,後來在東森電視很穩定上班至今。真巧在2014年後他們算在筆者舅舅家及苗栗那兒上班,那他們是把筆者當數鈔機嗎? 這裡貼出生死學的七次報告,個人的上台solo是另成一篇於13-2
附上第二次心得作業的原題,由當時知名王牌長庚醫院醫師孫孝治教授的論文「生死學0409孫孝治教授-生命教育與大學生通識人文素養」。這淺顯易懂而值得分享推廣,雖然這些好像與筆者沒什麼用途...(投影片因版權問題在此不附上省略) 生命教育與大學生通識人文素養
人生三問 任何一個人,不論是誰,也不論他在社會上扮演什麼角色,更不論他是富貴貧窮或疾病健康,都必需面對自己生命的三個基本問題:我為什麼活著?我該怎樣活著?我又如何能活出該活出的生命?第一個問題不簡單,古往今來很多有智慧的人都給過答案,所有宗教更是無一不致力於這個問題的解答。不過,生命的答案,終究必須自己去尋求。由外而內的答案如果不能得到由內而外的相應,那麼,答案即使是正確的,恐怕也只會擦身而過,與我們無關。第一個問題是人生最根本的問題。人偶然有了生命,卻必然邁向死亡,如何在這必死的人生中,肯定活著的意義與目的,實乃人生大哉一問。此問如果找不到答案,或者,如果一個人認為它根本沒有答案,那麼,後面兩個問題也就很難提出,更遑論答覆了。
如果一個人在第一個問題上能突破成住壞空的無常,能不陷溺於虛無主義或享樂主義的羅網中,那麼,他必然會關切第二與第三個問題。第二個問題也就是人該怎樣活著的問題。這不只是一個道德或倫理的問題,或者,更確切的說,道德或倫理的問題從來就不只是形而下的實踐問題,而更是與第一個問題相銜接的終極課題。如果生命有一個終極目標,哪條道路會通向它呢?哪條路又是所謂的「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的大學之道呢?
現代人的存在處境不是「複雜」兩字所能道盡。在這複雜中,我們常常不清楚方向,也不知道何去何從。要不要繼續一份友誼、一場戀情或一個婚姻?在鼓勵情慾解放的時代裡,又該如何看待劈腿與外遇?在後現代的今天,當結婚誓詞從「終身不渝」的盟約轉變為「當感覺還在時,我保證愛你」的契約,忠誠還有什麼意義?澳洲男老師嫖妓嫖到女老師,男老師沒事,女老師遭教育局處分。其後教育局則遭指控兩項罪名:性別歧視以及違反老師下班後之性工作權。究竟老師有無性工作權?性交易若有問題,何以僅單方面受罰?在人我的給與受之間又該維持怎樣的平衡呢?該如何面對立場各異、背景不同的人?該如何寬恕?無意的傷害也許容易原諒,但刻意的呢?而什麼又是刻意的傷害?可惡之人必有可憐之處,但在可惡與可憐之間,我該如何拿捏?在仁慈與正義之間我又該如何平衡?最後,關於生死也有很多難解的習題,例如:如果不能為了醫學發展的理由而殺死一個健康的嬰兒,何以可以拿人類胚胎來作實驗?受精卵、胚胎、胎兒、嬰兒這條連續發展的過程中,究竟有什麼重大的差異可以證成差別待遇?此外,面對「點燃生命之海」中那位受傷而全身癱瘓二十八年的西班牙人要求自殺協助時,我們該站在哪個位置上?Pro life或Pro choice?可不可以如他所要求的,提供他自殺的協助或助其安樂死?在極大而無希望的痛苦中,如何要求或邀請人貫徹活著的勇氣?總之,明辨善惡說來很輕鬆,但在不足外人道的人生點滴中知善知惡,實在不是容易的功課,這是人生第二個大哉問。
第一個問題與第二個問題都是「知」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有關人生目標與意義的「知」,第二個問題是有關人生實踐之道的「知」。不過,人生問題除了「知」之外,還有「行」的問題。一個人即使知道人生有值得追尋的目標,也知道通往目標的道路何在,但卻沒有力氣上路,或偏偏往相反的方向跑去,那麼,這所有的「知」都是枉然。人生誠然有很多事情是知難行易的,但也有更多是知易行難或知不易行更難的。如何調和知行,使其合而為一,是每個人必須提出並解決的第三個問題。人為什麼會知一套、作一套?又為什麼「言其所信,行其所言」是那麼不容易達到的境界?這就涉及到知情意行是否統整(integrity)的問題。身心靈統整的人才能夠「誠於中,形於外」,活出應該活出的生命。
分開來看,上述人生三問各有其獨立之旨趣,不過,合起來看,它們之間是相互為用的。知之愈深,行之愈篤;行之愈篤,知之愈深。真知與力行之間具有一種良性循環,使得越明白的,越能去力行;而越能去力行的,也越能有真切的明白。這正是佛教說「悲智雙運」的精義。
生命三學 長久以來,我國教育偏重工具理性,忽略目的理性,致使更為根本的生命課題受到忽略,而教育的目標則本末倒置。上述人生三問正是最受到忽略的生命課題。忽略的結果是:社會上瀰漫著人生觀模糊、意義感空洞、價值觀混亂與人格不統整的情形,並由之衍生出種種輕賤個人生命、傷害他人生命;只有利益,沒有公義的現象。依此,如何針對深層的生命課題,進行生命教育,實屬刻不容緩之工作。
生命教育者,一言以蔽之,即探究生命中最核心議題並引領學生邁向知行合一的教育。與「人生三問」相映照是「生命三學」。依此,生命教育應包含三項環環相扣的目標:
一、引領學生進行終極課題與終極實踐的省思,以建構深刻的人生觀、宗教觀與生死觀。 二、培養學生道德思考能力,並學習「態度必須公正,立場不必中立」的精神,來反省生命中的重大倫理議題。 三、內化學生的人生觀與倫理價值觀,以統整其知情意行,提昇其生命境界。
從學理言,此三項目標包含三個各自獨立但卻彼此交互為用的議題領域,它們分別是:(一)終極關懷與實踐、(二)倫理思考與反省、(三)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以下將先說明它們各自之內涵,再說明它們彼此相輔相成的關係。
(一)終極關懷與實踐,涉及的是人生最終極的課題,這包含了必死的人生究竟有何意義、又如何去開創其意義的人生哲學問題,也包含了有關死亡的省思與實踐的各種死亡教育課題,還包含了有關超越界與聖界信仰的宗教教育課題。
1) 生命意義的肯定與開創可以說是一切意義與價值肯定的基礎。人生不是只有飲食、男女與理財,更不是只有統獨、藍綠與經濟等議題值得關懷。人作為萬物之靈、作為神學家如拉內(Karl Rahner)口中所謂的「發問的存在」(ein fragendes Dasein),本質上就不只是追求實用功利的經濟動物而已,而還要探求意義與理想,並以之作為人生的出發點與歸依。人對自己及周圍的一切發出疑問並渴望答案。從某種角度講,宇宙人生確實很像羅素所感覺到的,似乎只是一團無明之氣,在複雜的機械因果中偶然聚散。果如此,一切是非分別、愛恨情仇、高峰低潮、乃至國家興亡、文明發展,都顯得貌似煞有介事,其實只是虛中之虛,幻中之幻。[1]由此可知,攸關意義探索與安頓的人生哲學課題何其重要。人如果不能肯定生命整體為有意義,便很難從生命的終極空洞中攫取實踐道德與向上提昇的動力。事實上,生命如果是沒有意義的,也無所謂那個方向是向上或向下了,一切最終歸於寂滅,如聖經訓道書之所言:「萬事皆虛,虛而又虛」(訓 1, 2);亦如金剛經所謂:「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不過,很遺憾的,在日常生活的具體實在中,人們很容易以具體為實在,而不容易察覺萬事皆虛的事實。也或者,即使察覺了,卻仍讓自己麻痺於開門七件事與電視報紙的實在感受中,免得整個人被虛無的陰影所侵蝕。於是乎,人生哲學問題顯得與庸庸碌碌的現實生活格格不入。反倒是「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飲食男女與功名利祿很容易盤據人們的心靈。人忽略死亡,忽略人是向死之存在的事實。
2) 人為何會忽略死亡?原因恐怕無他,而正是因為死亡是人所最不願意面對的事實。由於難以面對,因此人傾向於遺忘死亡。然而,遺忘生死是一切顛倒見的根源,它使個人的人生顛倒,也使整個人類文明陷於自我毀滅的惡性循環中。
首先,遺忘生死使人陷溺於無明的忙碌中,捨本逐末,忽略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物。索甲仁波切這樣描述大部分人的生活:
「我們大多數人都是這麼醉生夢死的,依循既有的模式活著:年輕時候接受教育,然後找個工作,結婚生子;我們買個房子,在事業上力爭上游,夢想有個鄉間別墅或第二部車子。假日我們和朋友出遊,然後,我們準備退休。有些人所面臨的最大煩惱,居然是下次去哪裡度假。 … 整個生活步調如此緊張,完全沒有時間想到死亡。為了擁有更多的財富,我們拼命追求享受,最後淪為它的奴隸,只為掩飾我們對於無常的恐懼」。[2]
本末倒置的人既然只顧著追求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事物,如飲食男女、功名利祿等,因此很容易會遺忘了愛。亞當傑克遜在「人生的四大秘密」中說道:
「在我們的心靈深處,每個人需要愛的程度比其他任何事都來的多,只是我們都忘了。我們汲汲於追求其他的目標,譬如事業、金錢和財富,我們專注地追逐休閒、娛樂,而忘記了生命中更重要的事」(二一頁)。
從巨觀的角度來看,整個社會遺忘生死的後果更為可怕。在這樣的社會中,教育體系不再提供真正的「生命教育」,頂多只是進行技術性的知識傳授而已。至於做人處事的道理固然也在社會教化或維護安定的功能意義下進行,然而,由於碰觸不到生命的深處,很難對人產生深度的影響。「年輕人接受各種各樣的教育,卻對於瞭解生命整體意義,以及與生存息息相關的主題,茫然無知,有哪件事比這個還要諷刺」與顛倒呢?不唯如此,遺忘生死的社會必然淺薄近利。當大多數人都習於今朝有酒今朝醉時,他們必定「肆無忌憚地為著自己眼前的利益而掠奪地球」(西藏生死書, 二一至二二頁)。
此外,在遺忘死亡的社會中,死亡很容易成為禁忌。人們對死亡的過程與處理避之唯恐不及,因此死亡變得愈來愈非人性化與機械化。著名的死亡學專家庫布樂‧羅斯(Elizabeth Kübler-Ross)便指出:
「今天的死亡過程在許多方面都變得更為可怕而令人厭惡,也就是說,更為孤單、機械化以及非人化。 … 死亡過程變得孤離而又無人情味,乃是由於絕症患者被迫從自己熟悉的環境運出,而匆匆忙忙送到急診所的緣故」。[3]
對於這一點,索甲仁波切感嘆地說:
「我們的社會只迷戀年輕、性和權力,卻逃避老年和病衰。當老年人完成了他們一生的工作而不再有用時,我們加以遺棄,這不是很可怕的事嗎?我們把他們丟進老人院,讓他們孤苦無依地死去,這不是很令人困惑的事嗎?」(西藏生死書, 二三頁)
遺忘死亡的社會就是如此,人們既只顧著自己生活,忌諱死亡,也就會躲避一切與死亡相關的人事物。然而,人人皆有死,這也就意味著,當人被死亡的陰影籠罩時,他也同時必須面臨被社會遺棄的命運。這樣的社會容或是年輕有活力者的天堂(事實恐怕也不盡然),但必定是老弱邊緣者的地獄。
從這個角度來看,死亡教育有如當頭棒喝,提醒在濁世中翻滾的人們:你可以忘記死亡,死亡卻不會忘記你;更提醒人們,「賺得全世界卻失去自己的靈魂,並沒有什麼好處。」「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裡的主人翁墨瑞若不是因為突然身處絕境,怎麼可能從「publish or perish」的絕對信念中醒覺起來,而察覺到過往對於學術成就或社會地位的追逐顯得荒謬虛幻?依此,死亡的必然固然讓人渾身不自在或情何以堪,但正視死亡卻是追求人生真理的重要契機與開端。不碰觸死亡經驗或忽略死亡的教育無法開展出真正深刻的人生哲學教育。
3) 不過,面對死亡果真就能超越生死嗎?追尋意義果真就能找到或安頓意義?這樣的問題大概已涉入宗教領域,因此是更為根本的人生課題。一般而言,人認識世界的主要工具是理性與經驗。不過,理性與經驗很難以超越現實人生的方式來觀照生命與世界的奧秘。從某種角度講,純粹依靠理性與經驗的死亡面對或意義探索恐怕若不是徒然無功,便至少是無法窺其全貌的。哈伯瑪斯便坦言:「哲學不能取代宗教的安慰」。[4] 這就涉及到了人認識世界的另一重要方式 — 宗教信仰。世界各大宗教都提供有關存在終極實相的智慧或啟示,更提供人如何提升靈性、邁向聖境的超升途徑。如何在多元宗教的世界中欣賞不同宗教的傳統,並為自己找尋一條適合自己身心靈開展的朝聖路途,毋寧是每一個人最為重要的終極課題,亦是宗教教育所最關心的課題。
(二)倫理思考與反省能力的培養:終極課題的安頓旨在確立人生整體的意義與方向,然而,人生不是只有生死意義與宗教信仰等終極課題而已。在生死兩點之間,人有具體的生活要過,更有具體的「有所為或有所不為」要省思與實踐。談到省思就涉入了倫理學或道德哲學的範疇。倫理學首重思考與反省。依此,嚴謹而系統的倫理思考訓練是倫理教育或道德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但正是這一環是我國學校教育向來所最忽略者。影響所及,不僅學生的道德教育停留在膚淺表面或洗腦灌輸的層次,就連師資之培育過程也缺乏基本的倫理學訓練,致使老師們在面對學生論及道德議題時,往往除了單向「說教」外,很難真正的「說理」,並進行有品質的雙向討論。而欠缺說理的倫理教育是很難成功的,因為它無法讓學生從自己內在的思考來領會與認同重要的倫理價值。事實上,在價值愈來愈多元的今日社會中,思考與反省的重要性愈來愈明顯。誠然,人們應該包容「多元」、擁抱「自主」。然而,「多元」很可能只是是非混淆的一種說詞,而「自主」也能夠是「只要我喜歡,沒有什麼不可以」的藉口。倫理思考與反省的目的在於探索道德的本質、判斷各種實踐的倫理意涵,使人在多元主義的洪流中能夠不陷溺於相對主義的困境中,並且能不僅知其然,且能知其所以然地掌握道德判斷的方法以及建構道德原則的思維途徑。
倫理思考的意義還可以用古人所說的「慎思明辨」與「擇善固執」來說明。「固執」是道德堅持與實踐的功夫,它必須以「擇善」為前提,否則就會成為「頑固」,也就是堅持了「吃人禮教」而不自覺。而「擇善」則以是非善惡的分辨為前提,也就是所謂的「慎思明辨」。不先慎思明辨,無從擇善固執。以現代語言來說,倫理思考的訓練若能以深刻細膩的生命經驗為基礎,又能具有倫理學的系統性與嚴謹度,大概就離「慎思明辨」不遠了。
倫理學(ethics)亦稱道德哲學(moral philosophy),關心人應該如何生活,探索「善是什麼」以及「如何擇善」等課題。簡單地說,「善是什麼」屬於基本倫理學(foundational moral philosophy)關心的對象,而「如何擇善」則是應用倫理學(applied ethics)的問題。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後者是前者的運用,兩者互為體用。[5]
基本倫理學希望透過理性思維與人性經驗來探索善惡的意義與特性,建構進行道德判斷及證成道德原則的方法理論。它的對象並非具體的「如何擇善」的問題,而是解決這類具體問題所必須具備的思想架構。舉例來說,在探討「可否說善意的謊言」、「可不可以有婚前性行為」、「可否借人執照,抽取佣金」等具體倫理問題之前,必須先探討「為何可以或不可以」這個問題;而要掌握「為何可以或不可以」,則必須先探討善惡是非等概念的意義。應用倫理學是基本倫理學在各個實踐領域的具體應用。個別的應用倫理學(例如醫學倫理)關心的是在特定實踐領域中如何建構一套完整的道德規範(例如完整的醫學倫理規範),以及在面對具體的道德困境時,如何進行道德判斷(例如分娩中若母子不能同時存活時該怎麼辦?)等課題。道德規範的建構一方面應紹承傳統的價值觀,另一方面也必須就不合時宜的傳統思想進行解構與重構的工作,更應該就傳統思想所不曾思考過的新興議題(例如代理孕母或複製人)提出即時的反省,來幫助人們在現代社會中知所抉擇,尊重人我的生命,並活出人性的光輝。
(三)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終極課題的探索與倫理議題的思考是「知性」面的生命教育。但生命教育不能只停留在「知」的層次,而必須融貫到人的身心靈與知情意行各層面,這就涉及到生命教育的第三個主軸,也就是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的課題。事實上,無論終極課題或倫理議題都不只是知識的問題,而更是實踐的問題。「實踐」面若要將生命知識內化為生命智慧,並將知情意行整合起來,使人達到「誠於中、形於外」的境界,就必須致力於人格的統整與靈性的發展。
什麼是人格統整可以由其反面,也就是人格不統整的諸多形式來理解,例如知行不一、心口不一、理性與情緒的對立、理性與情慾的緊張、自身價值觀的衝突與身心靈的不和諧等。具體來說則例如:明明知道多找的錢應該退還卻讓貪心蒙蔽而沒有退還;明明知道不該亂發脾氣,但當別人惹我時,卻還是控制不住;又或者明明已經結了婚,但面對吸引人的公司同事,卻仍然情不自禁想發展一段不該發展的關係等。人常常就是這樣,知道是一回事,做不做的到卻是另一回事。這就是「知行不一」或人格不統整(integrity)的問題。「知行不一」是最重要而困難的道德課題,也是任何道德教育所不能不面對的嚴肅問題。規避這個問題,道德教育將只剩下道德知識的灌輸,而與道德教育的真正目標背道而馳。
人格統整首要是指身心靈的統整,以及由之而來的知情意行的統整。孔子所說的「從心所欲不逾矩」正是一種知行高度合一或人格高度統整的境界。要怎樣才能達到這個境界呢?首先必須徹底瞭解人格不統整的原因,然後才能正本清源,提升統整度與靈性境界。不統整的原因大概包含三方面,其一是人生觀與人生體驗的膚淺,導致正確的價值觀無法內化,因而無法形成「誠於中、形於外」的力量。例如:人們大多都聽過「吃虧就是佔便宜」這句話,而且也認同其中的道理,但人們還是喜歡佔小便宜,並且不喜歡吃虧。這是什麼原因呢?原來,一般人的認同只是一種表淺的肯定,而不是一種深層的信念。而這又是因為人在直覺上雖然隱約知道它的道理,但由於缺乏深刻的生命經驗去印證它的真切性,更缺乏深刻的人生觀去支持這個信念,因此很難將它真正內在化並在實踐上去貫徹它。
不統整的第二層原因在於知性與感性的分裂,這可以表現為情緒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低落;也可以是「利令智昏」或「色令智昏」的愚昧。人即使有正確的人生觀,也有正確的實踐原則,並不保證就能知行合一,因為情緒平穩時的「心嚮往之」不一定表示在情緒混亂時仍然能夠「從心所欲不逾矩」。知性與感性的統整包含的課題很多,而且都很重要,例如:憤怒情緒的處理、寬恕與道歉的學習、貪婪與吝嗇的化解、狹隘心胸的開擴、男女情欲與真愛的分辨等。在這些問題上如果不能致力於統整的修養,知行之間的分裂將持續腐蝕個人的人格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不統整的第三層原因是靈性層次的無明。由於人不只是一種身體性的存在,而更是一種既超越又內存於身體的靈性存在,因此,人的人格統整問題不能忽略靈性的幅度。靈性的「內存性」指的是那在身體內,但卻能自覺與覺他的神性我的存在,而靈性之「超越性」則表現為神性我不受身體之束縛、渴望真理、追求美善、虔敬神聖並嚮往永恆的無限向度。靈性的無明使人在自覺與覺他兩方面都混沌貧乏,因此容易陷溺在物質世界的虛幻中難以自拔。
東西方宗教與文化傳統均提供許多靈性發展與修行的途徑。從身心的層次來看,包含適當的飲食、運動、靜坐、默觀等,從神性層面來看則包含在日常生活中與聖界的相遇,以及分分秒秒涵泳於智慧、慈悲、寬恕、懺悔、感恩、信心、希望、委身等神聖的氛圍中。靈性發展成就人格之內在和諧與統整,而人格統整則連結知與行,使人的終極關懷與倫理反省得以內化並外顯為真誠的實踐。
**********************
生命教育所包含的三個領域 — 終極關懷與實踐、倫理思考與反省、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 — 是相互關連的,而且必須統合觀之才構成完整的生命教育。蓋生命教育以知行合一為目標,而知行之間具相互為用性:深刻的力行能帶來深刻的真知,而深刻的真知又能推動人進一步身體力行。從第一個領域所涉及的終極課題來看,這是知行合一所不能或缺的深刻真知,涉及人生觀、生死觀及宗教觀等終極智慧的涵養。終極智慧賦予人生意義與目的,並提供人生實踐的終極基礎。欠缺這個基礎,道德實踐的意義便很難確立。意義一旦確立,人必須進一步透過慎思明辨來建構實踐的倫理價值體系。這就涉及了倫理思考與批判能力的養成。而終極智慧與倫理價值不能只停留在「 知」的層面,必須融貫到人的知情意行與身心靈各層面,這就構成了生命教育的第三個向度,也就是有關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的課題。人的人格愈統整、靈性愈清明,則對於生命的智慧就愈能有終極的了悟;而人生的終極智慧愈深刻,則愈能強化倫理思考與實踐的能力;倫理思考與實踐能力的提升復又增進人格之統整與靈性的發展。如此週而復始、綿綿不已,便形構生命教育向上超升的正向循環。
高中九五暫綱與生命教育 民國九十五年即將實施的高級中學新課程綱要(九五暫綱),將生命教育納為正式課程中選修課之家族成員。此舉不僅開創了我國教育史的新里程,即使從普世教育發展的現況來看,以如此宏觀細密的方式來完整化學校全人教育之內涵者,亦屬少見。本課程如果能夠落實,將在生命議題的探索及價值觀的內化上,大大匡正傳統課程之偏頗與不足。
高中生命教育類選修課之課程綱要架構係依循生命教育三大範疇(終極關懷與實踐、倫理思考與抉擇、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為原則,並在考量選修課之特殊性質與限制後,共規劃了八科各兩學分之課程。其中,「生命教育概論」是最基礎的入門課程,而「哲學與人生」、「宗教與人生」、「生死關懷」、「道德思考與抉擇」、「性愛與婚姻倫理」、「生命與科技倫理」及「人格與靈性發展」等則為七科進階課程。[6] 各科名稱及綱要召集人詳見下表:
其中,「生命教育概論」一科是生命教育的入門課程,內容涵蓋了七個進階課程中最基本而重要的議題,目的在於對生命教育整體提供一種梗概的導論,做為進階學習的基礎。
七科進階課程係按照生命教育規劃理念的三大範疇而建構者。「哲學與人生」、「宗教與人生」、「生死關懷」三科分別屬於人生哲學、生死學及宗教教育等終極課題與終極實踐的探討。至於「道德思考與抉擇」、「性愛與婚姻倫理」、「生命與科技倫理」則屬於倫理議題之思考與反省訓練。其中,「道德思考與抉擇」屬於後設倫理學與規範倫理學的範疇,目的在於探究道德的本質與道德規範的意涵,並引領學生學習道德判斷的方法。至於「性愛與婚姻倫理」、「生命與科技倫理」則是當代應用倫理課題中至為重要的兩個實踐領域。我國這些年來相當重視「性別教育」,不過,從教育部推動的性別教育內涵來看,大多只集中在兩性平等或平權的議題,而較忽略當代兩性議題在廣度與深度上的各種倫理意涵。是以「性愛與婚姻倫理」一科希望彌補兩性平等教育之不足,而引領學生在性愛與婚姻所涉及各層面的重要倫理問題上,有所探討與省思。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部分目前只規劃了「人格與靈性發展」一科,目的在於探究人格統整與靈性修養所涉及的各種議題,期能引領學生達到身心靈正向發展與知行合一的理想。
生命教育與大學通識課程 生命教育從九五年起即將成為高中正式課程。理論上,大學通識課程應在這個基礎上,深化生命教育的理論探索,並廣化生命教育的實踐體驗,俾使生命教育能獲得一貫化、全程化與完整化之落實。不過,從實務的觀點來看,要求高中在短期內普遍地給予學生完整的生命教育,大概是不可能的事。箇中原因很多:首先,九五暫綱所規劃的生命教育課程是選修課,在一般學校對於生命教育的認知仍然有限的情形下,升學主義的壓力很容易讓學校忽略這類與考大學無關的課程。[7] 當然,這種情形也不是一無是處的,它至少有一個重要的好處,那就是在選修的架構下,會開設生命教育課程的學校或老師大概都是出於理念的認同與教育的使命感,而不是由上而下一條鞭的強制作法,這使得生命教育的推動比較容易成功。不過,無論如何,高中生命教育還在篳路藍縷階段,大專生命教育的推動與銜接不必預設高中已有充分且適齡之相關課程。其次,全國三百多所高中目前只有約四十名取得合格證書的生命教育師資,這是新興課程必然會有的現象,因為九五暫綱之前的高中課程標準並無相關之課程,自然亦無相關師資之需求與制度設計。如今九五暫綱雖然已經實施,但相關之師資培育工作才剛剛上路,而且並非是大規模的進行,再加上生命教育師資的培育不是一蹴可幾的,因此,短期內高中全面實施生命教育選修課的可能性也還不大。[8] 總之,現階段大專生命教育課程之規劃可以就生命教育自身之體系如何完整構建來著手,而還不必預設進入大學之高中生已有充分之背景知識。
從本文所論述之生命教育架構來看,目前各大專院校的生命教育發展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現象:
1) 首先,院校本身有生命教育相關學理之系所或研究中心者,比較能在生命教育學術研究與通識推廣上有所著力。至於完全只有理工法商醫農之院校雖然可能更需要生命教育,但卻無相關之人力資源來進行生命教育之研究與推廣工作。
2) 其次,目前國內院校所謂生命教育相關系所多半都只涉及生命教育的部分向度,例如宗教系所提供宗教教育所需之宗教學內涵、生死系所提供生死學或生死教育之理論建構。就生命教育之完整發展言,亟需跨科際的整合,才能構建周延之學術研究與教育內涵,而滿足學生全人發展之所需。但跨科技的整合就涉及了人力與設備資源之擴充等攸關學校發展願景的課題。換言之,大專院校對於自身定位與方向的策略建構,應將生命教育納入省思,才可能談生命教育之跨科際整合與發展。
3) 另一個值得思考的現象是,目前在大專院校比較受到重視的生命教育課程似乎以專業倫理及生死學為主。這些課程的開設固然對於提升學生之生命智慧有所助益,但其問題則是容易失之片面,而不能提供全人宏觀之視野。先談前者。專業倫理(professional ethics)的開設大概是近幾年才逐漸蔚為風氣的事,例如醫護學院開設醫學倫理(medical ethics)、護理倫理(nursing ethics)或生命倫理(bioethics)等;商學院開設商業倫理(business ethics)或經濟倫理(economics ethics);而工學院則開設工程倫理(engineering ethics)等。這些倫理課程的開設固然根源於時代的迫切需求,並且對於提昇學生在專業領域的倫理認知,也確實有所助益。例如商業與經濟犯罪的頻仍,促使企業與商學院校都開始重視道德操守與誠信問題;醫病傳統的父權關係與各種醫療糾紛則促進了人們對於醫護倫理的重視;至於生物科技的發展與運用更引起人們有關生命是否受到操弄的憂慮,從而激發了生命倫理的探討。
然而,這些問題的解決是不能以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來進行的,而必須放在一個更宏觀的脈絡中來思維,但這正是問題所在。換言之,根本的問題是,開設專業倫理的學校多半都缺乏生命教育之整體思維,於是乎,專業倫理的開設不以基本倫理的素養為前提;而倫理課程之進行也沒有以終極課題之探索為基礎,並以人格靈性發展之課程來強化知行之統合。前者,也就是欠缺基本倫理學的結果是,學生往往在欠缺道德哲學素養的情形下,便進入個案導向的專業倫理探討中。這樣的學習固然仍能有某些成效(例如對個別的道德兩難實例獲得一種具體的認知),但卻掌握不到道德判斷的系統性思維方法。[9]至於後者的問題是說,欠缺生命教育整體思維的倫理課程忽略了「專業人」更根本的身份是「人」。換言之,專業人是否能持守專業倫理,關鍵並不只在於專業倫理知識的有無,而更在於專業人做為人是否能肯定生命的意義,並能在人格與靈性上有深刻而統整的智慧。黃崑巌教授常對醫學院的學生說:「before you become a doctor, you should first be a man」,真是誠哉斯言。生命教育要引領學生探究生命最核心的課題,目的正是要幫助學生成為知行合一的真人。一個人只有先真的是人,才能成為一個真的醫生。
4)生死學的課程能引導學生開啟生命的一扇新門,這點前文已多所肯定,此處不再贅言。一般人比較容易有的問題是,把生命教育化約為生死教育,再把自殺問題與生命教育連結,彷彿生命教育或生死教育就是處理自殺課題的自殺防治教育而已。[10] 實則,生命的範圍包含生死,但卻超越生死,故不能把生命教育化約為生死教育。而自殺問題固然是生命教育或生死教育所應當關切的課題,但也絕非是生命教育或生死教育所唯一關心的問題。事實上,即使自殺問題也絕不只是生死教育的問題而已。自殺就彷彿是生命冰山的一角,其背後包含的問題幾乎可以說是整個生命的課題。依此,只從生死教育的觀點大概不能掌握自殺課題的全貌。此外,生死學的課題也會涉及到一些攸關生死的倫理問題,例如安樂死。生死學若不與倫理學進行跨科際之整合,其面對生死抉擇之倫理問題變容易缺乏倫理思辨的精確與深度。
綜合以上各種觀察,大專院校之生命教育似宜進行更為通盤之思考與規劃。基本上,生命教育的目標與通識教育是若合符節的。若我國大專院校之通識課程能將上述生命教育的理念整合進來,必能在學生人生觀之深化、價值觀的內化,與知情意行的統整上,更幫助學生在身心靈的全人發展上邁步向前。以下,本文謹提出生命教育之通識課程芻議,期能拋磚引玉。
1)終極關懷與實踐領域:可開設「哲學與人生」、「宗教與人生」、「生死學概論」等課程,輔以「哲學概論」、「比較宗教學」、「臨終關懷與安寧照顧」等科目。
2)倫理思考與反省領域:應開設三種不同層次的倫理課程。第一層為基本倫理學與規範倫理學(fundamental and normative ethics),以做為其他一切倫理課程的前提,旨在奠定道德思維的方法論基礎。第二層次為攸關所有人實踐價值觀養成的一般「應用倫理學」,例如「性愛與婚姻倫理」、「生命倫理」等。第三層次則是所謂的專業倫理,旨在幫助專業人提昇專業領域的道德敏感度、強化其專業倫理判斷及規範建構的能力。
3)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領域:這個領域可以開設的課程很多,而且就其目標是要將知性之智慧連結到實踐之貫徹而言,也有給生命教育畫龍點睛之妙。宏觀式的相關課程例如「心理發展與人格統整」、「東方靈修理論」、「基督宗教靈修」等,個別之專題則例如「幸福與人格特質」、「情緒智商與壓力管理」、「悲傷輔導」、「心靈治癒與家族治療」等,這些課程之開設目標都是要從人格與心靈深處,幫助學生獲致內在之統整與靈性之提昇。
4)體驗與實踐學習領域:體驗與實踐可以帶給人很多深層的反省。近年來「服務學習」課程(service learning)的倡導是很好的例子。此外,「探索學習」之體驗與內省教育(Porject Adventure)以及「電影與人生」等課程,都很能幫助學生從具體的實踐與體驗中省思生命的課題。
有一位從集中營生還的猶太人吉諾特寫了一封給老師的信,本文要以這封信來總結我們的討論。信中所言,值得所有教育工作者深思:
「親愛的老師,我是集中營的倖存者,我看到了一般人未見之處,瓦斯房是由博學的工程師建造,兒童是由受過教育的醫生所毒死,嬰兒被訓練有素的護士謀殺,婦女和嬰孩被知識份子射殺、焚燒。所以,我懷疑教育。我的請求是,希望你們幫助學生做一個有人性的人,永遠不要讓你們的辛勞製造出博學的野獸、身懷絕技的精神病人或受過教育的怪人。讀寫算等學科只有用來把我們的孩子教得更有人性時,才顯得重要。」
依此,生命教育對於每個學生或每個人而言,都不是可有可無的。若學校能體認生命教育的重要,並能克服各種困難來實施它,實為學生之福,亦為社會整體之福。
參考文獻 索甲仁波切(1998),鄭振煌譯,《西藏生死書》,台北:張老師文化。
孫效智(2001),生命教育的內涵與實施,《哲學雜誌》第三十五期,頁 4-31。
孫效智(2002),與他者的關係 — 倫理學,文收:沈清松,《哲學概論》,台北:五南。
傅偉勳(1993),《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台北:正中書局。
Habermas, J. Zu Max Horkheimers Satz: Einen unbedingten Sinn zu retten ohne Gott, ist eitel. Texte und Kontexte. Frankfurt a.M.: Suhrkamp.
Russell, B. (1989). A Free Man’s Worship. In L. Pojman (Ed.), Ethical Theory: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pp. 528-32). Belmont: Wadsworth.
[1] 這正是羅素(B. Russell)在他的無神的科學宇宙觀中所揭示的無意義的生命圖像(image of meaningless life)。參閱:B. Russell, “A Free Man’s Worship,” in Ethical Theory: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ed. L. Pojman (Belmont: Wadsworth, 1989), 528-32. [4] 參閱:J. Habermas, “Zu Max Horkheimers Satz: Einen unbedingten Sinn zu retten ohne Gott, ist eitel,” Texte und Kontexte,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91), 125。 [6]八科綱要全文及相關網路資源,請參考生命教育全球資訊網(http://life.ascc.net)。 [7] 我曾經為文指出,高中生命教育課程之開設不但不會妨礙升學,恐怕至還能有提升學生升學成績的效果。這是因為即使從升學角度來看,高中學生只讀考試科目而忽略生命其他幅度,是否真有利於考試之成績,還屬未必可知。蓋生命課題受到壓抑或忽略的學生,如同腹背受敵般,極可能並不利於其讀書所需之專注與考試之準備。此外,由於生命課題無時無刻均需面對,而生命智慧亦需學而時習之才能精進發展,因此,高中生的生命教育應成為一種持續不輟的學習,理想的情形是每學期均能實施一科(或以上)的生命教育課程。尤應避免僅在高一或高二實施,而於高三停止施行之情形。蓋此情形正是一種結構性的反生命教育,它等於向學生宣示說:為了升學故,人格、人際與人生問題皆可拋。如此教育所培養出來的學生自然容易變得只有自我,沒有他人;只有利益,沒有公義;只有媚俗之追求,而無神聖之理想。
[8] 高中生命教育的師資培育,以現職高中教師接受第二專長之培訓與認證為最快速可行之方式。民國九十五年台灣生命教育學會與台大進修推廣部已合作培育出第一批生命教育第二專長師資。這一批學員皆為現職高中教師或校長,來自三十幾所高中,共七十七名。第二期師資培育亦已於二零零六年七月開始為期兩年的課程。相關資訊請參考生命教育全球資訊網(http://life.ascc.net)。
|
||||||||||||||||||||||||||||||||||||||||
| ( 心情隨筆|心情日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