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1/10/25 15:38:14瀏覽2998|回應68|推薦206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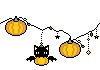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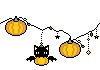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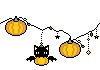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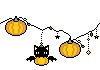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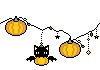  我仔細的想,可以確定在到紐約前從未聽過鬼節這三個字,自然無從知道鬼節是幾月幾日,是幹嘛的?但我永遠忘不掉我的第一個鬼節是如何開始,如何結束。 甚且在開始和結束的那個時段,我還不知道我身處於鬼節之中。這個鬼節一過竟然過了四個月。 我仔細的想,可以確定在到紐約前從未聽過鬼節這三個字,自然無從知道鬼節是幾月幾日,是幹嘛的?但我永遠忘不掉我的第一個鬼節是如何開始,如何結束。 甚且在開始和結束的那個時段,我還不知道我身處於鬼節之中。這個鬼節一過竟然過了四個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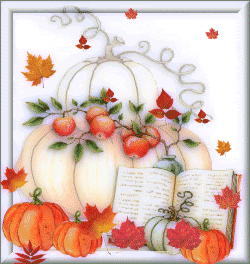 那年的暑假,剛大學畢業,拜別了爸媽,哥哥弟弟,和送行的男友,隻身飄洋過海負笈他鄉。拖著行李走入候機室時的那一刻,初次離家的我意識到我將獨自到一個陌生的國度,那兒再也沒有爸媽的護翼,那兒再也沒有人可以依賴, 那兒再也沒有人可以送我回家,那兒再也不是從前, 我悲傷的淚水如決堤般流下。我沉重的腳步只能向前。回首,家人,男友, 在淚眼婆娑中越來越模糊,越來越遙遠。 那年的暑假,剛大學畢業,拜別了爸媽,哥哥弟弟,和送行的男友,隻身飄洋過海負笈他鄉。拖著行李走入候機室時的那一刻,初次離家的我意識到我將獨自到一個陌生的國度,那兒再也沒有爸媽的護翼,那兒再也沒有人可以依賴, 那兒再也沒有人可以送我回家,那兒再也不是從前, 我悲傷的淚水如決堤般流下。我沉重的腳步只能向前。回首,家人,男友, 在淚眼婆娑中越來越模糊,越來越遙遠。 上了韓航就埋頭寫信,邊寫邊掉淚。就這樣在別愁離緒中,我到了賓州大姐姐處。 停留的幾週,受到姐和姐夫的熱情款待, 他們帶我在大學城附近四處遊玩,教我來美須知。接著在勞工節的長週末,姐和姐夫將我送去了我的學校。除了當初帶來的兩大行李, 一個拖包外,長姐如母,又給我買了一個睡袋,枕頭,檯燈,袖珍錄放音機和簡單的廚具,包括一個小電爐,一個平底鍋,一個小湯鍋,一個小菜板,一個削皮刀,等等。 上了韓航就埋頭寫信,邊寫邊掉淚。就這樣在別愁離緒中,我到了賓州大姐姐處。 停留的幾週,受到姐和姐夫的熱情款待, 他們帶我在大學城附近四處遊玩,教我來美須知。接著在勞工節的長週末,姐和姐夫將我送去了我的學校。除了當初帶來的兩大行李, 一個拖包外,長姐如母,又給我買了一個睡袋,枕頭,檯燈,袖珍錄放音機和簡單的廚具,包括一個小電爐,一個平底鍋,一個小湯鍋,一個小菜板,一個削皮刀,等等。 當車子出了荷蘭隧道後,映入眼簾的是滿地隨風飛舞的垃圾, 隨地亂滾的酒瓶。布魯克林的天空灰暗陰沉,兩旁不乏老舊的建築物,殘破的玻璃窗,破敗蕭瑟的景象和賓州州大的美麗校區有天壤之別。我心想這就是紐約嗎?姐姐姐夫當時也是阮囊羞澀的博士生,但仍然慷慨的帶我去中國城大啖一頓,買了叉燒烤鴨之類的外賣後,就將我送去了宿舍,他們就回轉賓州了。我四個月孤單,心驚膽顫的留學生涯於焉開始。 當車子出了荷蘭隧道後,映入眼簾的是滿地隨風飛舞的垃圾, 隨地亂滾的酒瓶。布魯克林的天空灰暗陰沉,兩旁不乏老舊的建築物,殘破的玻璃窗,破敗蕭瑟的景象和賓州州大的美麗校區有天壤之別。我心想這就是紐約嗎?姐姐姐夫當時也是阮囊羞澀的博士生,但仍然慷慨的帶我去中國城大啖一頓,買了叉燒烤鴨之類的外賣後,就將我送去了宿舍,他們就回轉賓州了。我四個月孤單,心驚膽顫的留學生涯於焉開始。 宿舍大樓 宿舍大樓 大姐走後,預訂的宿舍還在維修,無法住進,我只好先到一位和我在台灣素昧平生的同系學姐處打地舖。她對我很不友好,短短幾天,遭她很多白眼。後來,我想可能她沒有完成研究所學業,就棄學工作,年紀又大了些,同行相嫉吧。 雖然如此,這麼多年過了,我還是很感謝這位學姐收容我,讓我在她們油膩不堪的地毯上睡了幾晚。倒是她的香港室友對我很友善,讓我睡她屋裡的舊沙發,但我想還是睡客廳地上好了。這個嬌小的香港女孩,有著一頭長髮,小兒麻痺,需要穿鐵鞋,在中國城珠寶店打工,身上還別著槍,我暗暗的佩服她。人生地不熟,布魯克林治安又惡劣,本來就不喜出門,那時更是哪兒都不敢去了。每天24小時,外頭警車,救護車不時的呼嘯而過警笛聲直鑽耳門初來乍到舉目無親份外恐怖;醉漢怪人臭氣熏天,隨處可見。遊子思鄉夜夜不能成眠,只有獨自流淚。 大姐走後,預訂的宿舍還在維修,無法住進,我只好先到一位和我在台灣素昧平生的同系學姐處打地舖。她對我很不友好,短短幾天,遭她很多白眼。後來,我想可能她沒有完成研究所學業,就棄學工作,年紀又大了些,同行相嫉吧。 雖然如此,這麼多年過了,我還是很感謝這位學姐收容我,讓我在她們油膩不堪的地毯上睡了幾晚。倒是她的香港室友對我很友善,讓我睡她屋裡的舊沙發,但我想還是睡客廳地上好了。這個嬌小的香港女孩,有著一頭長髮,小兒麻痺,需要穿鐵鞋,在中國城珠寶店打工,身上還別著槍,我暗暗的佩服她。人生地不熟,布魯克林治安又惡劣,本來就不喜出門,那時更是哪兒都不敢去了。每天24小時,外頭警車,救護車不時的呼嘯而過警笛聲直鑽耳門初來乍到舉目無親份外恐怖;醉漢怪人臭氣熏天,隨處可見。遊子思鄉夜夜不能成眠,只有獨自流淚。   由於當年資訊的缺乏,完全不清楚我讀的研究所位於Brooklyn的黑人區,不在長島大學校總區 CW Post。為配合研究生都是帶職業進修,所有的課程都是在傍晚以後。全系外籍學生只有我和另外兩個日本男的,他們倆也是留職來美進修,所有同學都是30好幾的,只有我年紀最小且是全時學生。大家彼此之間來去匆匆並無互動。而且布魯克林校區沒有任何台灣留學生社團. 由於當年資訊的缺乏,完全不清楚我讀的研究所位於Brooklyn的黑人區,不在長島大學校總區 CW Post。為配合研究生都是帶職業進修,所有的課程都是在傍晚以後。全系外籍學生只有我和另外兩個日本男的,他們倆也是留職來美進修,所有同學都是30好幾的,只有我年紀最小且是全時學生。大家彼此之間來去匆匆並無互動。而且布魯克林校區沒有任何台灣留學生社團.  校總區  布魯克林校區   街景 街景 另外還有一個老生,曾明鴻,他住在我那學姐同一棟的公寓大樓裡。曾明鴻對我們很照顧,這四個月中唯一美好的回憶, 就是他開著他的老爺車帶我們四個老中去Atlantic City 和 Madison 花園廣場玩,這也是我在哪兒唯二的出遊。後來轉學離開時, 在雨中,曾明鴻幫我推兩箱笨重行李,將我送上灰狗巴士。曾明鴻僑居日本,為一熱血青年,空手道黑帶高手。為人正直,熱心,理想,MBA畢業後,自願申請回台服役。 另外還有一個老生,曾明鴻,他住在我那學姐同一棟的公寓大樓裡。曾明鴻對我們很照顧,這四個月中唯一美好的回憶, 就是他開著他的老爺車帶我們四個老中去Atlantic City 和 Madison 花園廣場玩,這也是我在哪兒唯二的出遊。後來轉學離開時, 在雨中,曾明鴻幫我推兩箱笨重行李,將我送上灰狗巴士。曾明鴻僑居日本,為一熱血青年,空手道黑帶高手。為人正直,熱心,理想,MBA畢業後,自願申請回台服役。 為了省錢,我申請最便宜的宿舍,就是沒有浴廁或廚房的房間(studio),有一個黑人室友。洗澡如廁都得到同層樓的公用浴廁,用鑰匙開門後才能進入, 但浴廁內全然沒有門或簾子。我盡量選人少時去,特別選邊間。我每日如受驚的兔子,平時能不出戶就不出戶。直到有一天進入浴廁時,赫然看到一個老黑男子也在裡面,在此前已聽聞宿舍大樓內種種罪案,強暴案,酗酒械鬥,抽毒品等等。趁著沒嚇昏前,奪門而逃。和姐商量後, 決定加錢搬到四樓附有浴室的小套房宿舍,這時已進入了10 月份。 為了省錢,我申請最便宜的宿舍,就是沒有浴廁或廚房的房間(studio),有一個黑人室友。洗澡如廁都得到同層樓的公用浴廁,用鑰匙開門後才能進入, 但浴廁內全然沒有門或簾子。我盡量選人少時去,特別選邊間。我每日如受驚的兔子,平時能不出戶就不出戶。直到有一天進入浴廁時,赫然看到一個老黑男子也在裡面,在此前已聽聞宿舍大樓內種種罪案,強暴案,酗酒械鬥,抽毒品等等。趁著沒嚇昏前,奪門而逃。和姐商量後, 決定加錢搬到四樓附有浴室的小套房宿舍,這時已進入了10 月份。 這個單位一進門有一廳附加一臥室(one bed room), 四個室友,一黑,一白,二黃就是我和另外一位也來自台灣的琴。琴的姐姐在中國城開餐館,琴白天在姐姐家餐館打工,晚上上完課為安全就住進宿舍。琴和白人都不願和黑女同一間,我一向不善與人搶奪,我只好和黑女睡一間了。這黑女 極盡所能欺負我,包括不讓我用插座,我就不能用檯燈讀書;不讓我用壁櫥,我的衣服只好放在皮箱裡;用廁所也得她優先。姐姐為我準備了一些簡單的烹飪廚具,她不借自用,拿了不還;把煙蒂丟在我的碗盤杯子裡。琴年紀比我大的多,來美有幾年了,黑女和她倒有說有笑。黑女欺負我,琴人前人後都是袖手旁觀,不過回想,琴並沒有和黑女合起來欺負我,算是不錯了。誰知黑女趁感恩節放長假時,把琴的電視偷了。等琴回來, 輕描淡寫的說,她出去倒垃圾,忘了鎖門,回來琴的電視就不見了,也已經很貼心的替琴報警。此地無銀三百兩,琴還以為她們是朋友呢。 這個單位一進門有一廳附加一臥室(one bed room), 四個室友,一黑,一白,二黃就是我和另外一位也來自台灣的琴。琴的姐姐在中國城開餐館,琴白天在姐姐家餐館打工,晚上上完課為安全就住進宿舍。琴和白人都不願和黑女同一間,我一向不善與人搶奪,我只好和黑女睡一間了。這黑女 極盡所能欺負我,包括不讓我用插座,我就不能用檯燈讀書;不讓我用壁櫥,我的衣服只好放在皮箱裡;用廁所也得她優先。姐姐為我準備了一些簡單的烹飪廚具,她不借自用,拿了不還;把煙蒂丟在我的碗盤杯子裡。琴年紀比我大的多,來美有幾年了,黑女和她倒有說有笑。黑女欺負我,琴人前人後都是袖手旁觀,不過回想,琴並沒有和黑女合起來欺負我,算是不錯了。誰知黑女趁感恩節放長假時,把琴的電視偷了。等琴回來, 輕描淡寫的說,她出去倒垃圾,忘了鎖門,回來琴的電視就不見了,也已經很貼心的替琴報警。此地無銀三百兩,琴還以為她們是朋友呢。 一到學校,我為減輕父母負擔,申請在圖書館打工, 一小時工資不到兩塊錢,但對飯錢已不無小補。這個學校治安太差,圖書採不開放制度。填了書單後,我們才把書從樓上書庫找出來,再送到櫃檯出借。有打工女生在樓上書庫被強暴,我每次打工時也都是風聲鶴唳,提心吊膽。 一到學校,我為減輕父母負擔,申請在圖書館打工, 一小時工資不到兩塊錢,但對飯錢已不無小補。這個學校治安太差,圖書採不開放制度。填了書單後,我們才把書從樓上書庫找出來,再送到櫃檯出借。有打工女生在樓上書庫被強暴,我每次打工時也都是風聲鶴唳,提心吊膽。 週末,通常都只有我一個人在宿舍,我沒有電話,沒有朋友,沒有親人,也不敢出房門。不是去圖書館打工,就是寫信,要不啃書。奇怪了,那晚就黑女沒出去玩。她告訴我,不准進房間,她有客人來,原來是她的情人,我就這麼在另兩個室友的房間呆坐一晚,又怕又累又覺噁心,不知怎麼辦?也怕他們報復,掉了一晚眼淚。 週末,通常都只有我一個人在宿舍,我沒有電話,沒有朋友,沒有親人,也不敢出房門。不是去圖書館打工,就是寫信,要不啃書。奇怪了,那晚就黑女沒出去玩。她告訴我,不准進房間,她有客人來,原來是她的情人,我就這麼在另兩個室友的房間呆坐一晚,又怕又累又覺噁心,不知怎麼辦?也怕他們報復,掉了一晚眼淚。  又個週末,只有我一個人在宿舍裡。過了午夜,忽然聽到宿舍鐵門咚咚大響,我從電眼裡一看,看到一個面目猙獰的巨大黑鬼,滿臉鬍渣,手拿著釘有釘子的木棒,穿著豹皮的背心,活脫脫就是非洲土著的打扮,三更半夜的要進門來,嚇得我牙齒打顫。他操著特別的紐約腔(紐約客說英文好像含著顆核桃)和黑人腔要找我室友,那個裝扮,我以為他要來尋仇殺人的。雖是鐵門,門上還有三道鎖,我還是怕他破門而入,怎麼辦?房裡又沒電話。我說她不在,他還是要我開門。我堅持說NO. 他磨蹭了幾分鐘後才走,當時度秒如年,心臟跳到嗓子眼裡。 事後才知道那晚是鬼節,這是什麼鬼節啊?黑子不化妝都怪嚇死人了,對已每日如驚弓之鳥的我,那種恐懼是我前所未經歷過的。 又個週末,只有我一個人在宿舍裡。過了午夜,忽然聽到宿舍鐵門咚咚大響,我從電眼裡一看,看到一個面目猙獰的巨大黑鬼,滿臉鬍渣,手拿著釘有釘子的木棒,穿著豹皮的背心,活脫脫就是非洲土著的打扮,三更半夜的要進門來,嚇得我牙齒打顫。他操著特別的紐約腔(紐約客說英文好像含著顆核桃)和黑人腔要找我室友,那個裝扮,我以為他要來尋仇殺人的。雖是鐵門,門上還有三道鎖,我還是怕他破門而入,怎麼辦?房裡又沒電話。我說她不在,他還是要我開門。我堅持說NO. 他磨蹭了幾分鐘後才走,當時度秒如年,心臟跳到嗓子眼裡。 事後才知道那晚是鬼節,這是什麼鬼節啊?黑子不化妝都怪嚇死人了,對已每日如驚弓之鳥的我,那種恐懼是我前所未經歷過的。 黑鬼室友越來越過分,有晚九點我下課回宿舍,黑女反鎖不讓我進大門, 其他兩個睡客廳的室友明哲保身,也不幫我開門。我在走廊外一直敲門,無人搭理。我又怕又氣,不知如何是好?我怎麼那麼倒霉來到這個鬼域, 碰上一群鬼?欺人太甚。爸媽教我,什麼吃虧就是佔便宜,什麼退一步海闊天空!沒法子了, 我只好打共用電話給曾明鴻。他馬上趕來,帶我去敲舍監的房門,波多黎各的女舍監說夜晚了,相應不裡。但曾明鴻知道堅持據理周旋,她不得不開門出來,很生氣的罵我們。她用備份鑰匙打開了我宿舍的房門。黑鬼看她進來,就惡人先告狀,哭了起來,聽不清楚她那黑人腔說什麼?我實在不知道她能抱怨我什麼?我那時英文雖還不夠溜,頭腦稚嫩單純,但也已忍無可忍,把黑鬼欺負我的事全盤說出,曾明鴻也幫我理論,要求換房。因為有前例,一個白女生抱怨她的黑室友, 結果被黑室友的男朋友強暴,事情鬧得很大。舍監也怕又有事端,答應可以換房間。黑鬼不肯換,那我換。結果換到的新宿舍更好,附有廚房,不必再加錢。但我的家人仍然擔心的不得了,贊成我轉學。在熬過了第一學期後,在姐姐的協助下,我順利的轉學了。 黑鬼室友越來越過分,有晚九點我下課回宿舍,黑女反鎖不讓我進大門, 其他兩個睡客廳的室友明哲保身,也不幫我開門。我在走廊外一直敲門,無人搭理。我又怕又氣,不知如何是好?我怎麼那麼倒霉來到這個鬼域, 碰上一群鬼?欺人太甚。爸媽教我,什麼吃虧就是佔便宜,什麼退一步海闊天空!沒法子了, 我只好打共用電話給曾明鴻。他馬上趕來,帶我去敲舍監的房門,波多黎各的女舍監說夜晚了,相應不裡。但曾明鴻知道堅持據理周旋,她不得不開門出來,很生氣的罵我們。她用備份鑰匙打開了我宿舍的房門。黑鬼看她進來,就惡人先告狀,哭了起來,聽不清楚她那黑人腔說什麼?我實在不知道她能抱怨我什麼?我那時英文雖還不夠溜,頭腦稚嫩單純,但也已忍無可忍,把黑鬼欺負我的事全盤說出,曾明鴻也幫我理論,要求換房。因為有前例,一個白女生抱怨她的黑室友, 結果被黑室友的男朋友強暴,事情鬧得很大。舍監也怕又有事端,答應可以換房間。黑鬼不肯換,那我換。結果換到的新宿舍更好,附有廚房,不必再加錢。但我的家人仍然擔心的不得了,贊成我轉學。在熬過了第一學期後,在姐姐的協助下,我順利的轉學了。 除了我個人遭遇外, 還有藥劑系的白人學生就在宿舍大門口外,光天化日下,車被搶後,還被一群黑鬼捅了十二刀,脾臟破裂,生命垂危。黑警衛擔心自己的安危,見死不救援,事後黑警衛被開除,又有何用? 除了我個人遭遇外, 還有藥劑系的白人學生就在宿舍大門口外,光天化日下,車被搶後,還被一群黑鬼捅了十二刀,脾臟破裂,生命垂危。黑警衛擔心自己的安危,見死不救援,事後黑警衛被開除,又有何用?  遊行 遊行 每年到了鬼節, 我總不由自主的想到初到紐約的那舉目無親,心驚膽裂的四個月。我經歷到欺善怕惡沒有是非的人性,冷漠袖手黑暗的大都會, 美國黑白種族的衝突, 和一個敗壞的環境。但也遇到了像曾明鴻熱忱善心,不畏強勢,古道熱腸的人, 在我最孤立無援時對我伸出援手,這種好人難求。可惜我生性迷糊,竟然沒有留下通訊,一直很想當面跟他說謝謝當年的照顧和溫暖的友情。 每年到了鬼節, 我總不由自主的想到初到紐約的那舉目無親,心驚膽裂的四個月。我經歷到欺善怕惡沒有是非的人性,冷漠袖手黑暗的大都會, 美國黑白種族的衝突, 和一個敗壞的環境。但也遇到了像曾明鴻熱忱善心,不畏強勢,古道熱腸的人, 在我最孤立無援時對我伸出援手,這種好人難求。可惜我生性迷糊,竟然沒有留下通訊,一直很想當面跟他說謝謝當年的照顧和溫暖的友情。 雖然留學生涯後面還有更多的荊棘挑戰等著我,但這段時日已堅強了不少我的心智,也漸漸讓我明白禮讓容忍有時只會招致更大的磨難和屈辱。家人都為我能安全離開布魯克林而高興,覺得自己還是幸運的。 每個曾駐足的地方,都讓我有懷念的時刻,但只有紐約布魯克林這個jungle, 我是逃離的。再去時,我會小心,但我不再害怕。 雖然留學生涯後面還有更多的荊棘挑戰等著我,但這段時日已堅強了不少我的心智,也漸漸讓我明白禮讓容忍有時只會招致更大的磨難和屈辱。家人都為我能安全離開布魯克林而高興,覺得自己還是幸運的。 每個曾駐足的地方,都讓我有懷念的時刻,但只有紐約布魯克林這個jungle, 我是逃離的。再去時,我會小心,但我不再害怕。 PS。陳明韶的浮雲遊子錄音帶一直伴著我, 從那時到現在. 11/24/11今天是感恩節,覺得是很幸運的一天。因為熱心的傅驛涵格友,竟然找到此文中30+年前對我伸出援手的曾明鴻。 我們電聊了一個多小時,毫無隔閡。茫茫人海竟然能再聯絡上, 除了感謝傅驛涵格友, 只能說緣分不淺。真的很高興。 |
|
| ( 心情隨筆|心情日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