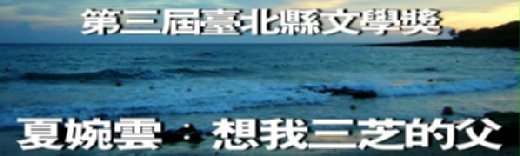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08/04/23 22:14:33瀏覽2069|回應2|推薦24 | |
第三屆臺北縣文學獎:想我三芝的父
第三屆臺北縣文學獎作品集》散文得獎人夏婉雲得獎感言:
我的三芝地圖是繪在童年記憶上的。回來三芝,這一切又都活了過來,模糊的街道、房屋、景物走近了,童年的事、物走回來了。穿過地圖中央的是海浪,浪聲一直在我心中起伏。 剛從繁華的台中市學校對調到三芝的國小教書,真有點不習慣。雖然我在這兒出生、六歲才離開,但畢竟隔了二十年,對這兒印象已模糊。現在,要長期面對它,油然而生的,是一股淡淡的、陌生多於熟悉的慌張感。 小時候,我在父母吵吵合合中長大。十坪大的眷舍圈不住母親,三芝沒工廠、沒出產,貧瘠的土地使她寒了心。 年輕的母親總嫌棄地說:「這兒什麼都沒有,只有你們外省人一個又一個的海防崗哨。」記得六歲那年冬天,他們永無寧日的吵,母親執意要離開父親,她指著遠處的崗哨,嘮嘮叨叨:「我受不了,夏天嘛燥熱烘悶,冬天又濕又冷;住這兒,薪餉永遠不夠用、我永遠找不到工作,才不要老死在這裡。」56歲的爸爸拉著母親的手,跪地求她:「不要嫌我窮、嫌我老,外面的花花世界不會比三芝好,不要帶孩子走。」
終究,母親帶著我投奔台中大姨媽,一去再沒回頭,她在工廠討生活。有了繼父之後,我安靜、過分乖巧地上學,母親怕繼父不高興,不准我提父親,也不准我說三芝;三芝離我越來越遠,越來越糢糊,遠到只剩一點一粒,像那微不足道的海砂一樣。我也曾試圖去回憶父親的樣子,但連一張照片也沒有;就算勉強想起一點什麼,也很快沒法連續下去,像面對著茫茫大海,丟不出魚線,沒有了魚線自然是勾不到那團記憶的。 之後我快樂又不怎麼快樂的讀高中,又考上公費的師院,直到在台中教了二年書,平靜的日子突然起了波瀾──母親得了肝癌,她很快的瘦骨嶙峋。一天在醫院,我附在她耳朵指著北方問:「媽!妳想不想知道那邊人的消息?」她看了我許久,兩行清淚落下。母親臨終前,緊握我的手,看著我猛點頭。 我知道母親的心意,她心裡有個秘密花園,這從來不說的悔楚已藏了二十年,我要幫她找到開花園的門匙,拉起那條勾得住記憶的魚線。 外縣市教師對調時,我填了偏僻的台北縣三芝鄉,同事們很驚訝,在惋惜聲中,我來到數百里之外的鄉下。 三芝果然很偏遠,如果台灣北部是一個桃子,那麼從台北市中心到三芝,可以說是從果核向外爬,是從內部的都市爬上來,來到外部果肉的邊邊。現在我就像是站在一顆完整的桃子表皮上,孤孤單單,像一滴水要面對整座大海。初來乍到,往海邊一站,大風一吹,就有種隨時要被吸入海中的漂浮感。後來,是三芝可愛的學生和老人拉住我的吧! 忙碌的開學、安頓好租處,適應了生活已是二月二十日。在街上我會看見老榮民拄著枴杖走,他們等車時我會和這些老人聊聊談談,我在其中找尋著父親的影子。 這些老人操著各省口音,而他們的老伴常是閩南族、埔人、啞吧、殘障。我問了多少人都不知道誰是「陳銀川」,直到228那一天。 就是「2004年228牽手護台灣」那天,我與室友跑到淡金公路、淺水灣上,加入手牽手活動,同一時間,我就認識了一群七、八十歲的三芝老伯伯。 那時我們站在蜿蜿蜒蜒的淺水灣路上,望著大海,雲霾散去,海上仍然波濤洶湧、海風呼呼。我和同鄉手牽手站在海岸線上和北門、金山、萬里的人,人人心手相連,我想像台灣海岸線1,434公里全站滿了人,連成人鍊的長城,如兒童畫,番薯地圖邊緣上都畫滿了人,無論原住民、台、閩、客、外省人。
陰雨連綿數週,那天才剛雨霽天晴,左右邊的「三芝手」粗糙硬實,這時突然颳起一陣強勁的海風,吹得我裙裾高高飛揚,我彎身壓下鼓風爐般的膨裙,大風一吹,我一個踉蹌不穩,眼看人牆因我而向前仆伏倒下──「長城」就要掙鉤脫鍊;說時遲那時快,左邊人強勁的把我扶正,虧得長繭的手如此大力,我連聲道謝。 我亟待站穩腳跟,頭上的帽子偏偏迎風飛走;我先用力撐穩隊形,再脫鉤離隊跑去撿帽子。帽子被風趕著向前跑,飛到芝蘭公園裡,飛到涼亭前另一小群人中,被一個老人彎身拾起,老伯伯微笑遞還時,我碰到他龜裂長繭的手;抬頭一看,是個癟著嘴、口中已無牙的老翁,我連聲道謝。這位老伯溫和地看著我:「不要客氣,小姑娘。」
我在涼亭裡左右張望,眼前不是一位而是一群,總共六個榮民,這涼亭距離「牽手長城」十幾公尺之遠,顯然是來看熱鬧的,我禮貌的找話問:「老伯,您們來『看』手牽手護台灣啊?」 一個眉上有刀疤操著四川口音的人,粗聲說:「手牽手是做出來的,什麼手牽手?我呸!」他往地下吐一口痰。 一個老伯大聲說:「要說護台灣,我們這群老兵最守護台灣。」然後回頭徵求同伴們的意見:「你們說,對不對?」所有的老伯們都點頭,說完他手一直抖,不由自主的抖手,大概得了帕金森症吧!我想。 這真有趣,我太幸運了,我回頭和室友喊話,留在涼亭裡不想歸隊了。我問:「您們年輕的時候就巡守海防,一直到老嗎?」但我心裡想的是父親。 他們說原來都先駐在別縣市,大約五十歲,才調到海防部隊來巡防養老。在以前,海防部隊駐紮在各海岸班哨,後來有電子設備、人造衛星等科技偵測海岸線,不需要人為戍守;同時兩岸局勢也和緩些,海防班也就陸續撤銷,改成巡安全了。 他們階級都是士兵、士官長,有人單身、有人在這兒結了婚。都是六十五歲退役,人情來往都在這兒,也就在三芝養老了。 「小老師,我們常常黃昏時來這兒聊天,看夕陽西下,吵歸吵,但老來還是伴。」一位不經意的說。 「常來這兒聊天?」我眼睛一亮。 第二天再來時,我找一話題,問道:「你們以前在海岸巡防,颳風下雨的,很辛苦喔?」我想到媽媽痛恨這兒的冬雨密布、海風欺人。 他們說三芝的雨季長達四個月,寒夜站崗穿雨衣還全身濕透,浪打來,只有孤孑的自己在,感覺天地為之崩裂,那份遺世感,只有站崗人知道;雨季漫長,影響站的情緒,他們嗓門特大、常愛吵架。 第三天,我又騎摩托車來公園涼亭和老兵們聊天。前次接觸的老兵對海是怨懟慨嘆,再次接觸,這些老兵看著滿天晚霞對海是喜愛不捨。 和他們日漸熟了,我鼓起勇氣問:「有人知道『陳銀川』這個人嗎?寧夏省人,北方高個兒。」他們都說不知道。刀疤佬讀出我的落寞,問我為什麼找他? 當我說明調過來的故事時,刀疤佬拍著胸脯說:「我幫妳找,我們三芝、石門、金山、萬里有榮民聯誼中心,沒問題。」榮民有肝膽、有俠義,我見識到了。 當天心情豁然開朗,我沿著濱海的原木步道走向觀海堤,太陽快要西斜,暗紅餘暉滿天,照得細沙一片嫣紅,而浪花還是白粼粼。賞完落日,我步入一家叫「卡薩布蘭卡」的咖啡店,倚靠窗邊,點一杯「卡布奇諾」,心情真是未有的舒暢。我拿出媽媽的照片,舉杯敬她:「媽!就快有好消息了。」 坐在這百餘坪的觀海平台,看遼闊的海岸上,趁店主人──楊先生空閑我和他聊天,我說自己是三芝人,記得以前這裡並不熱鬧。 他深表同意的說:「二十年前,這裡一到濕冷的秋冬,就像是一排廢墟,風吹門窗都『空隆 空隆』的響,非常殘破。這四年轉運了,颳起休閒風,咖啡店開得如雨後春筍。」 他說自己二十年前剛退伍沒工作,就回家鄉在這兒開了第一家咖啡店,以後別家陸續跟進,淺水灣爆紅成觀光名街。
「這兩年,本鄉的人不足,都要從外地請人來打工。」我不得不佩服他二十年前就有遠見,「本鄉的人不足,打工的人,都要從外地請來。」我看著媽媽的照片,啜一口卡布奇諾,哎!這冷咖啡既苦又澀。 飯後走回路邊牽車,海面星光燦燦,近處後厝漁港點點漁火。我仰頭輕聲對天上的媽媽說:「媽!當年要是有今天的咖啡店,您就可以在這兒工作,我們就不離家了,還可以數著星星回家呢!」回首看,海潮湧大浪,浪花翻滾,風雲變化,瞬息萬千。 芝蘭公園成了我每天必到之處,這些老伯伯對我搖搖手,我知道還沒查到。一週後的某天,「刀疤佬」指指右邊說:「陪我走到咖啡街,看一個人。」雨霽天晴,風已平,浪未止,海洋洶湧仍在掙扎脫困。我們默默走過荒廢的一落落「太空造型屋」、走過城堡似的佛朗明哥大社區。遠處海天交接線,一衣帶水,含著輕紗,泛著一線灰藍。 老伯邊走邊說:「咖啡街盡頭有一屋是榮民服務處,這『聯誼會』,是老兵聊天看報處,裡面有位老劉在看守,我們去他那兒。」
客廳的左邊沒什麼好看,一扇拉門關上,後面大概隔著一貯藏室吧!我猜。我走向右邊,牆上相框上有許多照片,刀疤佬一一介紹他們的聚會照,並說:「大部分人都回『老家了』。」 他又指指裡面:「老劉就住在那小房,上香是他的功課。」
我站起來,跨兩步就瞄到小房一單人床、一桌椅而已,但是牆上掛著蔣公與經國先生的遺照;兩邊床角,居然插著國旗和黨旗,旗桿還在,只是經年海鹽浸蝕,國旗已褪得不成顏色。我心中狐疑國旗和照片為什麼不放客廳而要放寢室? 回到有點紊亂的客廳,刀疤佬把左邊沒什麼看頭的拉門「刷──」地拉開,我冷不防嚇了一跳,雙腳差點退出,原來拉門後凹櫃裡,赫然立了許多紅木的牌位,牌位眾多,一排十二個,還分三排陳列。 「不是說聯誼會嗎?」我心驚膽跳,心算一下,三十四個牌位,我有不祥的預感,不由得呼吸急促。
「原本是聯誼會。老兵多半單身、獨居,沒人祭祀,擺這兒方便大家拜祭。」 我感覺一陣冷,從椅子上一躍而起,急忙湊近牌位,由第一排從左到右一路急尋,最後在第三排點中間,赫然看到「寧夏省銀川縣陳銀川之牌位」。我扶著牆緣幾乎暈眩,刀疤佬扶我坐回椅子,一直拍著我肩膀,但我捶他,哭著:「你太殘忍,為什麼不先告訴我?」 我趴著桌上嚎啕大哭,這想爸爸的痛,別人是不能理解的。我嚶嚶啜泣了好久,刀疤佬哄拍我這才開口:「我們以為他還在世,一直查不到你父親在哪兒。昨天才想到可能在這裡,我昨天才來,查了牌位。」 「今天,又不知道如何先啟齒,真是抱歉,小姑娘。」他繼續說:「這裡也稱著小忠烈祠,單身同袍的骨灰都在納骨塔,而牌位供在這兒方便祭拜。小老師,你要想到有三十多位兄弟陪他,有人常常祭祀,就不會太難過了。」 不發一語的劉老,這時駝著背,蹣跚的抬起雙腿,轉身,點起九柱香,海風也輕快地跟著他轉身。他點燃三柱香給我,我學著他先拜中間的地藏王菩薩、土地公陶像,刀疤佬唸唸有辭:「請保佑這裡的同袍,請保佑陳銀川兄弟。」又轉身朝外,向大海拜一拜,屋前插根香,海風這時呼嘯不止。再回頭,我跪在父親牌位前,心中哭著:「爸爸!女兒不孝,到現在才來找您,您一人在三芝,寂寞了快二十年。」我不可遏止的跪地不起。 去了三芝納骨塔,看到爸爸的骨灰罈,又把爸爸的牌位從淺水灣劉老那兒請來租屋祭拜。 每次,我只能和劉老筆談,八十三歲的他有重聽,而他廣東「佛山寺」縣口音,我越聽越懂。占地約五坪的「小忠烈祠」,也越來越不覺得陰森,原本覺得侵入樑柱、沁入桌椅的陰氣,多去幾次也不怕了。三十多個牌位,淒慘的清冷,想必劉老早已習慣。 「我爸晚年都做什麼?」 「他有沒說過有一女兒?」 可惜,劉老認識爸爸,但又不太熟,只能泛泛的談他。「榮民都習慣了,從大陸來-----,日子總要過啊!」「有些老兵的太太跑掉,榮民都這樣飄泊慣了,孩子離開鄉下也好,----。」 他愛邊說邊擦拭桌椅,年年月月的海風,伴隨著海沙,桌椅擦也擦不淨。滿臉皺紋、嘴皮扁扁的劉老,大陸開放後,像許多老兵一樣帶大筆錢財回老家,還把三芝房子賣了回廣東,又住不慣家鄉,洗劫似的回到台灣;住幾年榮民之家,也不喜歡,無錢無屋的只好寄居聯誼會,和牌位一起,居然熬了二十年。 這是多麼後現代啊!我苦笑著:在「海洋深呼吸」、「巴莎瓦諾」、「OIA 伊亞藝術咖啡館」、「普羅旺斯咖啡店」等異國風情店的邊間,有一個很傳統的老實人住著,家伸出去的沙灘,就是香蕉船馳騁的海域、水上摩托車的起點。而他過著洞窟式的生活,在少年郎呼嘯聲中自得的讀讀書、玩個「減紅點」;隔壁villa Sugar的年輕打工店員很知禮,都會請他過去吃三餐,雖然不知他姓誰名啥,也完全聽不懂他的鄉音,只稱他「阿伯」。
榮民袍澤逐一仙風作古,喪偶獨居的劉老想是最後一個駕鶴騰返的人。劉老是父親的影子,每次探視他,再回頭聽潮聲,看它刷起又刷落,在大海的底片上,這時代有太多大小小的悲歡離合。 「現在有您借住在這裡『照顧』它們,那將來呢?」我用筆談。 「不知道,『刀疤』他們,可以初一、十五、三節的輪班上香啊!放心,牌位放在一起,既使沒人祭祀,也不寂寞。」劉老專心的擦拭紅木牌位,慢慢地──似乎在向每一位說話。
海防人員的海不出三十公尺之外,我的海是不是也不出二十公尺之外?牌位的主人,下輩子還願靠海嗎? 來到這兒任教,天天看海、識海,我漸漸變了,我常常自省:老兵是國家的榮光,他們都是俱足的一滴水;小水滴,面對大海,是完整、也是俱足。我也是一小水滴,我如何瞭解大海?我如何了解從大陸來台的老兵,如何了解爸爸鰥居近20年的心,爸得年七十四,那如割的落寞是多大的痛,日日夜夜的割傷,我無法彌補;現在能做的,只有把劉老當成爸爸,多陪陪來日無多的劉老、多關心三芝的老兵了。
爸爸在我屋裡,和新做的媽媽牌位並列,每晚家人有幸全部到位。我安穩的輕閤睡眼,猶如漂在海面。爸爸是海,我可以睡在海面,先雙手、雙腳放鬆,再頭鬆、頸鬆、關節鬆,沒有一絲一點的壓力。我不思、不想,睡得很安適。每個清晨都酣暢醒來,我知道:海的胸膛厚實千丈,包羅萬象、胸懷磊落如父,我是它最愛的子女。 冬日,我常來聯誼會陪劉老,或唸故事或講笑話。海無聲的怒吼,我蜷伏窗口,想像自己能看到遠遠的深海旗魚,如果我是條長喙旗魚,對生養的海是怎樣的感謝? 有個雨夜,我站在租屋窗外,伸出舌頭,品嚐雨的濕潤,想著長喙旗魚,牠的尾鰭也很長吧!會啪啪打響嗎?夜裡,那條旗魚入夢來,濕漉漉的長尾鰭叩得我窗戶,「啪--啪」乍響,一直吵我、似乎邀我一探海的奧境。夢中,我跟著旗魚做仰式游泳,全身放鬆,一前一後,一大一小,我是海的兒女。我游到台灣海峽,兩手一拉,海峽壘起、兩岸攏來,爸爸、劉老、刀疤、癟嘴高興的走去對岸。醒來方知是夢;再細想這仰泳的姿勢好熟悉,哪裡見過?最後才想到夢的源頭是我看過的一張照片,是劉老翻箱倒櫃的找,找到他和爸爸年輕時的合照,他仰式游在大海中,不!睡在大海中。海和我糾纏共生,大海給我呼吸、哺育了我。從中部到北海岸,我一路仰慕它的風華,海一定有磁性,吸著我一路尾隨。
海邊榮民一一回「老家」了,如果我收集每位的故事、記憶,是不是我心中就有一個小小牌位,供奉他們、收納他們對海的記憶、意識。 爸爸!海一定是鹹、苦、酸、澀,集記憶的總合;您,在我心中,也是。 ( 本文部份圖片取自網路,如有侵權敬請告知當即刪除。)
|
|
| ( 創作|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