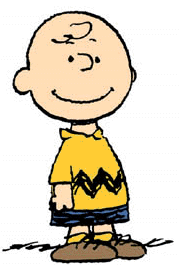能否以成敗論英雄? 歷史有時的確會有偶然的巧合和反諷。 「學衡派」的美國導師,新人文主義思想家白璧德1933年7月去世,《學衡》雜誌恰好在這個月停刊。 梅光迪是新文化運動的反對派,思想方法和文化觀念與胡適為敵。但他卻是最積極的自由戀愛、自由婚姻的實踐者。他革了舊式包辦婚姻的命,與自己的女學生(東南大學第一屆女生,也是西洋文學系的學生)李今英結婚。而胡適卻一生就範於包辦婚姻。 梅光迪反對白話文學,也拒絕寫白話文。可是他的女兒梅儀慈作為在美國大學執教的漢學家,卻是以研究中國白話新文學為志業,並且是著名的丁玲研究專家。 若以實用主義的功利眼光來看,由於胡適的存在,梅光迪成為一個人生的失敗者。胡適的陽光和輝煌,使得梅光迪逃遁海外或暗淡一隅。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梅光迪執教美國時,因受Mercier教授的《美國的人文主義》一文的啟發,而寫了《人文主義和現代中國》,這是他自1922年8月在《學衡》第8期發表《現今西洋人文主義》十多年後的歷史反思。回顧自己曾置身而失敗的中國的人文主義運動,一腔的傷感,滿腹的怨尤,以及無限的惆悵,流於言表。因為他看到新文化運動以來所形成的文化激進主義浪潮,以及關於變革與革命的信仰已經成為一種新的傳統。這種傳統比以往任何舊的傳統都具有自我意識和良好的組織性,且不容異己的存在。他無法施加自己的學術影響,感到無能為力。 人文主義運動? 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是否有一場所謂的人文主義運動?梅光迪的回答是肯定的。在《人文主義和現代中國》1一文中,他有系統的論述;《評〈白璧德──人和師〉》中,他說這是「儒家學說的復興運動」2。同時梅光迪也承認「這樣的一次運動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得到公平的待遇」3,是「中國領導人的失敗」4。其失敗的原因有兩點:一是因為它與中國思想界胡適及新文化派想要建成和接受的東西完全背道而馳。二是因為他們自身缺乏創造性,甚至沒有自己的名稱和標語口號以激發大眾的想像力。從一開始,這場運動就沒能提出和界定明確的議題。領導人也沒有將這樣的問題弄清楚,或者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它對普通學生和大眾造成的影響不大。《學衡》的原則和觀點給普通的讀者留下的印象是:它只是模糊而狹隘地局限於在一些供學術界閒談時談論的文史哲問題上。 而胡適對《學衡》的看法則是認為它只是一本「學罵」。他認為「新文化─文學」的「反對黨」已經破產,根本無力與「新文化─文學」對抗。更為樂觀的是北洋政府教育部已經下令,自1920年起,小學課本改用白話文。這樣一來,1922年1月創刊的《學衡》所反對的白話新文學,以及他們所反對的新文化運動的言行,便顯得蒼白無力。成了唐吉·可德戰風車的局面.... 白璧德的身影 歐文·白璧德的思想方法來源於英國的馬休·阿諾德。在梅光迪之前,中國留學生張歆海在哈佛大學師從白璧德時,曾以研究馬修·阿諾德作為博士學位論文。1923年2月,梅光迪在《學衡》雜誌上刊出《安諾德之文化論》,介紹阿諾德的文化思想。 阿諾德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化主將,是英美知識傳統中具有文化保守傾向的思想家。他對社會的變革,有自己主見。阿諾德《文化與無政府狀態》的中文譯者韓敏中在《譯本序》中指出:阿諾德所希望看到的變革和進步是「絕對不能脫離過去,脫離歷史和文化的根基,絕不能輕言甩掉我們的歷史、文化、情感、心理的包袱」。「為了在秩序中實現變革,使英國、當然也是使人類平穩地走向更高的理想境界,就必須依靠廣義的文化力量。文化不是行為的敵人,而是盲目、短效行為的敵人」5。 1914、1915年間,在西北大學讀書的梅光迪,因偶然的機會,聽到R S 克萊恩教授的一次演講。克萊恩指著白璧德的新著《現代法國評論大家》對同學們說:「這本書能讓你們思考。」6一種頂禮膜拜的熱忱,使梅光迪從托爾斯泰式的人文主義框框中走出,沈迷於白璧德的世界裏。梅光迪由白璧德思想的啟發而認識到,中國也必須在相同的智能和精神的引導下,以冷靜、理智的態度,在中國人的思想觀念中牢固樹立起歷史繼承感並使之不斷加強。只有這樣才能跨越新舊文化的鴻溝,使西方的人文主義思想與中國古老的儒家傳統相映生輝。為了能夠聆聽這位新聖哲的教誨。梅光迪1915年秋轉學到哈佛大學。 白璧德繼承了馬修·阿諾德的思想,其人文主義的要旨為生活的藝術,即追求人生盡善盡美的理想境界。人文主義要求具體的個人從自己的修養入手,以好學深思,進德修業,「向內做工夫」。進而謀求理性與感情的和諧,求得人格的完整。人文主義的理想為君子風度。君子有三長:中立(克己、節制、不激不隨)、敏感(反對麻木不仁,但也非好奇立異)、合理(合於標準,不隨心所欲,不逾矩)。這與中國的儒家學說:中庸、仁、禮正好相當,或最為接近7。 白璧德等人所領導人文主義運動主要目標是,要把當今誤入歧途的人們帶回到過去聖人們走過的路徑之上,即「用歷史的智能來反對當代的智能」8。.... 虛幻的精神啟蒙?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反對派,梅光迪認為胡適及新文化運動帶給中國人的是一場虛幻的精神啟蒙。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使得大多數中國人從極端的保守變成了極端的激進。而其中嚴肅認真的一少部分人,也正忍受著一種思想的空白和精神領域的尷尬所帶來的煎熬,甚至是絕望和憂傷。由於在中國的教育文化、政治思想領域扮演主角的知識份子(指胡適等人),自身思想膚淺,且已經完全西化,他們對自己的精神家園缺乏起碼的理解和熱愛,「對自己的祖先嗤之以鼻,以民主、科學、效率及進步為其支架,毫無愧疚與疑義地將目前西方的官方哲學當作積極的主要價值觀」11。「新文化運動」的結果,使中國文化喪失了自身利益的特性和獨立性,成為歐美的文化翻版。梅光迪擔心的是「用不了幾年時間,中國很可能就會成為西方所有陳舊且令人置疑的思想的傾倒之地,就像現在它已成為其剩餘產品的傾銷地一樣」12。他說導致中國大多數人走上激進之路的原因主要是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帝國主義列強給中國帶來的一系列的災難性的衝擊,而國內回應的便是由此引發的革命熱潮和革命運動。所有這一切加在一起便導致了對文化傳統的置疑和民族自信心的喪失。在面對陌生的突發性事變而又必須作出的快速變革和調整時,他們因準備不足而顯得茫然不知所措,進而轉向西方以求光明和向導。結果是中國失去了自身的文化優勢。梅光迪認為「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失敗的運動。 《學衡》的使命 梅光迪自己視他和《學衡》同人是另類,是對中國文化有更深層思考的,有能力對中國人的生活中發生劇變進行合理解釋的知識份子,是中國西化運動中的理性之翼。和美國的人文主義者一樣,中國的人文主義運動的支持者也是大學裏的學者。他們的學術陣地主要是1922年1月創辦的《學衡》雜誌(1922年1月──1933年7月),和相應的三個報刊:天津《大公報》的《文學副刊》(吳宓主編,1928年1月2日──1934年1月1日)、南京的《史地學報》(柳詒征主編,1921年11月──1926年10月)、《國風》(柳詒征、張其昀、繆鳳林、倪尚達編輯,1932年9月1日──1936年12月)。 在《學衡》的同人看來,捍衛中國知識界的偉大傳統,維護它的聲譽,推動中國文化的發展,是《學衡》神聖的歷史使命。面對文化激進主義的強大走勢和猛烈的批判炮火,他們並非對自身民族傳統中的問題熟視無睹,他們更願意承認中國的文化傳統在經過長期的與世隔絕之後,已經陷入狹隘的自我滿足、固步自封中,因此在比較和競爭中缺乏優勢。所以,它必須要得到豐富、補充,在退化的情況下,還必須得到修正。而不是徹底毀滅它。《學衡》同人堅信目前更為緊迫的任務是要對已經取得的成就加以重新審視,為現代中國重塑平衡、穩定的心態。這樣才是真正的文藝復興的基礎和可能。有了這個文化本位,才會有批判性的接受西方文化中有益的東西的必要條件。《學衡》雜誌的特別之處更在於它以各種方式告示國人,建立一個新中國唯一堅實的基礎就是民族傳統中的精華部分。其立場集中表現在哲學、政治和教育上的理想主義及文學中的古典主義。梅光迪明確指出,《學衡》的「立足點是儒家學說」13。這和胡適等新文化的激進派要「打孔家店」的行為是公然的敵對。 作為文人的中國人文主義運動的領導者,和美國的人文主義者一樣,他們十分注重道德基礎和文學的重要性,將其視為一種表達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他們成了中國文學古典派的擁護者,強烈地反對胡適等「文學革命」者所推崇的偏激思想和傾向。同時,梅光迪也不得不承認,他們的實際作用和影響是很小的。但他借用並認同《學衡》同人樓光來對他們所做的工作的基本估價,即《學衡》「批判了地方主義運動的泛濫及沽名釣譽之人惡行猖獗,為道德等諸方面的健康發展起到了補充和糾錯的作用」14。... 現實的取向 梅光迪的教學生涯主要是在東南大學、哈佛大學和浙江大學。其中,在哈佛大學是主講漢語。在東南大學和浙江大學是講西洋文學。他的人文主義理想主要體現在向學生傳授知識上。為東南大學的西洋文學系(由他創辦,並任主任)和浙江大學的外文系(任文學院院長),他付出最多。他的同事張君川回憶說:「梅先生自己學貫中西,也要求學生在努力研究西方文學外,不能忘記祖國豐富文學。他與吳宓老師素來提倡比較文學。如吳宓師在清華開有中西詩之比較一課,梅先生講課常中西對比,不只使學生加深理解,實開比較文學之先聲。」15 梅光迪由反對白話文,到「降格」16偶爾寫白話文,是經歷了一個轉變過程。因為中小學生教育都改用白話文了。為自己的子女教育,他不能不寫白話文。「他與自己的女兒通信時,總是用生動的白話文來表達自己的父女之情」17。 已為人父,且在美國受過教育的梅光迪,是孩子教育的實際狀況改變了自己自己對白話文的態度。白話文進入教育系統和孩子們輕鬆學習所帶來的喜悅,胡適在給朋友的信中有明確的表示。他說:「我看著長子讀《兒童周刊》和《小朋友》(給小孩看的故事書),我不能不感到一種快慰。畢竟我們用口語來代替文言死文字的努力沒有白費;我們至少已經成功的使千千萬萬下一代的孩子能活得輕鬆一些。」18梅光迪看到自己的孩子利用白話文的工具輕鬆的學習,一定和胡適有同樣的喜悅。.... | 

 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