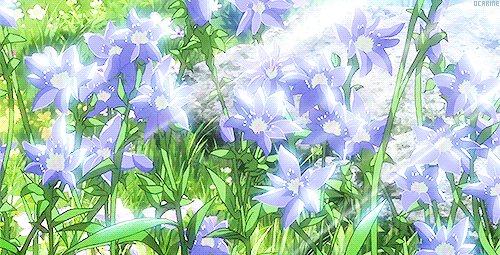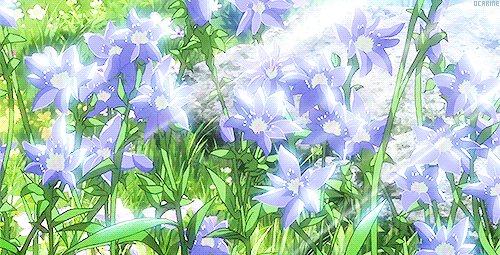
前言:地質高級工程師、作家張慶豫先生是我好友。此篇《送君上九霄》是張慶豫先生為祭朋友魏民逝世而作。張慶豫、魏民、以及文中提到的康平,都是作家、詩人;尤其在我的生活和工作圈子裡,他們是有名氣的文人、詩人。讀罷張慶豫為老友魏民而寫的這篇深情祭文,我很感動,徵得張慶豫先生同意後,轉登在我的空間裡,也是為了祭奠逝者和寄托我的哀思吧!
《送君上九霄 》張慶豫
老友魏民走了。不論我怎樣不情願不相信,列舉怎樣的理由說明他如何康健,魏民他還是走了。
9月16日晚,魏民夫人劉玉蘭同志,從武漢打來電話:“慶豫,我是玉蘭,告訴你一個壞消息……”先是右腦大面積梗塞,度過危險期後,二番住院再行康復期間並發了肺炎,9月13日闔然辭世。一位鐵塔般的大男人就此去了,享年78歲。
1954年秋初,魏民與我相識於宣化地質學校116班,同學三載,少年意氣;1957年天各一方,書來信往。至今算來60個春秋,一個甲子,歲月稠!太多的往事,太多的牽掛,太多的陰晴圓缺風和雨,被這天降的噩耗驟然定格在一個毫無思想準備的陌生時間點;萬般心緒激越,一汪堰塞湖水!接罷電話,我在喧鬧盡退的靜止裡枯坐,無言無淚。老伴兒勸慰:別太難過。
1993年,河北地質學院(前身即宣化地校)40周年慶,出版了一本《校友風采》的書,內有魏民《三人行》篇。文末寫道:“三人行,唯我腳步過慢,不過我感到欣慰的是,有慶豫和康平伴我同行。”他是謙指文學。我們三人都喜歡文學,也都投稿,還“吃稿費”,但最早登臨文壇的不是我,是魏民康平合著的組詩《我們的腳印》。此作發表於《河北文藝》1955年第10期,“一炮打響”,兩位年輕的作者結伴而行,出席了在保定召開的河北省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這件事很不簡單。畢業後,康平去了雲南,我四川,魏民湖北。魏民他是水文地質工程地質專業,長年奔波於漢江中上游,參加過4座大中型水電站的地質勘察工作。爾後奉調從政,宣傳幹事,黨委秘書,1984年出任湖北省地質學校黨委書記,正處職。
我和魏民再次見面,是22年後的1979年。其時我已調甘肅,和兩位同事去江西某鐵礦考察取經,路經武漢。魏民得信後從學校(沙市)趕來,相見於湖北省地質局資料室。1957年分手時,我19,他20,都還是孩子;22年後添愁增歲滿目風塵,面對面似曾相識,一時語塞。回蘭州後,我寫下一首小詩,紀念那次不同尋常的聚首。原詩如下:
寄贈好友魏民
(1979年2月28日午後,與魏民分手22年重會於漢口。心潮湧動不能自己,遂得小詩一首寄贈老友。)
葡萄未熟酒嫌酸,對樽一別廿二年。
川鄂千阻遙相望,樊城咫尺空作返。
武漢幸會疑是夢,楚天促膝唯恨短。
敬君坦蕩復厚重,長江黃河氣相連。
此處需作些許解釋:一是宣化的葡萄名氣很大,康平散文《母校之戀》,開篇道:“提起母校,首先想到的是葡萄。”我和魏民分手是陽歷4月,塞上春寒,葡萄還在夢裡,故有首句;二是“樊城咫尺空作返”,則另有故事在。
1959年,我於工作之餘,請假回京陪母親作眼手術。返程至武漢時想念魏民,便棄船乘車,繞道襄陽、樊城,逆漢江上行。當時魏民在湖北鄖縣工作。車至黃龍鎮,雨毀路面不能繼續。雨聲裡我在郵電所接通了長途電話,想請他到這邊來;我聽見魏民那久違的似真似幻的聲音,斷斷續續,時有語塞,為難得很。我感受到他巨大的激動與無奈。後來得知,我倆僅隔一座山,直距50公裡。20年後寫此詩,我把“空作返”的黃龍鎮誤寫為樊城了。許多年後,魏民依然自怨自責得很,專題寫過兩首詩,憶我“空作返”那日,他通宿未眠,隆隆的汽車輪聲從他頭頂一遍遍壓過,壓過。實則不能怪他。那是什麼年月呀!當初我“空作返”回到本單位,滿院大字報,“反右傾”運動正急。我生來是個跟著情緒走至死“不成熟”的人,而有序的人類社會更需要理性。熱火朝天的“大辦鋼鐵”就吃了這樣的虧。……到了食不果腹的1961年,抽著爛菜葉子過煙癮的我,突然收到個足有兩斤重的大郵包,竟是魏民寄來的黃金葉!那成色,那味道,堪稱金不換。
1986年始,我們相聚日漸增多,這得益於文學。我之於文學,只是喜歡,形同別人之麻將、釣魚、下棋,並無深意。魏民不論為民為官,也不曾中斷過文學創作,詩歌、小說、散文、劇本……散見於《河北文藝》、《蜜蜂》、《河北日報》、《天津日報》、《湖北日報》、《山野文學》、《芳草》等報刊雜志,獲獎作品甚多。我們都屬於“地質人寫地質”一類,便有幸被列入中國地質作家協會的首屆理事會名單,如此,見面機會就比較多了。魏民在《三人行》開篇寫道:“我的影集裡,珍藏著幾幅張慶豫、康平和我的合影,都是在幾次地礦部系統有關文學創作的會議期間拍的(也只有這種場合我們才能歡聚幾日)。每每看到這些照片,總使我想到三個人40年的真摯友情。”
現在,距離魏民寫那篇文章又過去20年。20年說短也短,說長也長,物非人亦非,就是遙遠的太陽也肯定有了改變,只是它太過偉大,我們看不見罷了。於是我突發奇想:人哪,人!你是真傻還是裝傻呀?放著有限的生命不加珍惜,今天敘利亞,明日烏克蘭,就不怕太陽掉下來嗎?我是指核戰。
2014年3月21日,太陽還在天上,我的電腦硬盤卻不幸崩潰了。送修兩家,未能“恢復數據”。眾多影音資料和文稿,包括魏民20多首極好的詩作,統統化作虛無。
進入晚年,魏民詩興大發,七言律詩居多。他不用電腦,只用手機,把洶湧澎湃之情從沿海發來,從南京發來,荊州發來。為了長期保存,我把它們逐一敲進硬盤,專設一文件夾:魏民詩輯。如果我不下這番功夫,任其留手機上,該多好呀!9月17日,我懷著僥幸之心,在災後的廢墟裡細細探尋。老天有眼,竟被我意外地找到一首逃過此劫的孤篇,未署日期,也非魏詩上乘之品,卻也珍貴得緊。躬錄如下:
桂樹林邊百花開,無言春歌勝天籟。
且看和風撫桃李,常念春雨育英才。
三尺講台展風采,六部著作始登陔。
句句寒暑星月鑄,行行皆為學智栽。
--賀天真天無新著同時出版
魏民夫婦育有三子,個頂個出息。詩中天無是次子,天真系兒媳,他二人同學相戀,名相近,又都姓魏,真是個美麗的巧合!天無天真夫婦,皆執教於母校華中師大,專攻文學理論和教學研究,碩果累累。寫到此處,我已望見九天之上的魏民了,聽見他“呵呵”的笑聲了!
飛吧,魏民,我永遠的朋友! 2014-9-18夜
--(此文原載2014年9月26日《甘肅地質礦產報》副刊)


 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