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徐政璿/綜合報導
日本在二次大戰戰敗後,發展不算順利,前總統李登輝在新書《新.台灣的主張》中,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廉價的台灣米輸入到日本,使日本農民生活變得困苦,將國內矛盾的解決方案轉向大陸外求,這就是近代日本失敗的原因。
李登輝透過新書回憶,在磯永吉與末永仁兩位日本農業技術人員的努力下,大正末期台灣成功種植出蓬萊米,但是結果卻是,廉價的台灣米輸入到日本,使日本農民生活變得困苦,於是貧困農民販賣女兒的情形層出不窮。
也因此接著,出身農家、對貧富差距感到不滿的青年軍官,在日本發動了「五.一五」和「二.二六」事件。李登輝表示,若他是當時的領導者,會首先從改革農村著手,但日本卻將國內矛盾的解決方案轉向大陸外求,這就是近代日本失敗的原因。
台灣米為什麼要輸入到日本 ? 台灣人自己都不夠吃了
台灣的農村窮到要吃蕃薯籤, 多少台灣農民窮要賣女兒 李登輝知道嗎
李登輝有關心台灣沒飯吃的乞丐嗎 ? 台灣米要去餵日本人, 卻不給自人吃. 說的過去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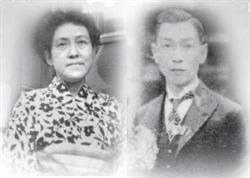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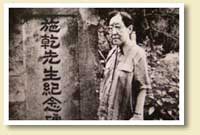

施乾
施乾(1899年-1944年),台灣日治時期台北縣滬尾辨務署(今淡水區)人,為愛愛寮(今台北市私立愛愛院)的創辦人。台北工業學校(今台北科技大學)土木建築科畢業後,在台灣總督府上班,因為在萬華看見乞丐的慘狀,於是在1922年創辦愛愛寮,協助乞丐謀生。後來日本籍妻子清水照子(1909-2002)有感於施乾的愛心,遠渡重洋嫁施予乾。施乾不幸因腦溢血早逝,清水照子與其家人繼續在愛愛寮照顧孤苦無依大眾,精神非常令人敬佩。
------------------------------------------------------------------------------
臺北淡水人。1911年自滬尾公學校畢業,翌年考入臺北州立工業學校,1917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隨即進入臺灣總督府商工課擔任技士。在職中因調查艋舺貧民的生活狀態,對乞丐產生惻隱之心,便自掏腰包醫治患病的乞丐,並教導其子女讀書。1922年辭去總督府的工作,在臺北市艋舺區綠町購地,創建「愛愛寮」,作為乞丐救濟收容所。1925年出版《乞食撲滅論》、《乞丐社會的生活》二書,贏得日本作家菊池寬的感佩,自臺返日後到處宣揚其悲天憫人的作為。1927年日本裕仁天皇邀請他參加登基大典,並由宮內省頒發獎金,從此每年支領1,000補貼愛愛寮。1933年成立財團法人「愛愛救濟院」,財政稍見安定,其夫人謝惜女士卻已積勞成疾過世,1934年續絃京都二高女畢業的清水照子(施照子)。1944年因戰爭致使全臺物資匱乏,施乾四處張羅,但經常只能以蕃薯籤與院民果腹,此時清水照子突然失聰,而為院務奔波的施乾也為高血壓所苦,終因腦溢血逝世,其志業由施照子繼承。
----------------------------------------------------------------------
二十世紀的今天,我們以生命作賭注呼籲乞丐救濟,是堅信只有站在人類愛,人道的立場才能指望問題的解決。只有愛可憐人之心,愛敵人之心,才能指望真正的天下泰平。--施乾
1923年(大正12年),一位24歲的台灣青年——施乾,放棄了令人稱羨的台灣總督府職務,以及大好前程,毅然投入台灣的乞丐救助事業,有別於以往的「施捨」觀念,施乾以「協助乞丐回歸正常社會」為出發,創辦了「愛愛寮」(今愛愛院前身)。
這樣的思維在當時代的台灣,是一項破天荒的行為,施乾受到台灣各界人士的支持與鼓勵,卻也多次承受了現實的經濟壓力。雖然施乾不幸在1944年因病去逝,但其所留下的,卻是對社會、對人類的貴重資產。在愛愛寮創立即將屆滿九十週年的今天,希望透過本書,讓我們再次思考我們所忽略的世界。
-------------------------------------------------------------------
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愛愛院
1923年由創辦人施乾先生於台北市萬華成立愛愛寮開始,原本以收容乞丐為主,戰後隨著台灣社會的進步繁榮,功能也隨之調整。近年來,機構外觀從木造院舍到鋼筋水泥的結構;從傳統家庭式的照顧模式到現代化經營;從獨自救貧濟苦的扶助到專業團隊服務輸送,在在將施乾先生的思與為,內化為每位工作人員的服務態度。
2012年的愛愛院,住民人數210人,男性110人、女性100人,平均年齡82歲,中低收入戶長者比例33.8%,而接受該院愛心扶助之比例為59%,住民50%持有身心障礙手冊,18%之住民入住該院長達10年以上。所有住民由一群跨專業之工作團隊成員,提供全程、全隊、全人、全家的照顧。愛愛院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作為宗旨,除了外部法規的要求外,更秉持愛心耐心的照顧與服務。服務對象除了院內長輩外,也擴展到外部獨居長輩,以多元化活動陪伴、照顧有需求的長輩。
愛愛院的價值已不僅只是為照顧長輩而努力,家屬的感受及員工的投入,儼然成為機構的社會價值。曾有萬餘名住民及家屬、工作人員是這片土地的過客,但每個人都為愛愛院寫下歷史,愛愛院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在施乾先生思與為的引領下,將永無句點的傳承。
-----------------------------------------------------------------------
吳理真撰 《台灣教會公報》2526期 2000年7月30日 p.9
社會救濟事業,多半是由宗教團體發起。廿世紀最偉大的仁愛典範之一的德蕾莎修女,以及慈濟的創始人證嚴法師,都是某宗教的修行人,她們實踐大愛的動力,多來自於信仰的體會。但是距今77年前,台灣就有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在沒有任何宗教背景的支持下,憑個人的力量建立了「愛愛寮」,收容流落街頭的乞丐,教導他們生活技能。淡水人施乾,一位理想主義者,不管在什麼時代,都是奇特的存在。而他的日籍妻子在他身故後承其遺志,繼續經營愛愛寮(後來改為收容孤苦無依老人的愛愛院),多年來已成為傳頌台灣、日本的「愛的傳奇」。
偉大的社會良心─施乾
施乾,1899年出生於淡水,家族薄有資產。他以相當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台北工業學校,進入台灣總督府商工課任職。在日本統治台灣初期,以台灣人的身分進入總督府任職,是相當不容易的事,他原本可以當個衣食無慮的公務員,結交權貴擺派頭的紳士。但是他卻選擇了一條非常不一樣的道路。
在一次奉派調查艋舺地區貧戶之時,施乾發現當地乞丐甚多,甚至好幾代都靠乞食維生,情況相當悲慘。古道熱腸的他決心要從根本來改善這些人的生活,著手開始把乞丐找來教導讀書識字、學習生活技能。1923年,施乾辭去人人羨慕、待遇優渥的公職,變賣家產,在今天的大理街搭建房舍,設立了「愛愛寮」。
據說當時施乾時常拖著拖車,到處尋找乞丐、鴉片癮者、精神病患和痲瘋病患等被社會遺棄的人,帶到「愛愛寮」來收容。愛愛寮像個大家庭,施乾及妻兒都和他們生活在一起;也像個學校,幫助乞丐重建生活。他對這些人很關心,也很嚴厲,急切地希望改變他們的生活習慣,讓他們成為社會有用的人。他的女兒回憶起爸爸時,常以「雷公性」來形容他的脾氣,熱情而急躁的性情可見一斑。
親身與乞丐一起生活,關心他們,也觀察他們。施乾寫成《乞食的社會生活》、《乞食撲滅論》等書,大聲疾呼請社會大眾關心注意,一起來讓社會不再有乞丐存在。他認為產生乞丐的原因,一方面是社會經濟競爭造成有人被犧牲,一方面是個人不願向上或沒有機會向上。於是他教導乞丐生活技能、學習識字,並收容被社會遺棄、沒有辦法照顧自己的可憐人,並呼籲政府也要出來做。
施乾的事蹟在當時相當轟動,總督府多次表揚,連日本天皇都在1929年「御下賜金」。但是這些支持,並不足以讓愛愛寮無後顧之憂。
「愛愛寮」的經費,最早是靠施家的家產(施乾勸說他父親賣掉一棟洋房讓他辦愛愛院),以及一些支持者的認捐,加上院民種菜、養豬及做手工的收入,勉強維持。有時也有官方的補貼或其他公益團體的撥款相助。直到現在,愛愛院都沒有一筆基金、或是固定的產業收入。維持這個人道主義的理想事業,其實相當艱苦。
日本小姐成了台灣乞丐母
1934年,喪偶的施乾在京都再婚,對象是當地富商清水家的長女、24歲的清水照子。兩人的婚姻,使這位高等女學校畢業的日本名門閨秀,成了「台灣乞丐母」。照子女士婚後來到陌生的台灣,身心所受的衝擊都相當大,何況又要面對奇特的乞丐寮生活。她努力適應,關心這些被社會所棄的人,不畏其身上的怪味與爛瘡,為他們洗澡、清潔,餵他們吃飯,很快贏得院民的信任與感激。
1937年台灣進入「戰時體制」後,物質匱乏,愛愛寮這樣的慈善事業更加困難維持,施乾先生必須時常出外募款、籌錢,或協助公家的事情,照子女士就得負起照顧全院的責任。就在戰爭結束前的1944年,積勞成疾的施乾去世了,年僅45歲,留下6名子女,照子女士必須辛苦地維持一家人與愛愛院百多位院民的生活。
戰後接收台灣的國民政府,對愛愛寮沒有興趣,任其自生自滅。照子女士考慮回日本,然而不忍心看一百多個院民重新成為乞丐,最後終於決心歸化為台灣人,繼續施乾的志業。如今,照子女士高齡90,身體健康,仍關心愛愛院的事務。她的事蹟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人報導,日本、台灣多年來也有不少要褒獎她的計劃,但是她對所有的褒獎向來都婉謝。對講究公關行銷的現代慈善事業而言,受獎對提高知名度、爭取支持是很有幫助的,尤其對愛愛院這樣缺乏龐大財力的機構。但是照子女士基於日本女性的謙卑,及基督徒「左手所做的事不讓右手知道」的精神,始終堅持著不接受表揚。這樣的態度,如同施乾當年創辦愛愛寮類似,都是濁世清流、非常難得的行徑。
你的杖你的杆安慰我
照子女士在戰後困頓的局面中,找到支撐她的一股重要力量:她認識了耶穌基督。信主以後,她熱心參加聚會,並向院民傳福音。每天在愛愛院裡,也有小型的聚會。在愛愛院,常可聽到她以不甚標準的北京話慢慢地說:「耶穌愛你!神祝福你!」
國民政府把愛愛寮改名為愛愛院,並安排愛愛院收容孤苦無依的老人,這些老人多是戰後隨中國政府來台灣的平民,沒有家人,也沒有榮民身分的福利,許多是纏綿病榻、身心障礙者,而且因長期處於社會邊緣,有些對人充滿敵意。幫助乞丐起碼可以從有些努力改進自己條件者身上獲得成就感,但是照顧這些「南腔北調人」,往往付出關心之後,不但得不到感激,還會被抱怨指責一番,照子女士及其家人這些年來的付出,其中的辛苦實在不是外人所能了解的!
照子女士因為有了虔誠的信仰,更懂得「愛」的意義,順服上帝的旨意,日日實踐「愛」而活得精神奕奕。她深知安穩在主懷中的滋味,將一切交託給上帝,始終保持單純善良的天性,在漫長的歲月中,不曾失落信心。而基督教的教導,也讓她更加謙卑、克己。
施乾雖然不是基督徒,但是從他的行徑看得出日本的基督教思想家賀川豐彥的影子。照子女士成為基督徒,宗教信仰成為支撐她繼續愛愛院工作的力量。而他們的四女兒施香,則成了一位牧師娘。「愛愛」傳奇,有上帝奇妙的作為。
讓愛愛的精神繼續傳承
國民政府來台灣之後,愛愛寮的名稱幾經變動,現在改稱為「台北市私立愛愛院」,多年來由施照子女士擔任院長,最近已正式成立財團法人。隨著社會變遷,愛愛院收容的對象從乞丐變成孤苦無依的老人,其中大半是戰後來台、沒有榮民身分的外省人。除了部分政府補助款之外,愛愛院仍然要靠外界的捐款才能維持。目前愛愛院的業務包括:安老所、養護所,還有自費安養中心。收容人數約兩百人。
愛愛寮的設立比慈濟要早半個世紀以上,其用心之偉大並不下於慈濟。但是愛愛寮從施乾的時代開始,就沒有想過要做「媒體公關」,或是自我宣傳。最早愛愛寮的事蹟廣為人知,據說是因為日本名作家菊池寬在艋舺看不到乞丐、大為困惑,一打聽才知道施乾的愛愛寮,於是回日本寫文章宣傳此事,才引起日本天皇的注意。但是即使如此,之後愛愛寮還是不懂得做宣傳。因為缺乏強有力的經濟支持,多年來,愛愛院在經營上時常面臨困境。為了讓施乾的人道主義在新世紀的台灣繼續發揚光大,為了讓愛愛寮的傳奇不致成為絕響,盼望您出一點力,一起來續成。
------------------------------------------------------------------------------------------------------
按:施照子1909 年3月30日生,, 2002年12月9日去世,享年93歲。
------------------------------------------------------------------------------------
施乾與照子 在愛愛寮行出恩慈
作者 / 風竹
101102_照子與施乾.jpg
2011年盧俊義牧師在台美聖荷西長老教會的靈修會,提到他教會的兒童夏季學校幾年來介紹了一系列對台灣有貢獻的人物,其中施乾先生是阮教會施敏娜姊的父親。聽完後我大感興趣,於是詢問敏娜姊有關她父親的故事,她給我2本介紹她父親的書以及幾篇報紙、雜誌的報導。讀完這些文獻後,讓我對施乾先生及其夫人照子女士有初淺的認識,並對他們為弱勢族群乞丐所做的大感敬佩。
■不計代價成立愛愛寮
施乾先生生於1899年,淡水人,畢業於台北工業學校(台北工專前身)土木建築科。畢業後工作時,在一次「細民」調查中發現台北的乞丐繁多,更看到一家三代都以行乞維生的悲慘現象,他的惻隱之心油然升起。施乾覺得他們很可憐,常常在下班以後買東西給他們吃,教他們識字,與他們聊天做朋友,聆聽每個人的悲慘人生境遇,就如同左拉所言:「天下幸福的事都大小雷同,但悲慘的故事卻千言萬語道不盡。」
為了能更深入地照顧乞丐,施乾不顧家人強烈反對, 辭去總督府職務,變賣全部家產,在1922年興建「愛愛寮」,做為乞丐救濟收容所,供他們食、衣與住宿, 一切免費。他親自為乞丐洗刷污黑的身體、理髮、捉蝨、資助病者就醫;除了照顧他們三餐與生活起居外, 施乾並教育他們或送他們的小孩去上學,改變他們的不良生活習慣,教他們種菜、養豬、製作豆腐、編草帽及各種手工技藝,讓他們用雙手養活自己,可以活得有尊嚴。
施乾在著作《乞丐撲滅論》裡闡述他的理想:「我願自始至終以如此熱情勇往邁進……我深知利己之極必將變成利他,利他的徹底將成為利己之理……只有如此,所有貧民、乞丐將被溫暖的手所救濟……在我們面前將展現從黑暗的、絕望的、不可有的社會,轉移到更光明、更有希望、可有的社會。」為何取名為「愛愛寮」?林金田著的書裡陳述:「原來那時乞丐,他們聚集的地方民間俗稱『鴨仔寮』,施乾的『愛愛寮』在台語的諧音上與『鴨仔寮』一樣,卻有更深一層含意,他希望大家能更愛自己也愛別人。」
■不平凡的先驅者
身為社工的我對施乾先生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作為有很深的感觸。是什麼樣的憨人會辭去令人羨慕的金飯碗,去照顧眾人唾棄、捧著破飯碗的社會寄生蟲?是多麼深度的執著與豪邁熱情讓施乾可以不顧家人的反對聲浪,一磚一瓦地興建收容所給他們一席棲身之處?是如何悲天憫人的胸懷,讓他在24歲這黃金年華「撩落去」拯救乞丐,做他們的心靈導師,帶給他們光明?有句話說「平凡人不會創造歷史」,唯有不平凡的人能夠看見異象,施乾便是這樣不平凡的先驅者。有人將施乾這位「乞丐之父」譽為「東方史懷哲」;盧俊義牧師則將其媲美於在印度照顧痲瘋病患的德蕾莎修女。不是基督徒的施乾先生活出了馬太福音25章35~ 36節所說:「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流落異鄉,你們接待我到你們家裡;我赤著身體,你們給我穿;我害病,你們照顧我。」
施乾的元配謝惜身體一直都不好,無生育,他們領養了2個女兒,而後謝惜在愛愛寮因勞瘁過度而死。元配過世後,施乾在堂妹的介紹下認識了日本女子清水照子,京都人,家境富裕,是一位千金大小姐。經過一段時日交往,照子小姐深為施乾悲天憫人的崇高胸懷吸引,不顧家人強烈反對,離開日本與施乾締結連理,那年(1934年)照子24歲、施乾35歲。
婚後他們育有3女1男(敏娜、施香、愛鄉、武靖)。照子嫁到台灣後,放下千金小姐的身段,化浪漫愛情為力量,與施乾一起管理愛愛寮,照顧院民,成為艋舺居民口中的「乞丐之母」。
然而,施乾在1944年(時年46歲),因突發腦溢血而與世長辭。照子在35歲成為寡婦,最大的女兒敏娜那時9歲,最小的兒子武靖才3歲,又有近200名的院民加上員工等待她扛起重擔,繼續經營愛愛寮(後改名為「愛愛救濟院」)。那時正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物資、食物、捐款都極缺乏,照子曾想帶著孩子們回京都與父母同住,院民一直懇求她,她也放不下,最後選擇留下來,歸化為台灣人,承繼施乾未竟的理想與志業。照子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她說:「我只是平凡的弱女子, 都是靠主耶穌的愛與恩賜,才能持續事業至今。所以我日夜學習主的犧牲精神,忍耐到底,以求無愧於心而已。」照子於2002年以93歲高齡去世,愛愛院由么兒武靖續任院長,提供給自費或公費的老人安養餘生。
■倚靠耶穌的照子
我去採訪施敏娜姊,70多歲的她含著淚水娓娓談著父親的「無私、有愛心」。至於母親,敏娜姊形容她是一個非常低調又重禮節的人,待人親切和藹,很有耐心。她覺得母親很可憐,年紀輕輕就守寡,又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時窮到吃豆籤或地瓜稀飯配鹽吃,也必須把4個小孩送到新店暫時給別人照顧,自己則留在愛愛寮張羅200多人的飲食及日常起居,但她無怨無悔,「靠主耶穌與大家的幫忙」是母親常講的一句話,就這樣打理愛愛院裡裡外外60餘年,直到她辭世。
敏娜姊說母親深得大家的尊敬,台北市歷任的市長如高玉樹、李登輝、陳水扁都很尊敬與疼惜她,尤其是李登輝先生,常去看她;也有大企業家如養樂多大老闆,常常帶5、600罐養樂多請院民喝,也常常捐款贊助愛愛院。她形容母親極具愛心,有話直說不拐彎抹角,脾氣好,人緣極佳,很關心院內的老人, 常常拄著柺杖到各個房間探望老人,噓寒問暖,老人都很喜歡她。
看完有關施乾與照子的文獻,又採訪到他們的掌上明珠敏娜姊的第一手資料,讓我內心很激動。我從事過心理諮商,覺得改變一個人的生活習慣與個性就如同移山般困難,但施乾先生做到了;我也輔導過很多靠政府救濟金生活的家庭,單親父母往往無心思考小孩的教育問題,因此一代又一代領著微薄救濟金生活,無法打破惡性循環,讓那時的我總是感到很心痛也很無奈。
平凡的我只能踩著前人的腳蹤做社會關懷工作, 所以我非常欽佩那些從無到有、創造歷史的先驅者。在那個大環境很貧乏的「民國前」時代,施乾先生不只免費提供吃住,更改變他們的習慣,終止了三代行乞的悲慘。
看著施乾的故事,讓我重新思考還能為目前服務的弱勢團體──發展障礙人士(the developmentally disabled)做些什麼?我能創造什麼工作機會給他們, 讓他們自力更生,甚至貢獻一己之力給社會?人只能活一遭,我常思索極其平凡的我要過怎樣的人生,要如何做才能使自己對周遭發揮些微影響力。施乾先生雖然只活了短暫的46年,但他如同蠟炬般燃燒自己,照亮了乞丐們的人生。我已經將近半百了,不知人生旅途還有多少年可以走,思考自己能再做什麼,才不會在見主面的時候汗顏。
註:《台灣先賢先烈專輯──施乾傳》、《為鄉里人傑塑像第三輯》。
文章及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160期
-------------------------------------------------------
與施乾一起打造「愛愛寮」的清水照子
整理/廖怡君
編按:「有你真好」曾介紹過台灣人道主義的先驅──施乾。今天,我們為大家介紹施乾的好牽手──清水照子,一個原本在日本過著優渥生活的小姐,遠渡來台,跟施乾一起打造台灣的乞丐之家。
民國28年7月14日,施乾與施照子於婚後第五年與兩女和奶母合影
1920年代,傳奇人物施乾以他個人的力量,在台北萬華創辦了乞丐收容所「愛愛寮」,希望透過關懷與教育,使台灣的乞丐絕跡。他的太太,日本京都來的清水照子,1934年,以認識這位有偉大心靈的人物為榮,遠嫁來台。
「愛愛寮」,依照子原來的想法,應該是一所像學校般有紀律又整潔的乞丐收容所,平日聚集從事各種生產事業,閒暇時穿起漂亮的制服打棒球。然而,當出身富裕的照子來台才發現,「愛愛寮」並非一幢整潔美麗的建築,而是在荒郊野外竹林中,以相當克難的方式搭建的棚子。施乾和他的母親、兩位養女所住的房子並沒有比乞丐們住的好多少。施乾的主張是,要幫助乞丐,本身就應該過跟他們同水準的生活。
院長施照子召開愛愛院生活檢討會
當時已經經營十年的「愛愛寮」資源仍然相當不足,要養活近百位乞丐,是個恐怖的重擔。施乾整天忙個不停,他對乞丐雖然和顏悅色,但是本性非常急躁而被稱為「雷公性」的他,對自己的妻子和女兒相當缺乏耐性,要求也很高,加上照子耳朵有點重聽,他經常提高嗓門對她吼,她不免感到委屈。
剛收容進來的乞丐,經常滿身跳蚤,全身是傷,髒臭不堪,而且大部分都不願接受別人的照顧,她必須想辦法為他們洗澡、施藥、剪指甲、抓蝨子。有時她還會遇到嗎啡中毒者毒癮發作時的暴力威脅,還天天聽著關在小房間鐵欄內的精神病患吼叫。結婚初期,她常常沿著鐵軌走呀走,渴望坐上火車就可以回家,然而家卻在海的另一邊!個性倔強的她,只能找個沒有人看到的地方痛哭一番。
施照子立於施乾先生紀念碑前
不過,丈夫堅持理想、身體力行去照顧乞丐,這樣的行徑仍然感動著她,讓她咬緊牙關撐下去,即使 1944年先生因腦溢血突然去世,她仍繼承亡夫遺志,主持了後來改名為「愛愛救濟院」的「愛愛寮」長達五十多年,因為她將生活上的所有重擔全卸給了主耶穌。1950年代,宣教師孫理蓮感受到照子的重擔和憂傷,協助她得到美援物質,並傳耶穌的信息給她。她的信仰單純而堅定,每天一早起來就是讀經、禱告,在愛愛院,常可聽到她以不甚標準的華語慢慢地向院民說:「耶穌愛你!上帝祝福你!」
(本文取材自新使者雜誌第78期)
-------------------------------------------------------
施乾先生是淡水先賢中最特立獨行者,也是最能彰顯台灣之人格 光輝者。1922年,他才24歲且甫新婚,竟毅然決然放棄世人艷羨的職 位與優渥的薪水,創設乞丐救濟收容所,投入永無止盡的慈善事業。 若非具備無上的悲憫胸懷和莫大的勇氣,誰能與之!
施乾,1899年誕生於滬尾米市街(今清水街146號),1912年自 滬尾公學校畢業後,考進台籍子弟極難踏進門檻的台北州工業學校。 1917年以優異成績畢業,不久為日本總督府商工課延聘為技士。在職 中因曾調查艋舺的貧民生活狀態,看見殖民統治下困苦無依的乞丐同 胞的生活,油然生起惻隱之心,便自掏腰包醫治患病的乞丐並教導其 兒女讀書。為了幫助更多的乞丐,於是轉託伯父施煥說服父親支助金 錢,並向施叔施坤山施合發木材行募得木材,在台北綠町(今大理街) 蓋了一座房舍,作為乞丐救濟收容所,題名曰「愛愛寮」。施乾此時 已辭去總督府的職務,全力照顧愛愛寮的乞丐及無家可歸者,並親自 為他們清潔身體、上藥、教導手工編織,又在後院空地養豬、種菜, 培養他們自給自足的能力。經費來源,只靠有限的募捐所得。最困難 的時候,施乾甚至變賣全部家產予以維持。施乾之義行,曾得日本文 豪菊池寬撰文報導而廣為日人所知,並獲日皇頒賜賞金。最令人感佩 的是,施乾元配謝氏惜女士(1932年去逝)、續絃京都小姐清水照子 ,以及施乾的子女,都隨施乾居住愛愛療,與二百多位乞丐共同生活 起居。1944年,施乾因高血壓遽發,英年早逝。照子夫人繼續秉承先 夫遺志,一直維持至今,而且施乾的大女兒、二女兒和兒媳婦也同時 在院內服務。施乾一家人的偉大風範,豈不令人擲筆讚嘆!而這也實 係施乾先生的精神感召所致。(錄自《金色淡水》)
施乾年表
1899
出生於台北縣淡水鎮。
1911
從公學校畢業
1917
以優異成績卒業,進入日本總督府商工課,成為該課的技士。
1922
在台北市艋舺區綠町購地,創建愛愛寮。
1925
印行《乞食撲滅論》、《乞丐社會的生活》二書。
1928
以貴賓身份應邀參加天皇就位大典,並獲頒宮內省賞金。
1934
在京都和日本女子清水照子結婚。
1944
以高血壓病發逝世。
施乾著作
《乞食是什麼》
《乞食撲滅論》
《乞丐社會的生活》
《丐撲滅協會—宣言 要旨 規約》
以上收錄於《孤苦人群錄》,北台灣文學13,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外婆過世後,子孫整理遺物意外發現一張日本男人的相片,才知原來那是外婆當年的未婚夫,是京都銀行家的富家公子,當時猛烈追求未擄獲外婆芳心,逃婚來台嫁給外公。」 ──洪子卿(清子照子的外孫)
日本政府在治台之初,本著人種優生學的角度,主張血統的純粹,嚴禁日本人與台灣人通婚。軍政時代(1895年8月到1896年3月31日)來台的日人全為官吏和士兵(壓倒性全為男性),僧多粥少,每每為爭奪台灣藝妓而起爭執。民政時代日本開放民間人士來台,初期渡台的日本女性幾乎都是娼婦(見《日本女人在台灣(明治篇1895-1911)》第二章,竹中信子著)。
之後日人在台定居人數增多,為了促進殖民地的經濟繁榮,並穩定台灣人民心,日本政府便將「內地法」(及日本本國國法)引進台灣,此後讓台灣人可以和日本人一起求學,同時也鼓勵台灣人參與政治事務。1933年正式頒佈「台日通婚法」,更鼓勵台灣男子與日本女性結婚。
婚姻除了愛情,向來也包含了現實的因素,比如殖民者男性與當地婦女結婚,通常為了政治招撫(如日本警察與原住民頭目結婚,有「和蕃」之意),而台籍男性想娶日本女子為妻,則多希望藉此有更好的出路。
當時著名的台籍作家龍瑛宗,在其成名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便有如此生動的描述:
「雖然也許是個虛妄的希望,但是如果有機會的話,就和內地人的姑娘戀愛並結婚吧。不是為此才頒佈內台共婚法的嗎?」
「不過要結婚,還是當對方的養子較好。戶籍上要是成為內地人,如果在官廳工作就會有六成加薪,其他各方面也都會有利益。不,不,就算把那種功利的考慮摒棄於外,如能和有著無與倫比的柔順和教養深厚,且又美麗如花的內地人姑娘結婚,把自己的壽命縮短十年或二十年,都不會埋怨的呀。然而這麼少的薪水,不是無可奈何的嗎?對,要用功,要努力,那才是解決境遇的一切吧。」
然而不管是虛妄的希望、現實的考量,政策既然開放了,就有種種的愛情發生的可能。其中富家女清水照子不顧家人反對,遠赴台灣下嫁鰥夫施乾的故事,深情更是傳為美談。
施乾於1899年在滬尾出生。父親原本服務於警界,後來轉業從商,家境相當不錯。1917年,施乾以優異成績自臺北州工業學校畢業,不久,便被日本總督府商工課聘任為技士。有一次,施乾奉派到艋舺地區貧戶時,發現到處都是乞丐。他們大都是因為貧窮、生病、殘廢、遭遇急難或吸毒等原因淪為乞丐。
這些乞丐除了吃不飽、穿不暖、住不好之外,他們還常常被歧視、欺負,甚至乞丐頭子也會欺負底下的小乞丐。而施乾最同情的就是一家三代均靠乞討維生的乞丐,這些生活在最底層的人似乎永無翻身之日,而當乞丐生病了,常常露宿街頭、無人聞問,非常淒涼。在實際接觸、了解過乞丐的困境後,施乾發現教育是讓乞丐脫離悲慘生活的好方法,於是他常利用下班時間去跟乞丐聊天,幫助生病的乞丐就醫,並教導乞丐認字。
後來,在一九二三年,他乾脆辭去公職,並說服家人支助金錢,在大理街創建「愛愛寮」,全心全意幫助乞丐改善生活。免費收容乞丐、鴉片癮者、精神病患和痲瘋病患等被社會遺棄的人,最多達兩百多人。
根據施乾的外孫,國內修飛機頂尖教官洪子卿表示:外界不知的是,當年外公為了「撲滅」乞丐,經常「捕入」院內強制收容,也就是將乞丐強行抓進院內(現今法治社會當然不容),輔導訓練學做畚箕、種菜、或至豆腐工廠學做豆漿等,至少要學得謀生一技之長才能出院。
不但如此,施乾還會為乞丐們理髮、剪指甲、捉虱子,也會親自餵食生病的乞丐,幫助他們接受治療,並替他們洗澡、洗衣。
1925年,施乾出版「乞丐撲滅論」、「乞丐社會的生活」,呼籲社會大眾發揮悲天憫人的精神,一起幫助乞丐脫離黑暗角落,這份心深深感動了許多人。1927年,日本裕仁天皇甚至邀請施乾參加其登基大典,並頒發獎金,補貼愛愛寮。然而艱苦的生活卻讓施乾的第一任妻子謝惜女士在1933年積勞成疾去世了。
不久之後,另一個傳奇的女人走入施乾的生命,她是來自日本京都富貴人家的清水照子。
當時日本文豪菊池寬來台,發現台北街頭竟看不到乞丐,對施乾收容教育乞丐做法非常敬佩,被寫文披露在日本媒體,引起廣泛注意。
清水照子看到這故事大為感動,兩人透過書信交往,1934年,照子不顧家人反對,決心嫁來台灣。
然而出身富裕的照子在結婚初期很難適應在愛愛寮的生活,一方面恐懼滿身跳蚤、骯髒不堪的乞丐們,有些人毒癮發作還會暴力威脅她。又加上施乾個性非常急躁,有時對自己的妻子和兒女相當缺乏耐性,外號「雷公」的施乾,常會對耳朵有點重聽的清水照子吼叫,讓她感到十分委屈。所以在結婚初期,據說清水照子常常沿著鐵軌走,望著火車,想念家鄉,一個人痛哭落淚。
後來,照子終於克服內心的恐懼,開使對乞丐們微笑,乞丐們也「先生娘」、「先生娘」的叫她,她並開始替乞丐們洗澡、擦藥、剪指甲、抓蝨子,也和施乾一起教乞丐們技藝和認字,還變賣身邊值錢的首飾衣服替愛愛寮度過經濟難關。
1944年,施乾因腦溢血英年早逝。隔年,日本戰敗,原本清水照子打算回日本,卻禁不住愛愛寮院民的哀求,加上也放不下丈夫照顧乞丐的理想,她決定歸化為臺灣人,改名施照子,留在臺灣繼承施乾的遺志,而「愛愛寮」後來改名為「愛愛救濟院」繼續經營下去。
2002年,92歲的施照子去世了,么兒施武靖繼任為院長,「愛愛救濟院」也改名為「臺北市私立愛愛院」,提供免費的老人安養服務,也有自費的老人安養業務。繼承施乾夫婦的遺志。
而關於清水照子,還有一段不為人知的故事。2008年12月21日施乾的外孫洪子卿接受《中國時報》的專訪表示:「外婆過世後,子孫整理遺物意外發現一張日本男人的相片,才知原來那是外婆當年的未婚夫,是京都銀行家的富家公子,當時猛烈追求未擄獲外婆芳心,逃婚來台嫁給外公。外婆生前都沒說這段往事,只把照片偷偷收藏在五斗櫃,可見外婆當時隻身來台心情之複雜,如果把這櫃子珍藏的照片回寄日本,那就有點像變調的海角七號,應該是海角九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