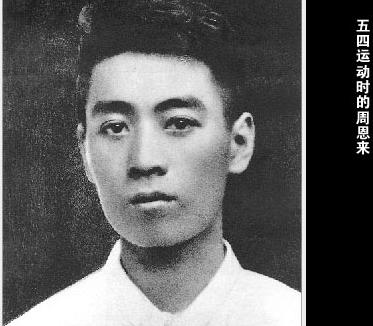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4/09/01 19:16:26瀏覽1731|回應0|推薦0 | |
毛澤東預言:我死後誰也壓不住鄧小平(圖) 文章來源: 多維 於 -
毛澤東很看重鄧小平,他曾說:“王洪文不如鄧小平”。毛澤東於1974年10月4日提議鄧小平擔任第一副總理,10月1l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近期召開四屆人大。 12月23日,周恩來抱病飛赴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情況。王洪文也到了。毛澤東再次明確表態支持鄧小平,說:“你們留在這裏談,告訴鄧小平在京主持工作。”“Politics比他強。”毛澤東指著王洪文對周恩來說。英文Politics的意思是“政治”,不懂英文的王洪文在一邊木然。毛澤東指著王洪文又說:“他沒有鄧小平強。”一邊說還一邊在紙上寫了個“強”字。 當周恩來匯報四屆人大人事安排,說到“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時,毛澤東一字一句地說:“我看小平做個軍委副主席。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 毛澤東又拿起筆來,在紙上寫了“人才難”,周恩來看懂了,說:“人才難得。” 毛澤東轉過頭來對王洪文說:“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又關照周恩來說:“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會後,你安心養病吧!國務院的工作可以讓小平同誌來頂。”周恩來點了點頭。 由此,在這重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澤東終於最後下定了決心。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1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月8日至10日,周恩來在京主持黨的十屆二中全會,討論了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增選鄧小平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在1月13日至18日召開的全國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決議周恩來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 至此,毛澤東采取“四步走”戰略,使鄧小平正式承擔起中共中央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工作。 毛澤東的預測 毛澤東在1975年時曾經對他身後的一些事情的發展做了預言,毛澤東的翻譯唐聞生在毛澤東人生的最後關頭將這些講話記錄了下來。 關於鄧小平: 毛澤東說:“小平看不起那些人,我在還可以,我死了,誰也壓不住他。他這個人對三自一包那些東西還是有感情的,對走資派恨不起來。” 當問起毛澤東同越共中央第一書記黎筍說鄧小平是少壯派是否有意傳位給鄧時,毛澤東說:“他隻要表態對文革有個基本認識,就不能動。你們這些人加起來也比不了他,他不是總理和老總,不妥協,不認輸,外麵是××殼,裏麵是鋼鐵公司。你們不了解他,我是知道的。” 關於華國鋒: 毛澤東說:“華是一個老實人,可是老實也就是沒用。他上來的好處是中間派,既不會左,也不會右,也容易被各方麵接受。不過現在還不是時候,都要看。這件事不要和江青他們講,也不要讓華知道。” 關於江青、張春橋、王洪文: 毛澤東說:“江青這個人得罪人太多,容易把人推到牆角裏去,逼得人家造**。我看我要死了她是不好辦的,人家都是敷衍她,不買她的賬嘛。我就教育她要她團結大多數,她是不會聽的。尼克鬆奉承我說我的東西改造了世界,我說就改變了北京附近的幾個地方。現在看連自己的老婆都沒有改變,還談什麽改變世界呢?她也不是一無是處,優點是反潮流,敢想敢幹。 春橋是思想家,比陳伯達強,他的特點是肯於動腦筋,弱點是經濟上不行,在軍隊裏麵也沒有威望,劍英和許世友也是看我的麵子。 王洪文當時提的快了,沒有考慮好,這是我的錯誤。此人沒有經曆過風雨,以後恐怕要補課。” 關於葉劍英: 毛澤東說:“劍英不說硬話,這點他們幾個都不行。他是大事不糊塗,小平就是小事也不糊塗,你們比得了嗎?他現在是不說話,實際已經被小平招安了。說是黨指揮槍,可是黨也要具體的人出來,否則,怎麽指揮?他這個人不看文件,文件還都不是放空炮?戚夫人說給漢高祖四句話:鴻鵠高飛,一舉千裏,羽翼已就,橫絕四海。你們知道是什麽意思嗎?” 關於身後中國的情況: 毛澤東說:“還是我的那八個字,衛星上天,紅旗落地。” 毛澤東還說:“我死了以後,是和平交班?是腥風血雨交班?”又對江青等人說:“我死了以後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 *****
晚年周恩來多疑:怕報復 怕像林彪一樣死去(圖)文章來源: 網易新媒體 於 -
確定總理患膀胱癌是1972年5月18日;實際患癌自然早於此。林彪事件對毛澤東的刺激是巨大的,對周恩來的刺激同樣是巨大的。在他們以大政治家的沉著鎮定麵對現實,有條不紊地處理這一事件,穩定局勢,安定人心之際,他們的身體和精神狀態都起了微妙的變化。向來謹慎小心的周恩來,在那段時間變得多疑;不僅是謹慎小心,甚至可以說是謹小慎微了。這方麵連專機組的同誌們也有了感覺。 (李揚評:周恩來害怕呀,怕有人報複他,讓他象林彪一樣死去。因為有人查清楚,林彪是被誰整死的了。) 林彪事件發生不到一個月,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訪問我國。10月10日,總理陪他去南方參觀訪問。 以往專機起飛,由機長向總理報告航線、時間、天氣、機況後,總理同機組同誌們握握手,問候一聲就放心地上飛機了。 這次不同。聽完報告,他不放心地問: “飛機檢查了嗎?” “都檢查過了。” “正常嗎?” “正常。” “沒發現問題?” “沒問題,都正常。” “試飛過嗎?” “試飛過。” “也檢查也試飛過了?”總理反複叮問。 “我親自檢查試飛過了。”機長張瑞靄從1954年起就為總理飛專機,從未見過總理這樣不放心。我自己跟隨總理乘飛機,何止百次,空中遇險就有過七八次,更不曾見過他這樣不放心。又問一句: “你們都是黨員嗎?” 得到肯定的回答才登上飛機。專機飛越長江時,張瑞靄報告說: “總理,要過長江了。” 總理一直在朝航線下方張望。以往遇險,都是我不放心,我緊張。我總想找機長去問個清楚,而總理都是一百二十個信任地穩坐不動。記得兩年前總理跟葉帥去河內吊唁胡誌明,專機升空不久就進入雷雨區,電光雷火映得天空一片紅,飛機像燃燒的火團一般。我不安地想去前邊提醒張瑞靄幾句,總理馬上揮手製止: “別去打攪人家,瑞靄他們會有辦法的。” 這一次卻顛倒了。飛得四平八穩,我一百二十個大放心,總理卻狐疑地朝下方望個不止。 “是過長江嗎?” 總理朝下望,朝張瑞靄凝視: “我怎麽沒看見長江呢?” (李揚評:周恩來嚇成這樣,因為心裏麵有 *呀.他注視張瑞靄的原因,是希望從這張臉上找出破綻,周恩來已經草木皆兵了.) “那裏,看到了嗎?在那兒!” 張瑞靄幫助總理找到下方寬闊的長江入海那一段,幾個人都跟著說看到了。 “瑞靄呀,這是長江嗎?” 總理臉上的狐疑之色使我也疑惑了,該不是海灣或外國的什麽河吧?總理的聲音充滿了不安: “我看不像呀!” “沒錯,總理,是長江。” 張瑞靄忙拿出地圖遞給總理: “你對照一下,現在看到的就是這一段……” 總理拿著地圖,在張瑞靄的指點下,對照半天才多少放下心地點點頭:“哦,是長江……” *****
揭秘:毛澤東阻止周恩來治療癌症始末(圖)文章來源: 多維 於 -
前九三學社中央主席,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吳階平是中南海禦醫。曾負責江青醫療保健、毛澤東遺體保護。從1968年開始,曾擔任周恩來等中共多位高級領導人的醫療小組組長。2011年3月2日吳階平病逝,3月21日出版的《三聯生活周刊》刊文《“一代國醫”吳階平》引用吳階平的原話披露,周恩來被確診患膀胱癌後,毛澤東先以“三項指示”阻止治療,後以檢查、觀察和治療要分“兩步走”為由拖延,最終使周恩來錯過最佳治療期,過早地付出了生命代價的前前後後。 文章說,1972年5月,周恩來在一次尿常規化驗中,發現紅細胞超出正常值。吳階平請來上海、天津老專家會診,確診為膀胱癌。醫療小組將治療方案報告中央後,得到的“三項指示”卻是:不檢查,不開刀,向周恩來、鄧穎超保密。醫療小組雖詳細解釋需檢查及治療的重要性及錯過治療時機可能發生的嚴重後果等等,但均無濟於事。在此期間,醫療組不斷奔走匯報請示,“甚至手持血尿瓶到許多首長家麵報問題的嚴重性,請求及早診治”,但手術的治療方案仍未被批準,醫生們隻能對總理進行保守治療。1973年1月,周恩來已經開始尿血。醫療小組拿著周恩來血尿的試管、化驗單,找到住在西山的葉劍英。幾天後,葉劍英拿著裝有周恩來血尿的試管,到遊泳池報告毛澤東。第二天,中央批準了醫療組的報告。兩個月後,周恩來終於住進玉泉山的臨時治療室,接受膀胱鏡檢查。然而就在檢查前一天,醫療組又接到指示:檢查、觀察和治療要分“兩步走”。吳階平清楚:真要分“兩步走”,很可能就永遠沒有“第二步”了。得到鄧穎超的支持後,醫療小組違背毛澤東的指示給周恩來做了手術,病情得到緩解。(編者注:2003年6月28日,本文提到的周恩來醫療小組成員之一張佐良在鳳凰衛視《魯豫有約》節目“周恩來得癌症 毛澤東為何批示不準手術”中說,毛澤東不是故意刁難周恩來,而是不相信外科醫生,擔心手術失敗,“因為主席幾次自己有病的時候,他對待病的態度也是這個樣子。”) 到了10月底,周恩來又出現血尿,癌細胞再度抬頭。吳階平和幾十位專家討論了多次,大家的結論是一致的:必須手術治療。在手術方案被批準前,周恩來需要每周輸兩次血來補充大量流失的血液。可是此時“批林批孔”運動進入高峰,一支支冷箭射向周恩來。正遭受病痛折磨的周恩來,又在精神上被煎熬、摧殘。有時他正在輸血,“革命派”通知他去開會,他隻能拔下針頭去參加。 在醫生們反複勸說下,周恩來親筆給毛澤東寫信請求做手術。幾天後,毛澤東批準了周恩來的手術請求。手術後,病情一度得到緩解。但到了1975年秋天,周恩來的膀胱癌由原來一般常見的尿路上皮細胞癌轉為鱗狀上皮細胞癌。這種癌腫惡性高,發展快。醫生們雖然竭盡全力,卻已無回天之力。 “這條鋼絲上走過的不少人都栽下去了,而使他身體保持平衡的杠杆兩端,一頭是他精湛、高超的醫術,另一頭則是他的政治敏感與審時度勢的本領。” “吳家醫院” 2004年9月的一天,協和醫學院前副院長董炳琨接到來自吳階平的電話。吳階平希望董炳琨給他寫一份生平材料,“重點要對一生做出評價”。今年88歲的董炳琨曾與吳階平一起搭檔過。董炳琨覺得這個特殊任務難度很大。“可是他說,要是不困難也就不找你了。”一個月後,吳階平把董炳琨約到自己的療養地,兩人傾心交談了幾個小時,吳階平後來還把自己寫的12篇回憶文章交給了董炳琨。吳階平的一生,由此也被清晰地被勾勒出來。 “吳家兄弟就可以開一個醫院。”吳階平兄弟4個,他排行第二,原名“泰然”,“階平”是他的號。吳氏四兄弟都就讀於協和醫科大學,除了名氣最大的吳階平之外,吳階平的大哥吳瑞萍是小兒科專家,二弟吳蔚然是普通外科專家,三弟吳安然是免疫學專家。其中吳蔚然當年與吳階平一道,是周恩來醫療小組成員,後來又成為鄧小平的保健醫生。“吳蔚然非常低調,不愛說話,其實他的水平和貢獻一點也不亞於吳階平。”曾任協和醫科大學教務長的劉世連告訴本刊記者。 吳家幾個孩子的職業完全是由父親吳敬儀主導的。吳敬儀是前清秀才,曾做過湖南候補知縣。吳敬儀有很精明的經商頭腦。辛亥革命後不久,盛宣懷要將他在湖南的10萬兩銀子轉到上海,因為當時兵荒馬亂,盛宣懷怕帶銀子被人搶走,他知道吳敬儀辦法多,便請他幫助想個穩妥辦法。吳敬儀在當地買了10萬兩銀子的美孚煤油,由水路運到上海;到了上海後油價暴漲10倍。盛宣懷喜出望外,要把賺的錢分給他一半,吳敬儀則要求替換成盛宣懷紗廠的股票。這份股票後來為吳家帶來不小的財富,也成為吳家第二代接受精英教育的物質基礎。 吳敬儀是一位標準的嚴父。他在家中辦了私塾,請當地最博學的先生教幾個孩子讀四書五經。他還經常請在紗廠工作的美國人的孩子到家裏跟自己的孩子們玩,這使得吳階平從小就會說一口標準的美式英語。吳敬儀對任何事情都認真負責,有些事情認真得甚至有些過分。他有幾塊金懷表,每天都要拿出來,與收音機裏的報時校對,準確度要求到秒。吳階平後來常說,父親對他一生影響很大。 當時社會動蕩,走南闖北的吳敬儀認為不能做官,做官會把心染黑了;也不能從商,亂世中從商隻能是傾家蕩產。在他看來,最好的選擇便是學醫。吳敬儀不知道從哪裏知道了當時剛創辦不久的協和醫學院,他便極力鼓勵幾個孩子去報考。吳階平的大姐夫陳舜名本已畢業工作,在這位嶽父的要求下也重新報考,上了協和;接著是大哥吳瑞萍。1933年,16歲吳階平考取協和醫學院在燕京大學的醫學預科班。 協和醫學院實行的是標準的精英式教育,預科3年後,還要學習5年本科,前後8年,所以能堅持下來的人並不多。一年級吳階平的同班有52人,3年後考入協和的隻有13人。剛入學的吳階平成績平平,以愛玩著稱。從三年級才開始發奮。三年級時,他被評為僅有的兩名優秀生之一,獲得免交1000銀元學雜費的獎勵。 協和每年都要舉行隆重的畢業典禮,並從四年級選一名品學兼優的學生做畢業典禮的學生司儀。儀式開始,司儀手持紀念牌和一根一尺多長的紅木棒,上麵套著一道道金箍,金箍兩麵刻著曆屆學生司儀的名字,金箍套滿了就形成一根金棒,學校將永久保存。吳階平的名字被記在第九道金箍上。1941年,協和醫院被日軍占領,這根金棒也不知所終,這是吳階平終生之憾。也是因為這一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協和停課,1942年1月學生全部撤離。吳階平這一批學生也成為老協和畢業生名錄上的最後一串名字。 “先專後紅” 從協和畢業後,吳階平來到中央醫院(又稱中和醫院,即後來的人民醫院)工作。1944年,在中央醫院擔任住院總醫師,隨後赴美進修。吳階平的導師哈金斯(Charles Huggins)是現代腫瘤內分泌治療的奠基人,曾獲得諾貝爾獎,他很賞識吳階平,想把這位高徒留在身邊當助手。但吳階平還是希望回國發展自己國家的泌尿外科。 吳階平1948年回國,作為新中國成立前夕第一批歸國的知識分子,受到新政權的極大重視。北京市政府剛成立,市長彭真邀請了一批知名科學家、教師和社會賢達參加招待會,吳階平是其中一員。 上世紀50年代,是吳階平醫學事業的巔峰期。吳階平在腎結核對側腎積水、男性絕育和腎上腺髓質增生三個方麵的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國泌尿外科界的地位。1951年,吳階平參加了北京市第二批抗美援朝誌願軍手術隊並任隊長,回國後,他遞交了入黨申請書,成了那一代知識分子中“先專後紅”的代表人物。 1962年,吳階平受命創辦北京第二醫學院,比他小一歲的馮佩之出任黨委書記。那時候的吳階平無論專業領域還是社會活動上,都已經有很高的聲譽,但他主動放低身段。馮佩之回憶,那時“二醫”經常組織學工學農,甚至去門頭溝煤礦勞動鍛煉,考慮到吳階平事務繁多,馮佩之告訴他不必參加,可是吳階平照樣跟他們去了煤礦。 與吳階平不同,馮佩之和董炳琨都屬於解放前參加革命的老幹部。被看成大知識分子的吳階平,卻處處顯示了對這些革命幹部的尊重。第一位夫人趙君愷去世後,有人向吳階平介紹了高睿,很多事情他都向董炳琨、馮佩之如實匯報。“人家名氣那麽大,還那麽坦誠地跟我講,有時我都不好意思。”董炳琨告訴本刊記者。93歲的馮佩之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更是連連感慨:“這樣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做到這一點,不容易。” 精湛的醫術,再加上政治上的積極進步,使吳階平的醫術活動範圍也越來越大,漸漸進入到為國家領導人看病、會診的醫療服務中。在普通人眼裏,這無疑是榮耀甚至權勢的象征,但身臨其境,才知道個中甘苦,甚至暗藏的巨大風險。 中共最高領導幹部的保健工作,最初是效仿蘇聯的一套體製,毛澤東對此早有意見,認為過於特殊化,脫離人民群眾,所以1964年撤銷了中央保健局,保健工作也陷於癱瘓。後來周恩來指示成立一個保健小組,由吳階平任組長,中南海門診部主任卞誌強和解放軍總醫院副院長曹根慧任副組長。 周恩來是了解吳階平的醫術、人品和能力的。他曾對別人評價說:“交給吳階平的任務都能完成得很好。”也許正因為此,周恩來把很多醫生最不願意接手的一項工作交給了吳階平——1967年11月的一天,周恩來把吳階平接到釣魚台賓館,正式交代他負責江青的保健工作。吳階平連連推說自己是泌尿外科醫生,不適合做保健工作,但在周恩來堅持下,他不好再推辭。回到家,他曾非常認真地對妻子趙君愷說:“如果哪天我不回來,你就等,耐心等到我回來,千萬千萬不要找誰去鬧。鬧於事無補,隻會壞事。” 在為江青做保健醫生的幾年裏,吳階平處處小心謹慎之餘,也運用他的智慧應對。董炳琨說,當時另一位保健醫、中南海門診部主任卞誌強每一次寫病曆都盡可能寫得很詳細,還說:“以後要真有什麽事,咱們可以有病曆為證。”吳階平淡淡地說了句:“還是少寫為妙,有三兩句,把事情說清楚就是了,寫多了也會出毛病。”吳階平的一番話讓卞誌強恍然大悟。 從1967到1973年,吳階平為江青做了近6年的保健醫生,總算安全地完成任務。當年在中南海工作的小筆記本,多年後吳階平還一直珍存著。上麵布滿了諸如CC、KS、CEL等各種“密碼”。他後來才解開了這個謎底:CC是江青,KS是康生,CEL則代表周恩來。原來這是吳階平怕萬一不小心弄丟了本子而設置的,他的謹慎和心思之縝密可見一斑。 “走鋼絲”的醫療 吳階平最被外界所知的,是他作為醫療組組長為周恩來看病的故事。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裏,吳階平需要應對的,已經遠遠超出一個醫生的職業範疇。 1972年5月19日,周恩來在一次尿常規化驗中,發現紅細胞超出正常值。吳階平從上海、天津請來老專家一同會診,確診為膀胱癌。吳階平、卞誌強、吳蔚然與張佐良4人共同向中央寫書麵緊急報告,請求中央審批做膀胱鏡檢查。 可是醫療組麵對的情況比較複雜,當時葉劍英、張春橋和汪東興三人組成“中央領導小組”,關於周總理的醫療情況,醫療組需要向“中央領導小組”匯報,“中央小組”對上向最高領袖毛澤東匯報,得到批準後才能實施醫療方案。即便周恩來本人,也不能決定自己的醫療方案。 周恩來醫療小組由吳階平任組長,方圻、吳階平的弟弟吳蔚然、吳德誠任副組長,後來醫療組擴大到50多人。關於周恩來的病情,醫生們的意見一致:一定要及早檢查、治療,必要時動手術,吳階平代表醫療組向中央寫了報告。幾天後,吳階平、卞誌強、張佐良3人在懷仁堂見到3位“中央領導小組”代表,他們說已看到了報告,並傳達了三項指示:一、不檢查;二、不開刀;三、要向周恩來、鄧穎超同誌保密。 醫療小組的卞誌強後來回憶,聽到這個指示後,大家“非常不安和焦急”,“雖詳細解釋需檢查及治療的重要性及錯過治療時機可能發生的嚴重後果等等,但均無濟於事”。在此期間,醫療組不斷奔走匯報請示,“甚至手持血尿瓶到許多首長家麵報問題的嚴重性,請求及早診治”,但手術的治療方案仍未被批準,醫生們隻能對總理進行保守治療。這一切最初都是瞞著周恩來進行的。吳階平事後回憶,周恩來對任何問題都要刨根問底,“以前無論給他做什麽檢查,他都會把檢查的原因、原理、結果問個一清二楚,可這幾次檢查之後他都沒有詢問結果,隻是一味拚命工作”。 1973年1月,卞誌強和方圻連夜找到吳階平,告訴他總理已經開始尿血。吳階平得知消息,心急如焚,他們拿著周恩來血尿的試管、化驗單,找到住在西山的葉劍英。幾天後,葉劍英拿著裝有周恩來血尿的試管,到遊泳池報告毛澤東。第二天,中央批準了醫療組的報告。 兩個月後,周恩來終於住進了玉泉山的臨時治療室,接受膀胱鏡檢查。膀胱鏡檢查並不複雜,是在局部麻醉下用來觀察膀胱內部的精密儀器,如果通過膀胱鏡檢查觀察到有早期膀胱癌的病灶,可在做檢查的同時用電灼手術器械把病灶電灼,這樣病情就能得到控製。然而就在檢查前一天,醫療組又接到指示,大意是為了慎重,做檢查、觀察和治療要分“兩步走”。吳階平心裏清楚:真要分“兩步走”,很可能就永遠沒有“第二步”了。 “怎麽辦呢?我就去找鄧大姐,我說:鄧大姐,現在毛主席說了,分兩步走。那麽我們進去看看,什麽也沒有,那也無所謂分兩步走。可是如果看見一塊小石頭,是不是順便把它拿出來就好了?還是要留著等著走‘第二步’?她說:看見那個小石頭,拿出來就算了。”鄧穎超的話讓吳階平心裏有了底,他說,“我想有鄧大姐這句話,不管怎麽著拚死拚活也得把這個點燒下來。燒下來危險是很大的,因為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可是有鄧大姐這句話,我們至少可以搪塞一陣。” 周恩來醒來之後便問情況怎麽樣。吳階平如實回答:“有一個東西,燒掉了。”周恩來毫不客氣地說:“不是讓你們分兩步走嗎?”鄧穎超趕快插話:“兩步並一步走好。”周恩來說了句:“你們該不該這樣做,還得看。”手術後,周恩來的病情得到了緩解。很快,電話裏傳來了毛澤東對醫生的肯定:“醫生們兩步並一步走做得好,感謝他們。”卞誌強後來對吳階平說:“你是帶我們走鋼絲,不但要掌握好平衡,還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 1973年4月,周恩來和鄧穎超在玉泉山與鄧小平夫婦長談,細致入微的周恩來在托付國家大事時還囑咐他們:“健康問題可找吳氏兄弟。”吳蔚然後來成為鄧小平的保健醫生。 到了10月底,周恩來又出現血尿,癌細胞再度抬頭。吳階平和幾十位專家討論了多次,大家的結論是一致的:必須手術治療。在手術方案被批準前,周恩來需要每周輸兩次血來補充大量流失的血液。可是此時“批林批孔”運動進入高峰,一支支冷箭射向周恩來。正遭受病痛折磨的周恩來,又在精神上被煎熬、摧殘。有時他正在輸血,“革命派”通知他去開會,他隻能拔下針頭去參加。 終於,在醫生們反複細致的工作下,周恩來親自提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希望能接受手術治療。幾天後,毛澤東批準了周恩來的手術請求。手術後,周恩來的病情一度得到緩解。周恩來的膀胱癌原屬一般常見的尿路上皮細胞癌,但到了1975年秋天卻轉為鱗狀上皮細胞癌。這種癌腫惡性高,發展快。醫生們雖然竭盡全力,卻已無回天之力。 1976年1月7日深夜,昏迷已久的周恩來微微睜開眼,看見守候在床邊的吳階平,清楚地說:“吳大夫,我這裏沒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們需要你……”這是周恩來一生中最後一句話。在此後的20多年裏,吳階平每提及此事都感傷不已甚至幾度哽咽:“周總理一生關心別人,就在大腦已經很少有活動能力的時候,關心的還是他人。” 可是令吳階平和醫療組成員意外的是,總理去世後,卻出現了很多指責之詞。“當時流言蜚語特別多,說什麽的都有,大意是指總理的醫療工作存在問題。醫療組成員都有很大的壓力。”董炳琨說。1月15日,借周恩來追悼會之機,鄧穎超專門把在周恩來身邊工作過的醫護人員和身邊工作人員等請到台灣廳,她對著總理的侄輩們說:“醫療組的同誌精心護理,工作非常辛苦,他們政治可靠,技術一流,他們已經盡了力了。”這樣事情才稍平息下來。 可是此事並沒有就此完全平息。在周總理去世10周年的1986年,外事部門又有一個人寫了一篇文章,對總理的醫療工作提出若幹質疑。文章稱:“中央”指定的醫療小組對恩來同誌精神和肉體給予了毫無人性的折磨,就連鄧大姐要去醫院探望都要經過王洪文和他們的醫療組的批準。文章不僅在國內刊登,而且發到國外。 “醫療工作其實是很複雜的。”董炳琨解釋說,“當時我沒有參與醫療工作,但是也間接地做了一件事。那時決定要給總理做膀胱的灌注,可是灌注治療的效果如何、有沒有病痛等,我們的經驗不太多,而上海的經驗比較多。上級就要我和一個泌尿科專家兩人一起到上海做調查。把上海各個醫院膀胱灌注的病例一個一個搜集調查。” “從這一件事情看起來,對總理做的每一個醫療措施都要經過多方論證,有具體材料才行。那時候全國上下,大家出於對總理的關心,提出的各種方子包括偏方、中醫方、西醫方多極了,但是不可能都用。使用方子得有科學根據,即便沒有科學根據也得有實際的結果。所以這些東西也很傷腦筋,這裏麵的看法也很多。” 那篇文章發表後,吳階平又一次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他覺得醫療小組必須要正麵澄清,於是他組織原醫療組的人向中央寫了一份報告,很快得到了鄧小平、李先念、鄧穎超的批複,他們都再次表示:醫療組對總理的治療是認真負責的,是適當的。前述文章的話並不真實。“為總理看病的經曆,讓他心裏很糾結。”吳階平的第一任秘書華杏娥回憶,有一次她陪著吳階平到“人大”開會,看到了李先念,他再次提及此事予以澄清,回來之後,說了一句:“中間李先念來了,事情說清楚了!”華杏娥說,吳階平對中央領導的治療守口如瓶,他隻是簡單跟華杏娥提過:“總理不是一個癌症,有好多癌症。” 從1957年起到1976年周恩來去世,吳階平在周恩來身邊工作了近20年。華杏娥說,吳階平的家裏,一直掛著一張12寸的周恩來的黑白照片。他的書櫥裏,擺放著總理送他的一座石英鍾。多年來,吳階平一直用這種方式來默默紀念著對他一生中影響最大的一個人。 特殊任務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打破外界封鎖,政府也積極開展外交活動,應邀為友好國家領導人治病,也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這方麵工作由周恩來總理直接負責。吳階平作為中國醫術最好的醫生,先後為4個國家的元首治過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為印尼總統蘇加諾治病。 蘇加諾患腎結石和高血壓很多年,但他拒絕手術,他的前任私人華裔醫生胡永良,也是他早年遊擊隊裏的老戰友。胡永良向蘇加諾提議,腎髒的問題西醫沒有什麽好辦法,是不是要請中醫來治療?中醫的話就要請中國的醫生。蘇加諾於是向周恩來提出了請求。 “中醫在中國是有一定的經驗,但是要出國看病還是有一定的困難的。所以周恩來就讓吳階平這個西醫來當中醫醫療組的組長,帶著中醫出國,副組長方圻也是西醫出身。”董炳琨介紹。臨行前,周恩來和陳毅還專門找醫療組談話,特別告訴他們:“有什麽事可以和大使館聯合向中央寫報告。” 其實中國醫療組赴印尼治療的環境也比較複雜:“他們的衛生部長是個準將,極力反對總統邀請中國醫生,而蘇加諾對中醫也不是很信任,我們還得想辦法讓他信任。另一方麵蘇加諾的醫療班子都是西醫,我們得和他合作,不能撇開他們單獨做事情,他的西醫和我們的中醫加在一起事情就非常複雜。”如何平衡關係,如何以中國西醫的身份,向不信任中醫的印尼醫生解釋中醫的治療,吳階平可謂責任重大。除此之外,很多細節問題,比如如何在戒備森嚴的總統府煎製中藥、如何說服蘇加諾讓他接受針灸,都是需要吳階平出麵溝通解決的。 吳階平先後5次率醫療組赴印尼為蘇加諾治病,“其實這裏麵包含著醫療、政治、外交的種種矛盾和困難,但吳階平都處理得非常好,這裏麵充分體現了他的智慧和能力”。董炳琨說。 吳階平赴印尼為蘇加諾治病期間,他的夫人趙君愷突然得了偏癱,為了不影響吳階平情緒,周恩來指示暫且不讓吳階平知道這個消息。於是當時中國駐印尼大使姚仲明把信扣了下來,隻告訴了方圻一人。直到臨回國前吳階平才得知這一消息,他說:“我完全接受總理和使館的安排。”方圻後來回憶說:“其實,我認為使館的同誌完全低估了階平同誌的覺悟水平,采取這種措施是沒有必要的。” 在與吳階平一起工作的幾年當中,董炳琨印象最深的,是他們共同參與的“李震案”。 1973年10月21日深夜,時任公安部部長李震被發現吊死在公安部機關大院地下熱力管道溝內。當時最高領導層對李震的死存疑,認為他沒有明顯的自殺動機,因而懷疑是他殺。李震的屍體被送到北京醫院太平間裏,上級要求絕對保密,隻準當時的部分醫院領導和指定參加屍檢的幾個人知道。 “李震案”由周恩來直接牽頭負責。他委派吳階平負責屍體解剖,董炳琨與林鈞才、吳蔚然、韓宗琦等人是組員,他們直接向中央負責,所有報告要幾個人同時簽名。 在當時紛亂的政治環境裏,李震之死的背後,是公安部甚至更高一層複雜的政治鬥爭。當時公安部掌權者傾向於“他殺”的結論,公安部內部也反複排查,先後有116人被懷疑與此案有牽連。可以說,對李震自殺還是他殺的鑒定,是在一種高度的政治壓力下進行的。 董炳琨回憶,其實從單純的醫學角度看,李震很顯然是自殺的:“他的頸部有明顯的繩索勒痕,胃裏有大量的安眠藥,有的還沒有完全溶化;肺髒有肺氣腫。”屍檢小組統一的意見是:死者先服藥後,自縊身亡。 在此之前,持“他殺”觀點的人認為,是有人先把李震勒死再把藥片灌進去的,造成自殺假象。“人死了之後能不能灌進去藥片,怎麽灌?我們做這個工作,必須非常仔細。所以回來之後,我們從協和醫院找了老式的食管鏡,然後在狗身上做實驗,看看在狗身上能不能做得到。”董炳琨回憶。在動物身上試驗的結果,等於推翻了這種猜測。 對“自殺”結論當時還有一種懷疑:李震是在地下室上吊的,四周沒有水源,胃裏的那麽多的安眠藥是怎麽吞進去的?周恩來顯然對此也有疑問。他對李震究竟死於自殺還是他殺也十分存疑,在他看來,李震沒有自殺的思想基礎。周恩來向吳階平仔細詢問了很多細節,最後提了一個問題:“沒水的情況下能不能吞下那麽多藥片?”吳階平回答:“沒水也能吞下去。”周恩來不放心,又追問一句:“你們試過嗎?”吳階平坦白回答:“沒有。” 董炳琨回憶,回來後,小組的人又開始針對這一個疑點進行了實驗。“我們自己幹吞藥片看能不能吞下去。吳階平帶頭吞了一小瓶酵母片,足足有100片;我們也都進行了試吞,事實證明幹吞是可以吞下去的。”“我們當時搞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就為這一件事情。每天晚上大家都要開會研究,每一個階段我們都要寫總結報告,總結報告那是字斟句酌,不留漏洞,不能讓任何人挑出毛病。每次報告都是吳階平定稿,全體小組成員簽字後上報。” “一號任務” 吳階平一生中參與的特殊任務不計其數,其中最特殊的一項,便是毛澤東遺體的保護工作。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當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要保護遺體讓各界人士參觀、吊唁、瞻仰,時間定為15天。毛澤東生前號召火葬,是政治局裏第一個簽字的領導人。所以最初決定的遺體保護,也是以保存15天為目標,醫務人員隻對遺體做了一般性處理,注射了一些甘油、酒精和福爾馬林等。 但是到了9月10日,以華國鋒為首的中共中央又決定永久保存遺體,並建立毛主席紀念堂,以供群眾永久性瞻仰。“這給醫務人員們出了一個大難題。”董炳琨解釋說,如果要永遠保存遺體,死後兩小時就要進行屍體解剖,取走內髒,用衝洗液把全身血液,包括最細微的毛細血管衝洗幹淨,注入防腐劑、凝固劑等。可是已經做的一般性處理已失掉了徹底處理的機會,遺體內血液早已凝固,再做那樣徹底處理已不可能。 中央決定成立遺體保護科研領導小組,由時任衛生部長劉湘屏、副部長黃樹則、醫科院副院長吳階平、北京醫院院長林鈞才、醫科院組織學教授徐靜和保健醫生李誌綏組成,這無疑是當時最重要的一項政治任務,隻許成功、不許失敗,還要絕對保密。 吳階平是9月11日得知新任務的。“我雖然承擔過多次重大醫療任務,但對這次的任務卻不可能像以往那樣充滿自信了。保護屍體並不難,所要求的隻是長期不腐爛,已有成熟的科學方法。保護遺體達到瞻仰的目的則完全不同,要麵部顏色、容貌、神態合乎要求,還要能接受光的照射和溫度、濕度的影響。作為一個臨床醫生,這方麵的知識當然不多,實際上還沒有成熟的科學方法。”可是,吳階平又深知,這是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雖然困難很多,卻不能不承擔下來,因此心情是很複雜的”。 “當時已有的遺體保護,最早的就是蘇聯,再就是越南的胡誌明。”董炳琨說。於是毛澤東去世的第三天,林鈞才帶領6位專家到越南了解和學習胡誌明遺體保護的方法和經驗;另一方麵,全國各地的臨床、病理、化學、物理、光學和機械學等70多位專家都被集中到北京,通宵達旦商討保護方案和技術方法。“主持這樣一個無先例可循的、多學科協同攻關的科研課題的人,必須是一個具有遠見卓識、博學多才、超凡組織領導能力的科學家,吳階平無疑是最好的人選。”董炳琨說。 9月18日追悼會結束後,中央要將遺體轉移到一個代號叫“769”的地方。遺體轉移後,具體的保護工作應該怎樣去做?這件事的責任實在太大,誰也說不好到底應該用哪一種辦法。專家幾經討論,最終決定按照北京專家的建議,暫采取液態和氣態相結合的原則。 “所謂液態和氣態相結合的原則,是指皮膚需要暴露在外的部分,主要是頭部和兩隻手在氣態中,隱蔽的部分,即身體是在液態中;平時在氣態中,一年一度的大保護時在液態中。胡誌明的遺體就是這樣處理的。”董炳琨說。 據《吳階平傳》透露,遺體保護最終按照原定的氣態、液態相結合的原則。配合這套原則,紀念堂建立了一套安全可靠的升降係統。當紀念堂開放時,毛澤東的遺體處在水晶棺中可瞻仰的位置,但不能給水分,因為水晶棺裏溫度很低,一給水分就會結霧,隻能采取幹濕結合的辦法,在遺體的衣服裏都包著水,也就是不裸露在外的地方實際上是處於液態保護環境,隻有麵部是處於氣態環境。瞻仰結束後遺體降到地下保護間一個特殊密閉的容器裏,在這裏給遺體更多的水分。每年毛澤東的生日之後,也就是12月26日後,都要停止瞻仰一段時間,把遺體完全泡在液體裏補給充足的水分。 從1976年9月到1977年8月,吳階平他們在地下室工作了一年時間,執行這代號為“一號任務”的特殊使命。而地上發生了翻天覆地、震驚中外的變化,也是在這一年中。“文革”十年當中,吳階平沒有經曆平常意義上的大起大落,然而這3000多個日日夜夜,他也猶如在“走鋼絲”,這條鋼絲上走過的不少人都栽下去了,可是正如《吳階平傳》裏的評價:“使他身體保持平衡的杠杆兩端,一頭是他精湛、高超的醫術,另一頭則是他的政治敏感與審時度勢的本領。” 情義之人 93歲的馮佩之,與吳階平搭檔共事過兩次,由此結下了近乎半個世紀的“同誌+兄弟”的深厚情誼。 與吳階平出身不同,馮佩之是解放前就在冀中一帶參加革命的老幹部。1962年,他被調到北京第二醫學院做黨委書記。馮佩之還記得赴任之前,衛生部部長崔月犁叮囑他:“吳階平是位新黨員,未來要承擔更重要的工作,要好好幫助他。” 那一段時間,正逢吳階平赴印尼治療,而其夫人趙君愷得了偏癱。馮佩之每天下班以後,都到友誼賓館接上有名的針灸醫生到吳家為趙君愷治療,每天如此,經過一段時間治療,趙君愷病情有所好轉,“能夠自己蹬縫紉機了”。久而久之,馮佩之不僅與吳階平的父母、嶽父母熟識起來,而且和吳階平的幾個孩子也相處得非常好。“有時候我去他們家,趙君愷在做飯,我就替她抱女兒。” 如果說兩人的關係之初,還有點為工作而考慮的“團結”之意,後來則因彼此欣賞而演變成私人友誼。馮佩之告訴本刊記者,吳階平也經常到馮家來,3個孩子也一口一個“吳伯伯”叫得親熱,吳階平經常對馮佩之的幾個孩子說:“你們長大了要學醫,當醫生很好啊!”如今馮佩之的兩個女兒和女婿都是醫生,就是深受“吳伯伯”的影響。 “文革”之始,身為北京師範學院(首都師範大學前身)院長兼黨委書記的馮佩之,首當其衝,成了第一批被打倒的大學校長,沒有行動自由;彼時,吳階平已經走進中南海,成為領導人的保健醫療組長,兩人的境遇迥然不同,也很久都沒有見麵。 某一天,吳階平委托他人找到馮佩之的孩子,送來了一張票,是莊則棟等人出國歸來在首都體育館舉行的表演賽。那時候,馮佩之的情形有了稍許好轉,“造反派”暫停了對他的批鬥,也允許他住在家裏,有了些小自由,可是行動之中還是有人監視。 “好多年沒見他了,我挺想他的,又不知道他怎麽樣,所以我決定拿這張票去看看。”進到首都體育館,馮佩之看到了自己一直惦記的老朋友吳階平。吳階平看了馮佩之一眼,沒有說話,仿佛不認識他。馮佩之也擔心會給老朋友有任何不好的影響,“也不敢正眼看他”。 過了一會,馮佩之突然聽到吳階平那邊傳來低低的聲音:“老馮,你怎麽樣?”可是說話的時候,吳階平的臉還是衝著前方。解放前從事地下工作的馮佩之馬上心領神會,也一邊目視前方一邊壓低聲音告訴吳階平,自己被批鬥已告一段落,現在主要是勞動改造。吳階平又問:勞改怎麽樣?馮佩之回答說:“我們這些走資派,勞動強度非常大,總是幹重活,我腰總是疼。” 吳階平聽罷,略一思索,又悄聲說:“你後天到北京醫院第一附屬醫院,找一位叫周仁厚的大夫,他是骨科專家,我讓他給你看看。” 對於自己在中南海的現狀,吳階平沒有半點提及。最後,兩人說了些互相保重的話後又裝作陌路人各自散去。整個談話當中,兩人都是目視前方,從沒有側過頭看對方一眼,即便暗中有監視的人,也絲毫不會察覺到任何破綻。 按吳階平說的時間,馮佩之請假到了北京醫院,在骨科病房找到了周仁厚。雖是初次見麵,但周仁厚對馮佩之非常熱情,這讓很長時間沒有人敢搭理的馮佩之很是感動。周仁厚為馮佩之檢查之後,寫了一個診斷書,上寫:腰椎間盤突出,建議免除勞動,休息3個月。馮佩之明白這是吳階平暗自幫助自己。有了這張假條,馮佩之的境遇改善不少。3個月後,馮佩之需要到“造反派”指定的醫院複查,醫生隻要看到最初的診斷書上署的“周仁厚”之名,出於尊重,都是按照他的醫囑寫下來,於是馮佩之憑借這張診斷書,免除了重體力勞動改造之苦,一直到了“文革”結束。重獲“解放”之後,心懷感激的馮佩之專程去看望周仁厚,老教授笑著說:“你哪裏有腰間盤突出!” 馮佩之的工作後來幾經調動,從北京第二醫學院到北京師範學院,“文革”後,先是到八機部做副部長,後來又到北京工業學院(現北京理工大學)做黨委書記。吳階平出任協和醫科大學校長兼醫學科學院院長後,他找到分管中組部的宋任窮,堅決要求把馮佩之調到協和做黨委書記,兩人於是有了第二次搭檔,其友情也一直延續下來。馮佩之說,一直到吳階平當人大副委員長,每年大年初一,第一個到馮家來拜年的,一定是吳階平。 因為腿腳不便,馮佩之沒有參加吳階平的追悼會,他讓老伴和女兒代表自己去了八寶山。回來之後,他細細地向女兒問起:吳伯伯變化大嗎?瘦得多嗎……“我失去了一個好朋友、好兄弟……”老人家長長歎了一口氣。 “國之大醫” “我們國家的名醫很多,在醫學上做出突出成績的人也很多,可是像吳階平這樣全麵的人,各方麵都比較優秀的人,在我遇到的人裏麵還沒有找到。”董炳琨說。 畢業於上海醫學院的華杏娥原是協和醫院內科醫生,後來被調去任吳階平秘書。華杏娥告訴本刊記者,吳階平非常重視教育。在協和醫學院任校長期間,每年他都要親自給新生上第一堂課。他給這些未來的醫生講從一開始學醫,每一步應該怎麽樣走;吳階平經常舉外科大夫做闌尾手術的例子,他說:“闌尾手術誰都會做,但是這裏麵的學問很大,醫生做得有好有壞,闌尾炎有輕有重,有發膿的、有死的,就是告訴學生別看是普通小病,其實裏麵的學問很多,要思考,並且要通過實踐來提高。” 1982年,由吳階平主持編譯的《性醫學》麵世。其實對青少年進行性教育,是周總理生前多次向吳階平提及的一個願望,吳階平也一直以此為自己的責任,並成為打開性教育這扇封閉已久大門的關鍵人物。《性醫學》出版後,轟動一時,書店甚至將它和那些滯銷書捆綁在一起銷售。“書攤上都打著‘吳階平性醫學’的招牌,我說,吳老不得了,街上都打了你的名字,吳老也有些無奈:怎麽能這樣子。”華杏娥微笑著回憶。吳階平還有一個願望是在學生中進行科學的性教育,為此他在《紅旗》雜誌上發表《青年的性教育刻不容緩》一文,呼籲製訂相關教材。可是他的建議遲遲得不到批準,曆經8年多,直到吳階平當上人大副委員長,此事才有轉機。 提起吳階平,華杏娥最深的印象是“聰明、能力強”。華杏娥說,當時吳階平身兼數職,既要管理行政工作,參加學術活動,還要出席許多外事活動。“他一個人兼顧這麽多,但是‘忙而不亂’,千頭萬緒他都處理得非常協調,從來也沒有見他著急的樣子,再多的事情他也從來不發火,不埋怨。”華杏娥說,吳階平當時還擔任“新藥審定評審委員會”主任,每一個新推出藥品都要他簽字。可是新藥申報的材料都非常多,堆在地上有1米多高。事務繁多的吳階平不可能全部仔細看完,但是那些冗長的材料,他隻看幾眼,便會一下子就看出其中要害,這份超常的智慧和能力讓華杏娥佩服不已。 有一件小事讓華杏娥印象深刻:“有一次他在跟我交代工作的時候,財務處的一個小女孩敲門進來給我一張支票,我看都沒看,順手交給他。他看了一眼馬上說,少了一個零。”這是很大數目的一筆基金,華杏娥驚出一身冷汗。但吳階平卻沒有說什麽。“出了這麽大的差錯,他不批評比批評還厲害。”華杏娥說。 “無論是給毛主席的醫療,還是給門口的一個工友看病,他都一視同仁。”華杏娥說,協和的工友都喜歡吳階平,有什麽毛病也“吳大夫吳大夫”地找他,吳階平也從不拒絕。為吳階平做秘書這麽多年,華杏娥從沒見吳階平發過脾氣。有一次,清潔工剛剛打掃完畢,地上比較濕。去辦公室的路上,吳階平腳下一滑摔了一大跤,把華杏娥緊張得要命。那時吳階平已是七旬有餘,可是他爬起來就走,還囑咐華杏娥不要埋怨工友,“是我自己不小心”。 吳階平的第一段婚姻有著濃重的舊時代色彩——他的第一任妻子趙君愷是父親為他定的親。當年,在燕京大學醫預科學習時,16歲的吳階平居然已經結婚,這成為校園一大新聞。吳階平戲稱自己是“包辦的自由婚姻”,與趙君愷關係也很好,兩人共同生活了45年,直到1978年,趙君愷因為嚴重的心肌梗死引起突發性心髒破裂去世。幾年後,他與高睿重新組織家庭,又相攜走過近30年。 華杏娥精心保存著她與吳階平在2006年的一張合影,那是她最後一次見吳階平。之後不久,她就聽說吳階平患了感冒,不久就住了院;“後來聽說他吃飯嗆到了,就給他下了一根管子,直到腸子裏,一直是鼻飼,也無法吃飯,一直就沒出院。”半年前她聽說吳老住進了ICU(重症加強護理病房),直到後來傳來去世的消息。“看著這些照片,挺懷念他的……”華杏娥眼圈紅了,低頭看著她特地找出來的那些照片。在每一張照片上,吳階平都在溫和地笑著。 *****
|
|
| ( 時事評論|公共議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