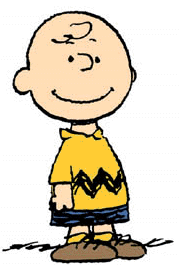因為要找以上這聯全詩,找到這篇文章
孫慶餘也引用了這首詩,同樣沉重:
http://taiwandaily.com.tw/news.asp?News_class_NO=03&News_no=15890&Up_date=2006/01/26
關於郁達夫的一聯句
鄢烈山
http://www.jwb.com.cn/gb/content/2001-12/15/content_65110.htm
郁達夫的名句“曾在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如今被廣為傳誦。上網在google裏鍵入“鞭名馬”、“累美人”的關鍵字,可以搜索到許多引用它的文章。引用者的“版本”(主要是“生怕情多”四字)五花八門,不錯的是都知道典出郁達夫。
這個聯句之所以膾炙人口,揣摩引用者意思,差不多都是把它當作名士風流的寫照。在一般人心中,帶自傳色彩寫留日學生偷窺東洋女(《沉淪》),與王映霞發生如火如荼的戀情,這樣的郁達夫正是風流浪漫的標本。他的這一聯句除了“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似的淺懺深戀能有什麼別的內涵呢?
如果我們把這一聯句“放”回原詩,依著全詩的情緒來品味,詩人抒寫的情懷決非浪漫或輕薄之類;恰恰相反,是對個人生活真誠的自警,是感時傷世滿腔的憂憤。
全詩是一首七律:“不是尊前愛惜身,佯狂難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數東南天作孽,雞鳴風雨海揚塵。悲歌痛哭終何補,義士紛紛說帝秦。”見於“1932年8月在上海寫”的遊記《釣台的春晝》。
這篇遊記記的是,“一九三一年,歲在辛未,暮春三月,春服未成,而中央黨帝,似乎又想玩一個秦始皇所玩的把戲了,我接到了警告,就倉皇離去了寓居”,在江浙附近的窮鄉里遊息。詩人夜探桐君山,徘徊古道觀;朝發富春江,造訪嚴子陵祠堂。倦臥江舟之時,夢中“還背誦了一首兩三年前”做的“歪詩”,即這首七律。而這首“歪詩”是“在和數年不見的幾位已經做了党官的朋友高談闊論”時做的。
尊即樽,酒器。因為是在“樽前”即酒席上做的,便有首聯和頷聯辭謝勸杯的句子。“佯狂難免假成真”可以說是悟道之言。佯狂者,或不願同流合污或憤世嫉俗;弄假成真的史不絕書,遠有狂飲無度的劉伶、窮途而哭的阮籍,近有放浪形骸不幸暴亡的龔自珍。杜甫曾有詩句贈李白:“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狂放不羈)為誰雄?”這些前人古意,與達夫此詩尾聯云“悲歌痛哭終何補”顯然是相通的。
請注意不論是1931年春,詩人面臨被“焚書坑儒”的危險,倉皇避禍鄉間之際,還是在此“兩三年前”,即國民黨蔣介石大肆清共鏟共之時,中國到處都籠罩著一片白色恐怖。所以此詩的頸聯有“劫數東南天作孽,雞鳴風雨海揚塵”的描繪。
共工在《尚書》與《史記》中是堯帝時的“四罪”(四大惡人)之一;在《淮南子》中是一人面蛇身的神話人物,他與顓頊爭帝位,造成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的大災變。“劫數東南”無非借這樣的典故狀摹國共內戰給中國造成的深重災難。《詩·鄭風》中有“風雨淒淒,雞鳴喈喈”、“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句子,脫胎於此的“雞鳴風雨”,藉以描寫中國漫漫長夜的昏昧。詩人用的典很平常,表達的憂思卻不平常。
國民黨這個“中央黨帝”對郁達夫這樣的知識份子採用的是或拉或打的兩手。做御用文人,為“黨帝”的專制獨裁效力,高官有得做,駿馬有得騎,是為“拉”;當年與郁達夫一起留學東洋有慷慨赴國難之志的朋友,回國後成了識時務的俊傑,他們就是遊記中所說“已經做了党官的朋友”。正是這樣一些以前似乎志同道合、有戰國高士魯仲連義不帝秦的高風亮節的朋友,在觥籌交錯酒酣耳熱之際,“紛紛說帝秦”,即遊說詩人擁戴專制獨裁的國民黨政權。當然,作者沒有被說動,於是,就只有亡命窮鄉遁跡山水。
可見,整首詩的原意,第一層意思,是對國民黨實行專制主義禍害中國的強烈抗議,對趨炎附勢投靠“中央黨帝”的無行文人的極大輕蔑。
到了作者寫這篇遊記的1932年8月,此詩的語境已變,所指相應地有了發展。1931年發生“九·一八”事變,張學良奉命不抵抗致使日寇迅速佔領我東北全境;1932年“一·二八”事變,日軍侵佔上海,國民黨政府遷都洛陽;3月溥儀偽滿政府成立,改長春為“新京”。跨海淩波,日寇的鐵蹄揚塵而來,大有一口吞下華夏九州的態勢。此時“劫數東南天作孽,雞鳴風雨海揚塵”用來描述作者對民族危亡的殷憂。“北地小兒耽逸樂,南朝天子愛風流”(郁達夫《過岳墳有感時事》句)是當權者的罪惡,而那些賣國求榮的文人效忠日本帝國,或鼓吹投降主義,或鑽進偽政權分一杯羹,則令詩人噁心。所以,詩人在嚴子陵祠裏,借品鑒“亡清遺老”夏靈峰先生的人格,說“比較起現在那些官迷財迷的南滿尚書和東洋宦婢來,他的經術言行,姑且不去論它,就是以骨頭來稱稱,我想也要比什麼羅三郎鄭太郎(指羅振玉、鄭孝胥)輩,重到好幾百倍。”於是詩人把這首舊作題在嚴祠的高牆上。
可見,這又是一首抒寫抗日愛國情懷,鞭笞喪失節操的卑鄙文人的詩。
單挑“曾因酒醉……,生怕情多……”來欣賞,恰如只見一朵離枝的鮮花,卻不認整枝的玫瑰;不,應當說是,恰如從整株仙人掌上摘下了一朵眩人眼目的小花,而有意無意抹煞它的母體。
詩人龔自珍作于道光五年(1825年)的《詠史》,即頸聯“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廣為傳誦的那一首,與郁達夫的這首詩的意境和情感頗為相通,茲錄於後:
金粉(繁榮昌盛)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盆(煮鹽設備,代鹽商、大款)狎客(傍大款的幕友幫閒)操全算(計畫、操控全局),團扇才人(大貴族子弟)踞上游(佔據社會上層位置)。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田橫五百人(寧死不降漢高祖的齊國義士們)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都被朝廷招安加官晉爵了)?


 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